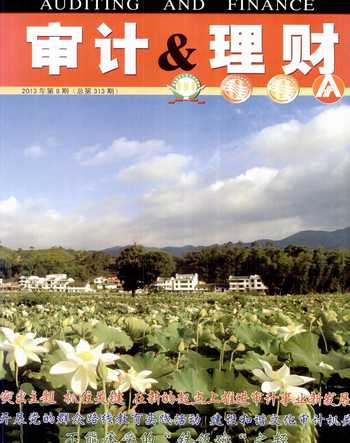農(nóng)網(wǎng)改造的秘密
湛新民 江紋
項(xiàng)目簡(jiǎn)介
G市審計(jì)局在對(duì)C縣第三期農(nóng)網(wǎng)改造工程項(xiàng)目竣工決算審計(jì)時(shí),發(fā)現(xiàn)有幾個(gè)村總是停電,分析認(rèn)為有可能是工程質(zhì)量存在問題,在排除線路設(shè)計(jì)、施工技術(shù)等方面存在問題的可能性后,審計(jì)人員迅速將目標(biāo)鎖定在施工耗用的材料質(zhì)量上。通過對(duì)經(jīng)常停電村與供電正常村耗用材料的對(duì)比分析,最終揭開謎底,證實(shí)項(xiàng)目建設(shè)單位存在工程材料“以舊代新”,套取項(xiàng)目資金賬外私分,影響工程質(zhì)量等問題。
審計(jì)過程
2009年6月,G市審計(jì)局派出審計(jì)組對(duì)C縣農(nóng)網(wǎng)改造第三期項(xiàng)目竣工決算情況進(jìn)行就地審計(jì)。審計(jì)組在聽取C縣供電公司關(guān)于該縣農(nóng)網(wǎng)改造工程實(shí)施情況的匯報(bào)后,即分成兩個(gè)小組,由審計(jì)組長(zhǎng)帶一組在縣城,對(duì)農(nóng)網(wǎng)改造的財(cái)務(wù)收支決算情況進(jìn)行審計(jì);項(xiàng)目主審帶一組到農(nóng)村鄉(xiāng)鎮(zhèn),抽查5個(gè)鄉(xiāng)鎮(zhèn)的農(nóng)網(wǎng)改造工程實(shí)施情況。
審計(jì)調(diào)查小組就入戶網(wǎng)線上戶調(diào)查時(shí),有不少村民反映,他們使用的電表很多是兩、三個(gè)月前買的,剛用不久還是新的可以不換,可是供電所和施工的人硬說農(nóng)網(wǎng)改造后使用的是新的計(jì)電箱,以前的電表不能用,否則電表會(huì)走得很快,這是為農(nóng)戶利益著想,所以必須全部換成供電所提供的新的電表,每戶每只電表僅收取材料成本費(fèi)60元。
“既然是這樣,收也就收了。但是,我們的舊電表不能用,為什么還要收去不讓我們自己處理?算里面的漆包線和塑料外殼,廢品收購(gòu)站每只電表可賣10塊錢呢!”村民們的話語(yǔ)里顯露出些許不滿。
農(nóng)網(wǎng)改造政策規(guī)定臺(tái)區(qū)和戶外農(nóng)網(wǎng)廢舊物資由建設(shè)單位負(fù)責(zé)拆除和回收處理,但網(wǎng)線入戶后的廢舊物資由農(nóng)戶自行處理。審計(jì)人員初步判斷,供電所和施工人員強(qiáng)行收走農(nóng)戶購(gòu)買的舊電表是違反農(nóng)改政策的,但隨之而來(lái)的疑問是,這些被收走的電表哪去了?是如何處理的?
村民們還反映,他們這有幾個(gè)村經(jīng)常停電,一問供電所,就說現(xiàn)在是高溫季節(jié),用電高峰,變電站負(fù)荷不了,自然就停了。可他們不理解,為什么總是停這幾個(gè)村,而且下半年的大冷天不是用電高峰也不是高溫季節(jié),照樣常停。
就在審計(jì)組上戶調(diào)查的幾天里,的確趕上了幾次停電,而那時(shí)縣城審計(jì)的一組告訴說他們那里沒有停電,打電話問與停電村同一供電所的其他鄉(xiāng)村,證實(shí)也沒有停電。
為什么呢?是變電站負(fù)荷過大而不得已停電?可為什么只停這幾個(gè)村的,就不輪流停別的村的呢?會(huì)不會(huì)存在施工質(zhì)量的問題?針對(duì)這一疑問,審計(jì)人員對(duì)有關(guān)供電所進(jìn)行了調(diào)查,結(jié)果表明:絕大部分村的工程項(xiàng)目都是鄉(xiāng)鎮(zhèn)供電所從縣電力安裝公司手中轉(zhuǎn)包過來(lái),再聘請(qǐng)各村電工具體施工,并由電工自行承擔(dān)施工質(zhì)量監(jiān)理任務(wù)。而這幾個(gè)老停電的村都是負(fù)責(zé)城網(wǎng)改造的縣電力公司親自實(shí)施。有施工資質(zhì)的公司,其施工質(zhì)量應(yīng)該會(huì)比村里的電工強(qiáng)啊?那老停電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這些疑問留在了審計(jì)人員的腦海里。
農(nóng)村調(diào)查的小組返回縣城,將調(diào)查結(jié)果反饋給被審計(jì)單位。被審計(jì)單位承認(rèn),縣城和農(nóng)村確實(shí)每戶收取了60元電表款,但將舊電表全部更換為新電表是為了保證工程質(zhì)量。考慮到全縣回收的電表和計(jì)電箱太多,會(huì)增加農(nóng)改工程的回收、儲(chǔ)運(yùn)和保管成本,且全部為不可再利用的廢舊物資,故公司開會(huì)研究決定,由施工員自行處置舊電表等,不納入公司財(cái)務(wù)和物資保管賬。但有個(gè)條件,是施工員回收時(shí)要電改農(nóng)戶自愿。
至于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的幾個(gè)村經(jīng)常停電的問題,供電公司負(fù)責(zé)人說施工質(zhì)量絕對(duì)沒問題,這幾個(gè)村的農(nóng)網(wǎng)改造工程都是縣電力公司親自施工的——說著還拿出了相關(guān)施工合同和監(jiān)理日志。可能是農(nóng)網(wǎng)改造剛完成不久,變電臺(tái)區(qū)和線路有個(gè)適應(yīng)和調(diào)整的過程,這個(gè)我們會(huì)跟進(jìn)維護(hù)。
被審單位的解釋似乎符合邏輯,也許C縣農(nóng)網(wǎng)改造真不存在什么大問題。晚上,審計(jì)組就近期的工作,展開了討論。審計(jì)人員甲認(rèn)為:根據(jù)農(nóng)戶反映情況時(shí)的態(tài)度和語(yǔ)氣,足以說明“農(nóng)戶自愿”的說法站不住腳。電表的問題應(yīng)細(xì)查,我們可以到廢品收購(gòu)站看一看。項(xiàng)目主審提出:關(guān)于幾個(gè)村經(jīng)常停電的問題,被審計(jì)單位解釋的“變電臺(tái)區(qū)和線路有個(gè)調(diào)整與適應(yīng)的過程”的理由同樣也不可信,調(diào)整與適應(yīng)的過程應(yīng)該是全縣的農(nóng)網(wǎng),而不是單單這幾個(gè)村。而且,同一施工單位的城網(wǎng)改造項(xiàng)目,經(jīng)了解除線路檢修和上面通知停電外,并沒有停電的情況,由于施工技術(shù)導(dǎo)致質(zhì)量問題的因素完全可以排除。可疑的是,為什么絕大多數(shù)的村都是由鄉(xiāng)鎮(zhèn)供電所聘請(qǐng)各村電工自行施工監(jiān)理,偏偏這幾個(gè)村由縣電力安裝公司親自施工并監(jiān)理?這里面一定隱藏著什么秘密。那是什么秘密呢?
審計(jì)組分析判斷,既然停電與施工技術(shù)質(zhì)量沒關(guān)系,那肯定就是施工耗用的材料質(zhì)量有問題。因此決定,再分兩個(gè)小組,一組負(fù)責(zé)查實(shí)農(nóng)戶廢舊電表回收處理情況;另一組重點(diǎn)調(diào)查核實(shí)經(jīng)常停電的幾個(gè)村農(nóng)網(wǎng)改造耗用的材料,從施工材料上撕開一個(gè)突破口。
審計(jì)一小組對(duì)負(fù)責(zé)廢舊材料物資回收、處置或再利用的供電公司下屬的物資公司的材料賬進(jìn)行審計(jì),并延伸調(diào)查了縣城僅有的三家廢品收購(gòu)站,結(jié)果正如農(nóng)戶反映的,供電公司按每只電表平均10元的價(jià)格處理廢舊電表,處理收入230.12萬(wàn)元全部作為“小金庫(kù)”,用于發(fā)放農(nóng)網(wǎng)改造中付出“辛勤勞動(dòng)”的公司領(lǐng)導(dǎo)與業(yè)務(wù)人員的下鄉(xiāng)補(bǔ)助。
審計(jì)二小組先是返回停電村施工現(xiàn)場(chǎng)實(shí)地檢查線路質(zhì)量,他們爬上電線桿和房頂察看,發(fā)現(xiàn)施工耗用的電纜導(dǎo)線很舊,很多地方還用絕緣膠布包裹著,還有部分村使用的變壓器也是翻新的。審計(jì)人員現(xiàn)場(chǎng)拍照并抄寫導(dǎo)線上標(biāo)明的品牌、規(guī)格后,又到其他供電正常的村將施工耗用的材料進(jìn)行比對(duì),發(fā)現(xiàn)不僅材料新舊程度不一樣,品牌型號(hào)也不一樣。審計(jì)人員立即返回縣城,找到縣供電公司材料倉(cāng)庫(kù)保管員,要求其提供幾個(gè)停電村領(lǐng)取材料的出庫(kù)清單。倉(cāng)庫(kù)保管員說,這些材料都是縣電力安裝公司直接提走的,進(jìn)和出都沒有通過倉(cāng)庫(kù)保管賬。
找到電力安裝公司負(fù)責(zé)人馮某,要求提供那幾個(gè)村的電纜導(dǎo)線、變壓器等材料來(lái)源、領(lǐng)取和使用情況。馮某以時(shí)間久了記不清或財(cái)務(wù)人員不懂財(cái)務(wù)、賬證不全等各種理由拒絕提供。審計(jì)人員將施工現(xiàn)場(chǎng)獲取的實(shí)物證據(jù)擺在馮某面前,要他認(rèn)清事實(shí),不要作無(wú)謂的抵賴和狡辯。
在證據(jù)面前,馮某不得不交待,這幾個(gè)經(jīng)常停電的村莊,使用的是縣城網(wǎng)絡(luò)改造拆卸下來(lái)的舊電纜導(dǎo)線,本來(lái)就已經(jīng)老化,加上一拆一裝和途中運(yùn)輸磨損,很多導(dǎo)線的外皮脫落,內(nèi)線斷裂,是用絕緣膠布封上的,而他們的變壓器也是縣城電網(wǎng)改造時(shí)換下來(lái),經(jīng)過適當(dāng)檢修裝上的。經(jīng)常停電由此而來(lái)!這幾個(gè)村的農(nóng)網(wǎng)改造之所以要由C縣供電公司下屬的電力安裝公司親自施工,其目的不是為了確保農(nóng)網(wǎng)改造質(zhì)量,而是為了掩飾其不能讓農(nóng)戶知道的秘密。
經(jīng)審計(jì)初步測(cè)算,C縣供電公司在農(nóng)網(wǎng)改造中采用電纜導(dǎo)線、變壓器“以舊代新”的手法,虛列工程成本套取資金280余萬(wàn)元,套取的資金一部分用于彌補(bǔ)供電大樓建設(shè)的不足,一部分落入縣供電公司領(lǐng)導(dǎo)、財(cái)務(wù)人員等個(gè)人口袋。
審計(jì)體會(huì)
本案審計(jì)人員把在實(shí)地調(diào)查中聽到的村民關(guān)于舊電表被收走的抱怨和有的村莊經(jīng)常停電的現(xiàn)象作為疑點(diǎn)線索,追查出供電公司將農(nóng)網(wǎng)改造的導(dǎo)線和變壓器“以舊代新”,謀取私利的案件。此案例提示我們,一是審計(jì)工作,不能就賬論賬,應(yīng)善于觀察與審計(jì)項(xiàng)目相關(guān)的異常情況,并探尋其背后的原因,一個(gè)看似偶然的異常現(xiàn)象,其背后常常隱藏著較大的秘密。二是應(yīng)充分重視取得一手證據(jù)和從外圍取證。此案審計(jì)人員通過現(xiàn)場(chǎng)察看,實(shí)地拍照,取得供電公司“以舊代新”的證據(jù),令其無(wú)從狡辯。供電公司用舊電表設(shè)立小金庫(kù)的問題,從公司賬面難以發(fā)現(xiàn)和取證,審計(jì)人員于是從外圍廢品收購(gòu)站入手,獲取了關(guān)鍵證據(jù)。
(作者單位:九江市審計(jì)局、江西省審計(jì)廳)
- 審計(jì)與理財(cái)?shù)钠渌恼?/dt>
- 老兵新傳
- 欲留吾心山水間
- 又見桃源
- 央行連續(xù)三次展開逆回購(gòu)操作,今日回籠資金50億等28則
- 漫漫人生路悠悠審計(jì)情
- “酸甜苦辣”審計(jì)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