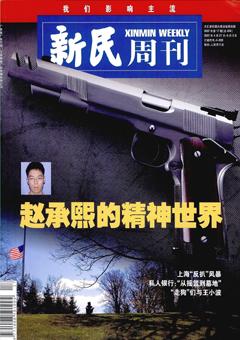“狀元”落榜之贊與貶
熊丙奇

當教育機構無法讓公眾相信復試成績與筆試成績是一樣過硬、一樣可信之后,任何一種錄取結果,都可能遭致不同角度的質疑。
最近,全國人大代表王全杰為其在考研筆試中獲得報考學生“頭名”,且領先“榜眼”12.5分,但最終被所報考單位拒錄的學生“打抱不平”,王代表在博客中發文《我考研分數第一我卻落了榜》,直指研究生招生復試中存在“貓膩”,其博客很快就吸引了10余萬點擊率,數千跟帖,相當大的比例,贊同王代表,與他一起聲討研究生招生單位的黑幕與交易,呼吁取消隱含著眾多不公平因素的考研復試。
對于研究生招生單位究竟是否存在貓膩,筆者不可憑空而論。讀到這篇博文,聯想起三年前的“甘德懷考博”事件,腦子里立刻浮現出近年來輿論對香港地區高校“拒招”內地個別狀元的一片贊揚之詞,記得相關的題目是“港校拒招狀元給我們的反思、啟示”,認為港校注重人才的綜合素質,不唯分是論,真正倡導了“素質教育”——其實,香港有沒有“素質教育”一說,我不得而知,但筆者不由思考這樣的問題:對于境外高校的招生,為什么我們會不由自主地相信其會秉承公平與公正,而不會懷疑“狀元”落榜中有何貓膩,更不會擔憂境外高校不招收狀元會惹怒“成績優異者”,但卻會不由自主不相信內地招生中會秉承公平與公正,并進而懷疑第一名落榜肯定有不可告人的黑幕呢?出現這種現象,筆者認為,關鍵之一在于內地教育機構(高校及研究生培養機構)的公信力幾乎喪失殆盡。根據王代表提供的幾個證據——筆試考分第一、高出第二名12.5分、復試感覺順利、大學表現優秀——說實話,對此也很難就斷言研究生招生單位在招生過程中一定存在貓膩。因為按照當前的研究生錄取規則,筆試成績第一,復試落榜的可能性不但存在,而且可能性極大——以北京大學發布的2007年研究生章程為例,章程規定:“復試不及格者不予錄取。復試及格者能否錄取,以考生的總成績名次為準。總成績包括兩部分,即初試成績和復試成績。復試成績占總成績的權重一般在30%至50%的范圍內。”根據這樣的章程,筆試第一名,顯然不等于“總成績”第一名,如果因為復試不合格、或者總成績分數排位低而落榜,完全是規則所允許的。此次“狀元”落榜,很可能就是因為其在面試中表現不佳,得分不及格或者較低,從而在總成績榜上輸給他人。但是,從當下的社會輿論分析,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筆試成績是難以做手腳,可以保證公平公正的,而擔憂復試成績有“太大”的“水分”與人為操作空間。
王代表為弟子“復試”成績的“不可信”提供了兩個依據,一是在筆試中沒人送禮給監考官,而在面試中卻有不少人托面試官;二是兩個小時的面試無法對面試對象進行全面評價。高校與招生單位能對這兩個“不可信”質疑給予正面回答嗎?對于前者,在復試中托人、找人幾成公開的秘密,有權有勢者更是如魚得水;對于后者,從面試委員的組成,到面試的內容、評價標準,歷來就存在爭議,學術管理的行政化,以及教授學術聲譽的下降,無法保證評價本身完全按學術標準獨立行事。這正是內地招生復試與境外高校相比的“軟肋”所在——我們前不久剛剛熱議內地女博士在香港高校的行賄事件,這反映出香港高校對“托人”、“找人”的深惡痛疾,也反映出香港高校教授的學術品行——這也正是造成內地高校“聲名掃地”之原因。
當教育機構無法讓公眾相信復試成績與筆試成績是一樣過硬、一樣可信之后,錄取規則本身的權威與公正就遭受質疑。任何一種錄取結果,都可能遭致不同角度的質疑——按筆試分數高低依次錄取,也會有指責說復試是擺設,是浪費時間與金錢;而按綜合成績錄取,筆試高分者顯然不服。
但,可以想象,如果所有招生錄取考試全部回到分數至上、筆試至上這一弊端眾多的過去模式,中國教育的應試教育將進一步被強化,中國社會的教育觀、人才觀將進一步被扭曲。因此,我們需要呼吁的不應是取消復試,而應是如何進一步建立可以保證公平、公正的教育制度,對教育體制進行根本改革,包括打破教育資源的壟斷,促進高等教育的競爭;改革高等教育內部管理體制,淡化教育的行政管理氛圍,并由此重建高校與教育機構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