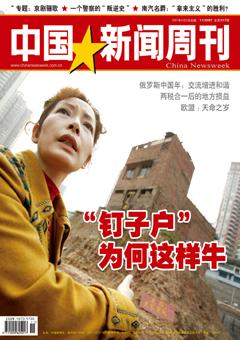“儒學計劃經濟”能靈?(下)
黨國英
解決社會上諸多問題的辦法還是要靠市場化和民主化改革,而不能退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老的計劃經濟不行,給計劃經濟戴上儒學的帽子還是不行
“儒學計劃經濟”取媚眾人的一個做法是對現實的某種特殊的批判。目前,見諸報刊、網絡的批評文字多集中在官場腐敗、分配不公和環境危機幾個方面。但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還是要靠市場化和民主化改革,而不能退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老的計劃經濟不行,給計劃經濟戴上儒學的帽子還是不行。現在社會上大量問題的存在是因為改革的不夠,而不是改革的基本趨向存在錯誤。
“儒學計劃經濟”論者給資源緊張問題開出的藥方是烏托邦幻想,這個藥方甚至會導致政治上的全面的極端集權主義。有論者稱,中國人應該過一種“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簡樸生活,對現代化的道路提出懷疑。我以為,作為個人的生活態度,誰要選擇鄉間的生活甚至是落發為僧的生活,無所謂正確或錯誤,但要干預民眾的生活選擇,就值得探討了。改革開放的結果之一是給廣大人民群眾增加了生活方式的選擇機會。經驗已經表明,絕大多數人民群眾愿意通過自己的努力和競爭過上物質豐裕的生活,而上世紀80年代出生的年輕一代會有更廣泛的生活興趣。試問“儒學計劃經濟”論者,你們如何去改造他們的生活方式,讓他們過一種簡單的生活?他們不愿意選擇你給他們的生活方式怎么辦?改造他們的思想?為了實現你們的政治“理想”,你們很有可能會全面控制消費品的供應,難道讓我們的社會退回到上世紀60年代么?
“儒學計劃經濟”論者描述的生活前景很令我們迷惘和憂慮。我們不知道究竟什么是“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生活。迄今為止,描述生活水準的最重要的指標是“恩格爾系數”。為了降低生活的各種消耗,我們是不是要過一種“恩格爾系數”為0.8的生活?或者我們該學習美國阿米什人的生活方式,不用電,也不用任何動力機械?或者放寬地說,我們是不是從今天開始應堅持“零增長”原則?
對于這些選擇的后果,我想起一些西方人士對中國西藏政策的批評,他們希望我們的西藏保持一種“原生態”的生活方式,否則,西方的旅游者到了中國看不到中國的落后,豈不掃了人家的雅興?“儒學計劃經濟”論者既然只能勸說中國人保持對發展的克制,而不能勸說西方人放棄他們的特別“文化”,那么,西方人要來我們這里攫取資源,我們拿什么抵御他們?批評者總是聲稱要反對“叢林原則”,可是,如果我們聽了他們的勸告放棄“叢林原則”,不去和西方競爭,西方人就能當一個公正的“國際警察”來保護我們的“田園詩”般的生活么?再說,社會的權威結構必然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原生態的經濟發展水平必然伴隨以人身依附為特點的權威結構,此時不論儒家學說的調門有多高,人對人的奴役將是基本的社會關系,“儒學計劃經濟”論者是不是對這種社會結構情有獨鐘?
資源問題還是要通過發展來解決。資源的數量和利用效率是技術變化的函數,而技術變化則是制度變遷的函數,經濟發展的歷史資料可以確鑿地證明這一結論。如果把環境養活人口的能力作為資源緊張度的指數,原始社會的資源緊張程度大大超過當今社會。從目前全球的人口以及人口的生存方式看,資源緊張的確是一個嚴峻的問題,但這正是新一輪技術創新的時機。有兩項技術對未來人類命運有決定性的影響,一是受控熱核反應技術的突破,另一則是轉基因農產品安全技術的突破。前一技術突破后可以大大降低海水淡化的成本,基本停止對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后一技術突破后又可以大大降低食品生產的成本。從目前的進展看,這兩項技術的突破只是時間問題。
在這些技術還沒有突破之前,還是要借助經濟學的定價理論緩解資源供應的緊張。我國能源價格低,水價低,低廉的價格沒有反映能源和水的利用所產生的“外部成本”。工業用水、農業用水和生活用水的過低價格是水資源浪費的主要原因。不同地區應該有不同的用水價格,差價應該大到足以吸引工商投資和人口向水資源豐腴地方流動的程度。國家的稅收制度應該支持合理資源價格的形成。
在結束本文時,我又在想一個老問題。既然“儒學計劃經濟”沒有任何可稱道的學理支撐,為什么還有人要堅持這樣一種“學術”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