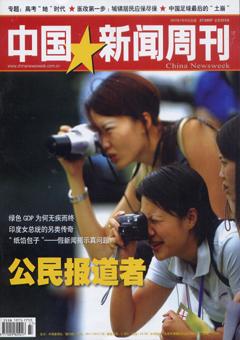醫改第一步 城鎮居民應保盡保
楊中旭
作為醫改方案制訂工程啟動以來第一個有意義的變革,城鎮居民基本醫保試點將為醫改前行累積動力
繼“新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之后,“全民醫保”邁出了堅實的第二步。7月23日,全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會并頒布《國務院關于開展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這標志著始于1998年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范圍正式擴展到城鎮居民。
轉眼之間,多部委醫改協調小組成立已近一年。作為醫改方案制訂工程啟動以來第一個有意義的變革,城鎮居民基本醫保試點將為醫改前行累積動力。
醫保框架趨完整
7月16日,周一,住在北京市西城區三塔社區18號樓的劉女士下班回家時發現,樓門口貼上了展覽路街道社保所的通知:城鎮居民中無醫療保障的老年人(男年滿60周歲,女年滿50周歲)和非在校少年兒童參加大病醫療保險,7月16日到8月20日于社區居委會辦理申請登記參保手續。
在做了整整兩天研究、兩次撥打北京市社保咨詢電話12333之后,劉女士替5歲的兒子做了參保登記。按照北京市政府2007年11號文件和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2007年95號文件的規定,她的兒子每年參保繳費50元,財政補助50元。
“你問我社區究竟有多少人有資格參加這一輪的醫保,我回答不上來,現在也沒工夫統計,到8月20號就能清楚了。”三塔社區居委會一位陳姓工作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就在與記者說話的間隙,一位78歲的老人走進居委會領參保的3份表格。陳耐心地告訴老人如何填寫,如何到戶口所在地社保所辦理存折并往里面存上300塊錢,“如果不清楚就讓子女代勞”。隨后老人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說出自己的姓名的時候,陳迅即有了反應:“您就是寧興欽?享受低保?那您只需要存10塊錢存折工本費就行了,剩下的錢政府替您掏。”
在“致全市城鎮老年居民的一封信”中,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這樣描述如何繳費:城鎮老年人大病醫療保險基金是由個人繳費和政府補助而來的,籌資標準是每人每年1400元,您個人只需繳納300元,余下的1100元全由政府補助,也就是說,“每天繳納九毛錢,大病醫療保一年。”

在一個保險年度內,老人可享受的累積支付最高限額為7萬元,兒童為17萬元。盡管老人繳費遠較兒童為多,但其發病比率更高,綜合之下,報銷最高限額反而不及兒童為多。同樣是住院,老人能夠報六成,兒童可達七成。
在醫院的選擇上,16家A類醫院、相關專科醫院都在城鎮居民醫保涵蓋范圍之內,居民所需要選擇的3家定點醫院,均為就近就醫的社區醫院等小規模醫療機構。“這就是補需方的好處,我可以自由選擇。”剛剛為兒子辦理完參保手續的劉女士說。
盡管北京并不是此番全國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工作會議上正式啟動的試點城市,但從2004年以來,包括北京在內的很多地方已經先于中央啟動改革。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繳費數額亦有很大差異。就全國而言,中央財政將為中西部每位參保人補助20元,并要求地方財政補助不得低于20元。通盤計算,全國財政每年的最低支出為120億元左右。
據本刊了解,在6月21日于江西南昌召開的中部地區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試點吹風會上,國務院副總理吳儀代表中央正式宣布了這一標準。隨后的6月28日和7月5日,國務院又召集東部和西部省份,分別在江蘇鎮江和甘肅蘭州召開了兩次吹風會。
在東部省份吹風會上,福建省提出,考慮到福建在東部省份中較為落后,請求中央能夠考慮將福建當成中西部省份看待,當時就得到了吳儀的首肯。
吹風會上,不斷有省份提請中央增加試點城市。考慮到很多地方已經先行,中央隨后改變了每省兩個試點城市的初衷。到了7月23日會議正式召開之時,首批試點城市已經達到了79個。
與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相比,城鎮居民醫保待遇偏差。其中,后者不擁有個人賬戶,節余也就不可結轉到下一年度,平均繳費標準也較前者為低。
“醫改方案爭來爭去,只有城鎮居民這一塊因為好操作而獲得推動”,多部委醫改協調小組一位專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由于已經有了城鎮職工這一塊現成的體系,盡管也有技術難題,但總體說來,試點工作只需擴容即可”。
去年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曾經提出到2010年建成“全民醫保”的目標。根據中央計劃,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將在2008年覆蓋到全體農民,此番加入的城鎮居民試點的具體規劃是:2007年啟動,2008年擴大,2009年覆蓋到80%,2010年達標。這樣,由城鎮職工、“新農合”與城鎮居民三方組成的醫保框架已趨完整。
同時,由于試點使得醫保權重加大,改變了過去補貼供方——國有醫院的格局,意味著民營醫院只要搶得醫保這一“美人”歸,就可以在經營方面叫板國有醫院,“事實上降低了社會資本進入醫院投資領域的門檻”,多部委醫改協調小組專家說,“這在為下一步的改革累積動力”。
此前有傳聞說,醫改方案討論時,“補需方漸成主調”。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醫療保險司原副司長、中國醫保研究會副會長熊先軍在接受本刊采訪時指出,準確地講,補需方只是在本次試點中獲得確立,但在醫改方案中,補供方還是補需方,還遠未定局。
博弈“基本”
在城鎮居民基本醫保試點推進過程中,衛生部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兩大核心部委博弈的焦點在“基本”這兩個字上面。
作為大病統籌賬戶的管理方,業界一直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看作“大病保險”的代言人。此番在做城鎮居民制度設計時,社保部門再次將重點放在住院,而對門診報銷著墨甚少。
在北京市的方案中,大病醫療保險主要解決住院醫療費用,以及惡性腫瘤放射化療和化學治療、腎透析、腎移植后服抗排異藥的門診醫療費用。也就是說,高血壓、糖尿病等主要在門診就醫的大范圍疾病都未被列入門診報銷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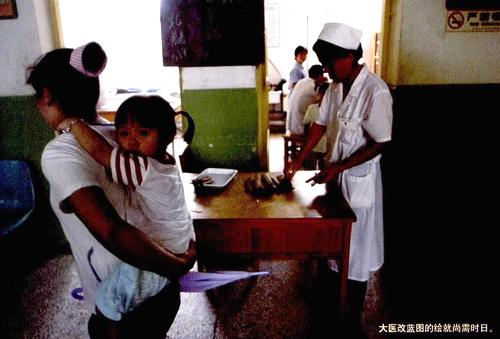
在這一問題上,衛生部繼續以前的立場,要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在制度設計時去掉“基本”二字,理由是:如果連高血壓、糖尿病這些最常見的疾病都不給保險,就稱不上“基本醫保”。
面對質疑,社保部門解釋說:“門診這一塊社保部門一定會管,現在暫時先由地方自行規定。全管起來需要一個過程,改革是要逐步推進的。”
社保部門堅持留用“基本”二字的背后,是因為“社保部門知道,如果這一次不寫進去‘基本這兩個字,門診那一塊就要被衛生部門拿走了”,多部委醫改協調小組專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社保部門只有守住這兩個字,才有可能在未來改革深入時繼續獨家持有城鎮醫保管理的權力。”
由于在就醫方面患者與醫護人員之間
具備天然的信息不對稱,從世界范圍來看,只有衛生部門才能從專業角度防止院方的逐利醫保傾向。但在1998年中國政府機構精簡的制度設計中,出于平衡部門利益的需要,城鎮醫保管理權被授予了勞動和社會保障部。
多年來,社保部門花費巨大精力,聘請醫護專業人員審核醫保報銷項目,“實際上,社保部門管不了也管不好。”社保部門人士對本刊說。
除了圍繞管理權的博弈,此番試點尚有兩處未盡完善之處,計劃外大學生和農民工兩部分群體成為改革的邊緣人。
學生群體中,中小學在校學生由學校出面保險,計劃內大學生享受國家公費醫療政策,惟有計劃外大學生,此番連待遇最低的城鎮居民這趟末班車都沒有趕上。在進行制度設計時,社保部門曾經設想將計劃外大學生納入保險范圍,但遭到教育部門反對。
另外,由于各地對農民工政策不一,農民工這一群體中,存在著參加城鎮職工、城鎮居民、新農合、無保險四種類型。考慮到地方差異非常大,此番試點同樣將權力下放給了地方。
廣義醫改方案還在制訂
本來,衛生部門負責的社區試點與社保部門負責的城鎮居民醫保試點一直在同時推進,此番后者脫穎而出,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中央可能已經意識到社區試點欠缺可操作性——如果兩者繼續并行,將造成在一個國家內存在3套醫保支付系統的情況。如果說“新農合”支付系統存在的客觀現實是城鄉二元體制,在城鎮存在兩套不同的支付系統,在世界各國的醫改實踐中沒有先例。
“我想提醒你注意,此醫改(城鎮居民醫保試點)非彼醫改”,中國醫療保險研究會副會長、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醫保司原副司長熊先軍對本刊記者說,“一個廣義的醫改包括了三方面的內容:上游的藥品流通體制改革、中游的醫療體制改革、下游的醫保體制改革。其中,上游和下游的改革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總體框架已經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匹配,惟有中游體制,還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
“重要的是將醫院納入市場經濟體制的管理框架內,醫生可以自由流動,從而盤活三級衛生資源。”勞動保障部門的官員告訴本刊。
去年9月多部委醫改協調小組成立之時,并未在上、中、下游方面突出改革重點,而是將三者混成大鍋飯。熊先軍明確表示,重點不突出正是此輪醫改方案遲遲不能出臺的根源。
“在醫療體制改革中,社保部門能夠配合做的事情,就是醫護人員背后的福利制度如何轉軌”,熊先軍說,“當初文化體制改革時,文化部門把社保部門的很多個司都請去研究,包括養老司、工資司和醫保司都在內,這才叫整體設計”。相形之下,多部委醫改協調小組中,社保部門只有醫保司參與,改革從最初的組織架構上就是一只跛腳鴨。
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解放軍總醫院原院長朱士俊從組織架構方面給出了具體的制度設計:為最大限度地回避部門紛爭,保障民眾利益,建議國務院成立專門的醫療改革委員會,“否則就是按下葫蘆起了瓢”。
在思路和組織架構都未能清晰的背景下,已經醞釀了將近一年的醫改方案仍未出爐。
從去年9月多部委醫改協調小組成立,到今年元月確定6家學術機構代為起草醫改方案的4個月內,衛生部與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就各自方案爭得難分難解。衛生部堅持補供方,提出了“兩層構架、雙重保障”的社區衛生體系建設方案,財政總投入初步估算為2690億人民幣,而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堅持補需方,堅稱“只需盤活醫院存量,幾百億即可解決問題”。
學術機構接手4個月之后,方案評審會于5月28、29日在北京市懷柔區召開,除了補需方、強調市場機制方面的呼聲略為加強之外,其他方面如醫療服務與籌資方面的分歧依舊。
身為方案評審會委員的朱士俊在會議結束之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8套方案中,尚無一套方案提交了醫院改革總體框架的研究報告。
此外,由于多部委醫改協調小組分別與9家機構簽署了保密協議,至今尚無完整方案披露。據本刊了解,方案中更多持有政府主導立場、補貼供方的方案還包括復旦大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衛生組織,而其他學術機構則更為側重補貼需方。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學、世衛組織、中國人民大學的方案頗有“騎墻派”的味道,即對供需雙方都補貼。
現在距離2008年“兩會”只剩下7個月左右的時間,5年一度的中央機構改革方案也已在制定中。從時間上看,上述機構改革方案到今日尚未定局,也就很難在未來5年內理順管理權限上的邏輯。
“歸根結底,還是改革的動力在現階段小于阻力”,熊先軍說,“好在上游和下游的改革越徹底,越能顯示出中游改革的滯后。等到明年大家繼續感覺到‘看病難、看病貴的狀況仍然未有緩解,就會明白改革的欠賬到底在哪個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