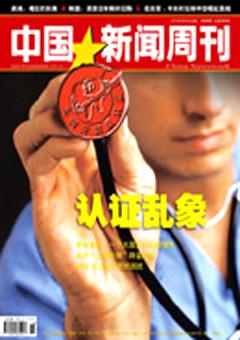凌志軍:中關村反映了中國崛起的真相
李 楊
“中關村的歷史和中國的發展是合拍的,所以我才有興趣寫它”
《人民日報》資深記者凌志軍近日出版新書《中國的新革命》。
書的副標題是“1980—2006年,從中關村到中國社會”。由此可見,這本書是通過描寫中關村的發展反映中國社會的變遷。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我將著眼于整個國家的大歷史”,只不過這次凌志軍“選擇的樣本是中關村”。
凌志軍最初被公眾認識,是因為1998年他和同事馬立誠合作出版了《交鋒》。這本記錄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的政論著作,發行量超過200萬冊。此后凌志軍繼續時政寫作,2003年出版《變化》一書再度引起反響。
在將近10年的時間里,凌志軍完全沉浸于對中國變革的描繪中。他勤奮地記錄下自己看到的每一個細節,并不斷把它們加入自己的寫作框架之中。
因此有人稱他為“時政作家”,可凌志軍本人卻強調自己是個記者。他說,“我并不期望本書的描述能和中關村的正史合拍,那是歷史學家的事。我本人的職業是記者,對于人物和事件的取舍,更多的是出于記者的本能。”
凌志軍說,他的創作風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威廉?曼徹斯特《光榮與夢想》一書的影響。曼徹斯特最大的特點是采用實錄的手法,使讀者知道“在什么樣的時間條件下會發生什么樣的事情”。而凌志軍效仿的恰恰是這一點,他把中關村的人物、企業及社會變化放在中國轉型的大格局中。
在凌志軍看來,中關村是中國改革的一個縮影:“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這個國家打碎了精神枷鎖,戰勝了饑餓,又讓自己成為全世界最龐大的‘制造車間。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術的高地,把‘中國制造變成‘中國創造”。“中關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為它是這條道路上的先行者。”
“中關村在創新之路上蹣跚而行的曲折歷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國崛起的真相。”凌志軍在書的前言中寫道,“這包括它的陽光和陰暗,包括它的英明之舉和愚蠢行為,也包括它的混亂和秩序。”
在對中關村做系統研究之前,凌志軍先后跟蹤了坐落在中關村的“微軟”“聯想”兩家企業,并創作了《追隨智慧》和《聯想風云》。盡管有人說這兩本書“有點商業意味”,但并未影響人們對這本關于中關村的新書的關注。
就在書稿剛剛完成之際,凌志軍被查出患有重病。近日,本刊記者專訪了病中的凌志軍。
民間力量的崛起
中國新聞周刊:為什么選擇中關村?
凌志軍:中關村延續至今,跨越我們國家全部改革歷程。同時我意識到,我所看到的中關村的一些事情為公眾所不知,而公開輿論中很多深入人心的東西,又與它的本來面目相去甚遠。于是我便生出一個念頭,想把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梳理清楚。
中關村作為科學城事實上從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了,但我寫的中關村是改革開放以后的20多年。它的這段歷史與中國的發展是合拍的,所以我才有興趣寫它。這段歷史就是中國新的意識形態、經濟形態乃至技術運作模式得到承認和支持的過程,也是民間力量成長起來的過程。
中關村是中國任何一個地方無法比擬的。它的人物太多:富人和窮人、博士和文盲、外來人和本地人、高官顯貴和三教九流,都能在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有機會在這里譜寫精彩篇章。它的事件紛繁復雜:經濟問題、政治問題、技術問題、環境問題、社會問題、文化問題、傳統問題、意識形態問題、人的本性問題,每個故事的結局都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然而最重要的是,它的故事還在繼續,所有人物都是“進行時”。
中國新聞周刊:在這段歷史中,中關村最具價值的東西是什么?
凌志軍:很多人認為,科技是中關村的最大特色。但我不這么看,與其說中關村在技術上有什么貢獻,不如說中關村最大的貢獻,在于對舊體制的破壞和突破,從而激醒了中國人創造財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熱望。中關村的意義在于,它試驗著新的社會思想和價值取向。
有時候我覺得中關村更像一個技術中轉站,有模仿,也少不了盜版,但在某些枝節領域開始了自己的創造,這與中國的發展是一樣的。比如服裝、家電、汽車等領域都走過了從模仿到原創的過程。技術含量越高,這個過程就越長。中關村走的就是這樣一條路,所以說它是先行者。
必須指出的是,單就技術而言,中國很少在哪個領域是領先的,但這并不妨礙別人承認中國的崛起。這是因為在中國,新的人、新的思想、新的體制、新的制度漸漸得到公認,并成為社會主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有幾個地方民間力量生長非常快。比如溫州,上世紀80年代初期溫州的民間力量在農村和小城鎮的商業中崛起。在中關村,則是城市科技人員這股民間力量的崛起。經過20多年,今天人們對民間力量、民間資本的態度已經完全不同了。
“跟隨戰略”的傳奇
中國新聞周刊:有人說中關村是騙出來的,存在信用危機,有人說中關村“長不大”,創新能力不強。對于這些針對中關村的爭議,你怎么看?
凌志軍:其實中關村問題的根源發生在中關村之外,我認為它的一切都與中國的現實合拍。比如盜版問題,中關村的盜版歷來就有,90年代達到高峰,今天還有,但好了很多,聯想已經大批購買微軟的操作系統了。這個過程基本上是和國家大形勢連在一起的。
我認為,創新和模仿不能完全分開。我們國家在很多方面都既包含了模仿也包含了創新,經過了一個先購買、后模仿的過程。
迄今為止,中國市場上大部分新產品,從轎車到電熨斗,都包含了這樣兩個過程。學者將其稱之為“跟隨戰略”,官方的通行說法是“引進先進技術”和“國產化。”從某種程度上說,“跟隨戰略”所發揮的作用,是中國崛起的最大傳奇。中關村就是這樣一個傳奇。
其實,有時模仿比創新更有利。有經濟學家指出,創新的成本是模仿的4倍。一個國家要想領先就要付出更大的成本,這也是很少有哪個國家能永遠領先的原因。目前有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跟隨戰略很成功,8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90年代東亞一些國家的崛起,以及中國20多年來的發展,都是跟隨戰略的成功。
中國新聞周刊:中關村的發展主要是政府驅動還是市場驅動?它的內在推動力是什么?
凌志軍:我認為民間力量正在成為主導力量。中關村發展早期,政府基本沒有介入,后來有一段時間政府介入比較多,主要集中在市政建設上,比如修路架橋。就對企業的管理而言,政府基本不管。
在我接觸的政府官員中,中關村管委會政府職能轉變是比較好的。主要原因是它沒有多大的權力,不像其他政府部門一樣擁有各種審批權。所以它存在的職能主要是服務。
創新是中關村崛起的內在推動力。我說的這個創新不是技術創新,而是商業制度的創新、資本制度的創新、人才制度的創新。中關村最擅長的就是把一種技術拿來,通過商業創新實現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