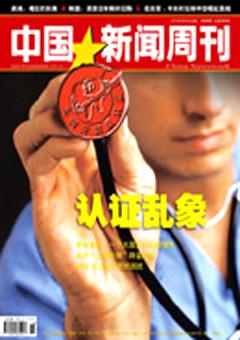爭(zhēng)議中關(guān)村
李 楊
中關(guān)村自誕生之日起就飽受爭(zhēng)議,只不過(guò)凌志軍的新書再次把這些爭(zhēng)議推到了公眾面前。其中兩個(gè)焦點(diǎn)是:中關(guān)村的發(fā)展模式該不該以經(jīng)濟(jì)總量為目的;對(duì)“一條街”的房地產(chǎn)開發(fā)是不是破壞了中關(guān)村的原生活力
媒體近日披露了一則北京市官員落馬的消息。新聞主角是中關(guān)村的“父母官”——北京市海淀區(qū)區(qū)長(zhǎng)周良洛。據(jù)《財(cái)經(jīng)》雜志報(bào)道,周是在有關(guān)部門查辦北京地產(chǎn)商人劉軍案時(shí)被牽出的。巧合的是,劉軍去年夏天案發(fā),是因北京市原副市長(zhǎng)劉志華案。而劉志華被調(diào)查前除擔(dān)任副市長(zhǎng)外,還兼任中關(guān)村管委會(huì)主任。
兩位中關(guān)村的主要領(lǐng)導(dǎo)相繼落馬,在科技園區(qū)引起不小震動(dòng),也給中關(guān)村的發(fā)展蒙上了一層陰影。一位不愿具名的中關(guān)村創(chuàng)業(yè)者對(duì)本刊說(shuō),“政府官員的營(yíng)私、腐敗,以及權(quán)力介入市場(chǎng),損害了中關(guān)村公平競(jìng)爭(zhēng)的規(guī)則。”
兩本針鋒相對(duì)的書
事實(shí)上,中關(guān)村自誕生之日起就飽受爭(zhēng)議,只不過(guò)凌志軍的新書再次把這些爭(zhēng)議推到了公眾面前。
迄今為止,敘述中關(guān)村的書籍很多,但真正對(duì)這一區(qū)域做系統(tǒng)梳理和評(píng)論的只有兩本。一本是凌志軍的《中國(guó)的新革命》,另一本是“互聯(lián)網(wǎng)實(shí)驗(yàn)室”和“博客中國(guó)”網(wǎng)站負(fù)責(zé)人方興東的《中關(guān)村失落》。從書名不難看出,凌、方二人對(duì)中關(guān)村做出的結(jié)論是相反的,一個(gè)認(rèn)為它代表著一場(chǎng)方興未艾的“新革命”,而另一個(gè)則認(rèn)為它已經(jīng)“失落”了。
凌志軍說(shuō),他并不認(rèn)為中關(guān)村的發(fā)展是光明一片,其中也有“陰暗和混亂”,但他堅(jiān)信中關(guān)村發(fā)展的主線是上揚(yáng)的,是充滿生機(jī)的。這一觀點(diǎn)可以從下面的故事得到佐證。
2005年的一天,凌志軍來(lái)到位于中關(guān)村的清華創(chuàng)業(yè)園A座302房。在這里,他看到了一間裝著38家公司的屋子。“每家公司只不過(guò)占有其中一個(gè)方格,由一張簡(jiǎn)易電腦臺(tái)和一把轉(zhuǎn)椅組成,和大公司里那種員工座位沒(méi)有什么差別,只不過(guò),在通常鑲嵌員工姓名的地方貼著公司名稱……他們是老板、會(huì)計(jì),還是自己公司惟一的員工。只要花500塊錢就可以在這里坐一個(gè)月,而他們?cè)谶@里的時(shí)間通常不會(huì)超過(guò)半年。”“很多人失敗了,但總會(huì)有人成長(zhǎng)起來(lái),擴(kuò)大隊(duì)伍,搬到樓上。那里有單間辦公室,沿著走廊排列,是為他們這些人準(zhǔn)備的……12個(gè)月、也許18個(gè)月之后,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會(huì)垮臺(tái),但必定有幾家繼續(xù)成長(zhǎng),搬到更大的寫字樓去,占據(jù)整整一層。”
凌志軍把這個(gè)故事放在了書的前言中,足見(jiàn)這個(gè)場(chǎng)面對(duì)他震撼之大。“所有這些構(gòu)成了中關(guān)村的故事,也成為這個(gè)國(guó)家歷史的一部分。”
《中關(guān)村失落》出版于2004年8月。這本書的核心觀點(diǎn)是:中關(guān)村已經(jīng)不再是中國(guó)高科技創(chuàng)新的中心,中關(guān)村已經(jīng)無(wú)力領(lǐng)導(dǎo)中國(guó)的高科技走向。“近3年過(guò)去了,”方興東接受本刊采訪時(shí)強(qiáng)調(diào),“我對(duì)中關(guān)村的這一基本看法并未因時(shí)間推移而改變。”
“我說(shuō)的中關(guān)村失落,并不是說(shuō)中關(guān)村完全喪失了自己的優(yōu)勢(shì)。畢竟這么多年的積累,這么多高校、科研院所聚集在這里,要想找出幾家好公司來(lái)并不難。”方興東說(shuō),“我說(shuō)的失落指的是,中關(guān)村在中國(guó)高科技產(chǎn)業(yè)的格局中喪失了中心地位和領(lǐng)導(dǎo)地位。”
讓方興東做出上述判斷的理由很多,以互聯(lián)網(wǎng)為例,2003年底以來(lái),互聯(lián)網(wǎng)走過(guò)“冬天”開始回暖,進(jìn)入新一輪黃金時(shí)期。攜程、靈通、盛大、騰訊、搜房、百度、TOM、慧聰、阿里巴巴、e龍等網(wǎng)站相繼在美國(guó)納斯達(dá)克上市。“然而,除慧聰和百度,其他網(wǎng)站幾乎都與中關(guān)村不沾邊。”方興東說(shuō),除此之外,在硬件、軟件和通訊等領(lǐng)域,中關(guān)村也眼睜睜地失去了領(lǐng)導(dǎo)權(quán)。
“我認(rèn)為形勢(shì)非常嚴(yán)峻。”方興東說(shuō),90年代,中關(guān)村的優(yōu)勢(shì)是絕對(duì)的。但這幾年,隨著上海、深圳、杭州、武漢等地在高科技領(lǐng)域崛起的勢(shì)頭不斷上揚(yáng),中關(guān)村的領(lǐng)導(dǎo)地位正在逐步喪失。
早期中關(guān)村:民間推著政府走
雖然凌志軍和方興東觀點(diǎn)針鋒相對(duì),但兩人對(duì)中關(guān)村前期的發(fā)展,具體說(shuō)就是上世紀(jì)八九十年代的興起,則沒(méi)有分歧。1980年10月,以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員陳春先為首的幾個(gè)科技人員,成立了“等離子學(xué)會(huì)先進(jìn)技術(shù)發(fā)展服務(wù)部”,以一種準(zhǔn)企業(yè)的方式嘗試科技成果直接轉(zhuǎn)化為社會(huì)生產(chǎn)力。1983年,服務(wù)部發(fā)展成“北京華夏新技術(shù)研究所”,其實(shí)是我國(guó)第一家民營(yíng)科技企業(yè)。此后,中關(guān)村的科技企業(yè)、科技成果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出來(lái)。
凌志軍強(qiáng)調(diào),80年代中關(guān)村的公司群和商業(yè)體系,是在政府管制的縫隙和漏洞中創(chuàng)建起來(lái)的,與70年代末期安徽小崗村農(nóng)民發(fā)動(dòng)的“革命”如出一轍。這里的每一個(gè)進(jìn)步,并非政府率領(lǐng)民間向前走,而是民間推著政府向前走。
中關(guān)村當(dāng)年備受爭(zhēng)議的還有當(dāng)時(shí)的商業(yè)模式,而這也已成為公認(rèn)的國(guó)際慣例。“代理商—分銷商—零售商”是全球計(jì)算機(jī)產(chǎn)品銷售模式中通用的商業(yè)鏈,也是今天中關(guān)村的商業(yè)模式。但90年代初,中關(guān)村只有“批發(fā)”和“零售”兩種銷售方式,都是被動(dòng)地坐在店里等待顧客上門。1992年4月,現(xiàn)在“聯(lián)想”的領(lǐng)軍人楊元慶找到了中關(guān)村一個(gè)叫“鷺島”的小公司做自己的代理,銷售惠普公司的產(chǎn)品,讓“鷺島”分銷其代理銷售的“惠普繪圖儀”,以營(yíng)業(yè)額的3%作為回報(bào)。楊元慶的助手林楊,參照“惠普”和“聯(lián)想”的分銷協(xié)議,為“聯(lián)想”和“鷺島”起草了一份代理合同,被認(rèn)為是“中關(guān)村第一份真正意義上的代理合同”。
今天中關(guān)村:“一次性硅谷”?
目前仍然存在激烈爭(zhēng)議的是中關(guān)村2000年以后的發(fā)展模式。這時(shí),隨著政府對(duì)園區(qū)介入的逐步加深,中關(guān)村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
方興東認(rèn)為,政府犯了一個(gè)方向性錯(cuò)誤,那就是把中關(guān)村這個(gè)高科技園區(qū)當(dāng)成一個(gè)工業(yè)園區(qū)來(lái)追求經(jīng)濟(jì)總量。“以稅收為目的,以大企業(yè)為品牌。”
對(duì)于應(yīng)把中關(guān)村引向何方,政府其實(shí)心知肚明。現(xiàn)任中關(guān)村管委會(huì)主任戴衛(wèi),這位溫和而精明的官員向本刊闡述中關(guān)村的發(fā)展指標(biāo)時(shí),除強(qiáng)調(diào)“對(duì)北京市生產(chǎn)總值的貢獻(xiàn)”以外,還列出了專利數(shù)、企業(yè)研發(fā)投入、上市公司數(shù)量一大堆發(fā)展指標(biāo)。
然而方興東說(shuō),他更愿意根據(jù)實(shí)際情況做出判斷。“近10年來(lái),從土地、貸款和稅收政策看,毫無(wú)疑問(wèn),大企業(yè)得到的好處比普通創(chuàng)業(yè)者多得多。”他說(shuō),政府向大企業(yè)傾斜原因很簡(jiǎn)單,只要拉來(lái)一家年收入上百億的跨國(guó)公司,園區(qū)業(yè)績(jī)就可以輕松拔起一大截。
方興東選擇了一個(gè)參照物討論中關(guān)村問(wèn)題,那就是美國(guó)硅谷。無(wú)論在創(chuàng)業(yè)者眼中,還是在政府眼中,硅谷都是中關(guān)村的樣板。“硅谷不會(huì)因?yàn)槔瓉?lái)了哪個(gè)大公司就特別高興,不會(huì)因?yàn)槭澜?00強(qiáng)落戶于此就大肆宣傳。”方興東說(shuō)。
方興東說(shuō),硅谷是一座生生不息的活火山。上世紀(jì)60年代半導(dǎo)體產(chǎn)業(yè)初露崢嶸,硅谷推出了英特爾、AMD等企業(yè)。70年代計(jì)算機(jī)開始擴(kuò)張性增長(zhǎng),硅谷推出了蘋果、Tandem等企業(yè)。80年代個(gè)人電腦革命啟動(dòng),硅谷又推出Sun、Cisco等軟硬件企業(yè)。90年代互聯(lián)網(wǎng)熱潮中,硅谷又奉獻(xiàn)了網(wǎng)景、雅虎等企業(yè)。總之,方興東說(shuō),硅谷始終在不斷推出高成長(zhǎng)企業(yè),并成為整個(gè)國(guó)家高科技領(lǐng)域的領(lǐng)導(dǎo)力量。而中關(guān)村更像“一次性的硅谷”。
另一個(gè)關(guān)于中關(guān)村的激烈爭(zhēng)論,是圍繞大規(guī)模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展開的。
中關(guān)村近年的硬件變化可謂翻天覆地。綠蔭覆蓋下的白頤路已經(jīng)拓寬成為寬闊的中關(guān)村大街。大街兩側(cè)的電腦小商販都搬進(jìn)了玻璃幕墻的海龍大廈、硅谷電腦城和太平洋大廈。占地51公頃的“中關(guān)村西區(qū)”變成了一個(gè)“城中之城”。
中關(guān)村安靜了,干凈了,漂亮了,但門檻也高了,“草根”們漸次退出,活力正在減弱。一位名叫王緝慈的北京大學(xué)教授對(duì)這種“高大整齊”的形式并不以為然。本刊記者至今仍清楚地記得,2002年,剛從美國(guó)回來(lái)的她,看到中關(guān)村大興土木后不解地說(shuō)了一句英文:“What are they doing now?”(他們?cè)诟墒裁矗?她還上書當(dāng)時(shí)的北京市領(lǐng)導(dǎo),指出“如此重大決策是倉(cāng)促的”。
方興東尖銳地指出,“房地產(chǎn)的開發(fā),把這片土地持續(xù)發(fā)展的資源一次性兌現(xiàn)、一次性開采,結(jié)果是破壞了草根崛起、成本很低的蓬蓬勃勃的市場(chǎng)生態(tài)。”
王志東曾對(duì)記者回憶起80年代末的中關(guān)村,感慨萬(wàn)千。“那時(shí)的中關(guān)村大街上,狹小熱鬧的門臉摩肩接踵,感覺(jué)中關(guān)村離世界很近。世界上386剛出來(lái),中關(guān)村的386也出來(lái)了;然后美國(guó)開始搞網(wǎng)絡(luò),中關(guān)村也有網(wǎng)絡(luò)了。不夸張地說(shuō),到中關(guān)村轉(zhuǎn)一圈,就知道世界上的新東西了。”相形之下,王志東對(duì)于今天的中關(guān)村悵然若失,“現(xiàn)在一說(shuō)中關(guān)村,最先想到的是海龍、太平洋等電腦配件市場(chǎng)。我不希望中關(guān)村成為歷史。”
方興東認(rèn)為,房地產(chǎn)的開發(fā)破壞了中關(guān)村的市場(chǎng)生態(tài),使中關(guān)村喪失了獨(dú)特的市場(chǎng)敏感度。“正是當(dāng)時(shí)這個(gè)外表一點(diǎn)不美好的市場(chǎng),匯聚了中國(guó)IT業(yè)軟硬件廠商,匯聚了生產(chǎn)制造、研究開發(fā)、倒買倒賣的各路上下游廠商,并輻射到全國(guó)各地。”
方興東還為中關(guān)村選擇了另一個(gè)參照物——浙江義烏。他說(shuō),中關(guān)村和義烏的起步非常相象。但義烏的產(chǎn)業(yè)鏈?zhǔn)冀K沒(méi)有中斷,雪球效應(yīng)越來(lái)越明顯,而且不斷升級(jí),現(xiàn)在不僅是中國(guó)的義烏,還是世界的義烏。“成功的經(jīng)驗(yàn)是什么?”方興東自問(wèn)自答:“就是政府的無(wú)為而治和純粹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
“如果到最后,在中關(guān)村寬敞明亮的大樓里,住的都是利用我們高素質(zhì)的人才為其打工的外國(guó)機(jī)構(gòu),你說(shuō)我們到底是中關(guān)村的罪人,還是功臣?”早在2003年,有四通元老、“中關(guān)村村長(zhǎng)”之稱的段永基就曾反問(wèn)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