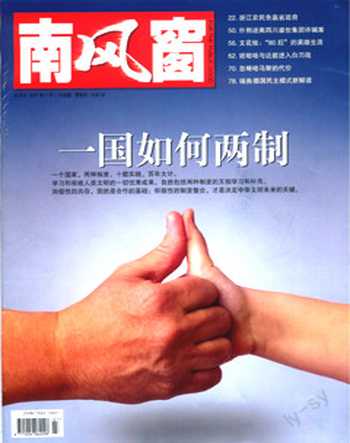區域經濟合作的香港樣本
袁易明
香港回歸既承載著在社會制度上一國兩制偉大戰略構想的實現: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又承載著兩種類別經濟制度的并存:香港充分自由的市場制度和內地的轉型經濟制度。
在回歸后的相當長時間里,實現平穩過渡、維持香港穩定是中心議題,其后5年,關于促進香港的繁榮又成為討論的焦點。
對內地而言,香港回歸給國人帶來政治上的自豪感,這是政治收益;在經濟上,內地同樣分享了合作創造出的利益。香港對于內地發展有三大貢獻:體制貢獻,為內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提供借鑒與啟迪;要素貢獻,大量港資北上減低內地發展過程的資本約束;溝通貢獻,搭起內地與國際間雙向交流的橋梁。這三大貢獻是回歸后兩地共同繁榮的根本理由,也是香港保持穩定繁榮的重要基礎。
制度差異意味著機會
在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經濟區域化趨勢的基本背景里,世界上產生了兩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典型案例:一個是出現在歐洲大陸的歐盟,另一個就是中國境內羅湖橋連結的香港與內地之間。
歐盟可以稱得上區域經濟合作的一個完美的例證。在眾多不同經濟體和不同政治體之間建立起來的歐盟,其一體化程度遠超人們原來的預期。經濟方面,成員之間不論是微觀經濟領域,還是宏觀經濟的變動均已進入趨同的狀態,形成了實際利潤率的均等化,成員經濟周期已出現同步化,并實現了失業狀態的趨同和成員國間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趨同。
歐洲經濟一體化的建設過程經歷了處于不同層次的兩個階段:功能一體化和制度一體化。功能一體化過程消除不同經濟體之間的市場阻礙,經濟要素在成員國間自由流動,以實現經濟過程的融△c通過這一階段,成員國間自然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得以整合。功能一體過程中要素流動帶來任一成員國資源配置空間的擴大,共同創造出歐洲經濟的發展“紅利”。
內地與香港間的合作在世界經濟合作歷史上是一個獨特的區域經濟合作范式,其獨特意義在于一個國家內不同社會制度的兩個地區間的合作。如果說,歐洲27個國家創造了世界上制度相同,體制、機制相近,發展水平相當條件下的區域經濟合作的經典,那么,在香港和內地間的合作,則是社會迥異、經濟制度不同、發展水平懸殊條件下區域經濟合作的一個范例。
內地處于經濟體制變革轉型期,不完善的市場體制是內地經濟制度的主要特征,與香港成熟、完善而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形成強烈的制度對比,這是香港與內地10年來經濟關系深化的制度背景。另外一面,香港已經成為國際著名金融、貿易、旅游、信息大都市,其經濟發展成就舉世公認,而內地人均GDP少于香港的1/20,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稀缺,這與香港經濟形成巨大落差。
正是在制度差別和發展水平差別同時存在的背景里,香港與內地間的生產力分工迅速深化:大量香港制造業跨過羅湖橋北上,其本質內涵是資本、管理和一般性生產技術的由南到北,其間,數百億、上千億資金的跨境移動是引領力量。香港本土制造業平均資本收益率已大為降低和資本融資成本小是香港資本移動的兩個前提性因素,相反的是,即使在毗鄰的深圳,由于發展初期資本要素的嚴重匱乏(相對地,勞動力和土地極為豐富),使得資本要素的邊際收益率很高,在經過從香港到深圳的短距離遷徙之后,香港資本就實現了從低收益率向高收益率的轉換,同時,內地資本在短期內的大量增多大幅度地提升了土地和勞動力兩個要素的生產率,內地創造財富的能力快速起步,在內地與香港間開始出現區域經濟“增長紅利”。
內地與香港間的經濟合作始于1980年代,而全面的發展和深化則是在1997年香港回歸之后。1997年以后,香港資本依然是內地外來資本的主體,在與其相鄰的廣東地區更是如此,至2003年8月的10多年時間,該省共引進海外投資1200多億美元,其中約825多億美元來自香港。要素的北移,極大地擴大了香港產業的生存空間,形成香港經濟對內地區域性資源的調配能力,同時通過其“橋梁”角色,提升香港調配國際資源的能力。
市場力量—直是兩地合作的主體力量。值得注意的是,雙方自發合作開啟之時,已經擁有了一個必要的前提,即內地改革與開放方略的實施。這一前提為香港要素進入內地開啟了大門,雖然如此,兩地之間的以制度安排作為協調合作主要途徑的局面始終未出現過。
在兩地產業合作開始的前幾年間,得先機的深圳和廣東省就取得過很高的經濟增長成績。而香港分享的合作效益也大得驚人,數百億美元的港資獲得豐厚的回報,更有意義的是,香港產業獲得歷史上罕有的升級轉換機遇,為在新的發展階段里使香港在全球保持強勁競爭力準備了“伏筆”。
制度性整合決定未來
制度整合是區域經濟合作過程中各參與方之間的體制與機制的協調過程。
正如丁伯根所言,區域經濟一體化存在著消極一體化與積極一體化兩種類別:在區域貿易自由化過程中產生的,只涉及消除歧視與流通限制等方面的經濟整合是消極經濟整合;在此基礎上發生的通過修訂已有法律與機構和設置新的法律與機構,以保障市場的有效運行和集團內宏觀政策目標的實現的整合,被丁伯根定義為積極整合。
要真正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需要在合作形態上實現由消極整合到積極整合的升級,并且完成積極整合過程,只有這樣才可以出現經濟政策趨同和經濟發展的趨同,由此充分地挖掘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的兩種效率:市場擴大產生的規模效率和來自制度整合后的制度協同效率,以推動區域經濟持續繁榮。
香港與內地的一體化進程已經完成了丁伯根消極整合階段,即功能整合階段,在近30年的合作之后,合作形態依然止步于功能整合。現實看來,兩地間功能整合的空間已相當有限,兩地的體制、機制間的差別已經成為繼續推進一體化進程的約束因素,這表現在:高度自由而成熟的香港經濟體制與建設中的內地不完善的市場體制(框架)相對應,形成兩地對合作推進主體在認識上的差異;兩地產業發展過程中的規范、標準不同,局部地損害兩地產業合作的范圍與深度;制度原因導致兩地人口的非對稱性流動——香港居民的自由流動和內地居民的管制流動;管理的協調不足使得海關兩地兩檢長期存在,大幅增加區域內的交易成本等。
基于現有的合作框架與協調機制,香港與內地間的制度整合可以起步于三大內容:建立特定的兩地一體化組織與管理機構,以彌補常規管理的缺失,強化現有的協調機制(如泛珠三角合作框架、粵港聯席會議等);修訂兩地的不利于合作的規定、規章、政策;促進原來民間的分離、游離交流形態向組織化轉變,建立有效的產業間、行業間的一體化機制,促進產業發展規范、產品標準的趨同化。
在這之上最為重要的當屬加快內地市場經濟體制建設與完善步伐,只有當兩地的市場制度差別已大幅度減少,兩地貨物、人員、服務、資本的流動自由而充分時,兩地產業分工才會高度深化,基于兩地比較優勢的內地與香港、深港經濟共同體才會出現,“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與華南地區才有成為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區域的可能。
(作者為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