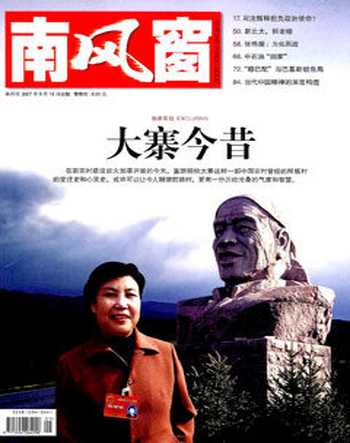“專項整治”常規化反思
王大鵬
“專項整治”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是一個人們再熟悉不過的詞語了,大到國務院,小到一個單位,無論是涉及國計民生的食品安全,還是網絡游戲中的外掛私服,我們都能夠看到“專項整治”的身影。
所謂專項整治,是政府出于整治某種市場行為、某個行業或者突出的社會問題的需要,由一個主管部門,更多的是聯合多個部門,集中執法人力、設備、資源,在較短時間內從重、從快地進行聲勢浩大的行政檢查、執法處罰行動。
過去幾年,全國性的專項整治已經出現相對密集的特點,近期開始的房地產交易秩序專項整治、交通部“兩防”專項整治、信息產業部的電信收費專項整治、環保總局的造紙行業排污專項整治、民航總局的安全專項整治外,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專項整治、安全生產專項整治,過去幾年每年都開展過。其中,食品安全專項整治雖然進行過幾次,但今年形勢格外嚴峻,國務院專門成立食品質量和食品安全領導小組,進行為期4個月的專項整治。像教育亂收費、涉農收費幾乎是年年進行專項整治。又比如公安部,在一段時期酒后駕車現象十分突出的時候,也進行過酒后駕車專項整治。
除了全國性的專項整治項目,以及地方政府配合中央政府專項整治的行動以外,各級各地區政府都開展了名目繁多、涉及各領域的專項整治,從最直接的衣食住行到虛擬世界,幾乎沒有一個領域不能夠被納入專項整治的范圍中去。冬季來臨,可能就來一次冬季供熱專項整治;某個幼兒園發生治安事件,可能就來一次幼兒園周邊安全秩序專項整治;某個行業稅收征收工作困難,可能就來一次稅收專項整治;旅游旺季到了,可能就來一次市場秩序專項整治,如此等等。如果簡單搜索,專項整治名目就可以羅列上百種。
頻頻出現于各大媒體并與“專項治理”具有家族類似的詞,還有“嚴打”、“突擊整治”、“集中整頓”、“拉網式排查”等。通過這些詞匯,不難看出,專項治理的產生都源于突出的社會經濟問題,問題導向是所有專項治理的本質屬性。在專項整治活動中,政府在短期內最大限度地動用行政管理資源,采取疾風驟雨般的執法方式,雷聲大,雨點也大,相關的宣傳鋪天蓋地,相關的行動轟轟烈烈,其運動性特征顯而易見,具有“運動式”治理的性質。這樣一種本來是作為應急手段的治理方式,緣何成為一種近乎常態的治理行為?
效力的邊界
從專項整治的實際工作看,其內容絕非是日常工作的擴大化,使用的手段又都是常規的行政手段,并沒有使用非常規的強制措施。
但專項整治能夠獲得短期內的明顯效果,是因為對行政資源集中使用,施政目標具有明確的時間限制,責任追究也相對嚴厲。其效力也正是來自于非常規性。
在專項整治過程中,治理主體為了盡可能地達到治理目標,會調用社會上一切具有執法職能的政治權力資源對治理客體進行強力治理。專項整治具有打擊力度大、成果顯效快的優勢,可以在維護社會經濟秩序、打擊違法行為方面獲取短期的收益,并內在包含行政處罰的規模效應,迎合了公共治理的現實需求。毫無疑問,在這種情況下,專項整治的進度大大快手別的治理方式,治理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

因為專項整治是為了達到某種特定的目標而發動的,因此,主管部門一般希望在盡可能短的時間里快速地解決存在的疑難問題或突發性事件。專項整治在經濟學上被稱之為矩陣式社會管理方式,這樣的管理方式成本是非常高的。專項整治的時間越長,成本就會越高。甚至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在專項整治過程中,由于時間短、任務重、人員多、細節密等因素的存在,導致開支的核算和運用監管有相當大的難處。特別是在—刀切的治理過程中,資金的調撥主要是運用行政調撥的方式,這就更加導致資金監管的難度加大。在實施治理的過程當中,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借雞生蛋、虛報瞞報的各種撈取國家資財的行為,導致治理成本的虛高。
基于投入產出的經濟因素的考慮,主管部門就會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結束專項整治過程。—旦專項整治行動達到預期的目的,主管部門就會立即退出專項整治過程。但專項整治短期內的有效性,可能會促使官員反復使用這種治理手段。在有些地方,進行過多少次專項整治,已經是表達工作成績的重要內容。對治理對象而言。一次專項整治之后,也可能會反彈。
專項整治結果的反彈指在治理結束后,專項整治的客體又重復出現甚至出現程度更加劇烈或嚴重的癥狀的一種現象,從而形成—種惡性循環。因此,時間的短期性決定了專項整治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治理方式,沒有從源頭上杜絕治理客體再生的根源,治理客體一有機會就會再生,導致治理客體的反復出現。也這是一般的專項整治的工作部署中,都會強調與建立長效機制結合起來的原因。
專項整治與運動式治理
那么,在當下的中國,為什么作為一種非常規手段的專項整治會有常規化的趨勢呢?
美國學者詹姆斯·湯森等人認為,自從毛澤東逝世后,中國面臨著一種制度化運動的悖論,即改革意味著中國生活的常規化,但它卻是以動員的方式進行的。這種“制度化運動的悖論”,集中體現了中國政治發展與國家治理過程中管理常規化與制度理性化的困境。“專項整治”就是轉型中國在面對特殊的社會形勢,通過對行政資源的再調配,集中力量解決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突出的社會經濟問題的一種運動式治理活動。
“運動式治理”是傳統社會主義時代中國最常見的—種國家治理方式,這種國家治理方式以執政黨在革命戰爭年代獲取的強大政治合法性為基礎和依托,通過執政黨和國家官僚組織有效的意識形態宣傳和超強的組織網絡滲透,以發動群眾為主要手段,在政治動員中集中與組織社會資源以實現國家的各種治理目的,進而達成國家的各項治理任務。在轉型中國,這種運動式治理中的核心要素——政治動員與意識形態宣傳都是在國家治理能力欠發展的基本前提下,對國家治理能力的一些外部救濟和邊際改善措施。
在轉型中國,原有的動員體系日益弱化,社會與單位調控體系日益出現裂縫,權威性資源的流失是一個較為明顯的現象。雖然改革開放導致配置性資源大幅度增加,國家治理的技術性基礎設施大大增強,但是就社會資源總量而言,國家治理資源的貧弱仍將是一個長期的歷史事實。國家治理資源的匱缺導致常規化的治理體系經常運作失靈,直接損害了社會問題的治理績效。國家必須間歇性地實施“專項整治”來彌補這種結構性缺陷。“間歇性社會控制”成為轉型中國國家治理的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作為國家治理活動的“專項整治”是國家權力重要的再生產機制與再擴充機制,常態社會的“專項整治”蘊藏著中國社會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再生產機制。通過運動式治理實現國家權力的再生產與再擴充,確保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延續與維系是轉型中國國家治理的內在邏輯。
只有在國家治理資源充裕、權力的市場網絡與制度網絡完善、國家權力的后勤基礎設施發達的前提條件下,國家治理能力實現了質的飛躍后,常規化的治理才能徹底替代運動式治理,“專項整治”才可能真正退出歷史舞臺,我們才能夠對“專項治理”來一次真正的專項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