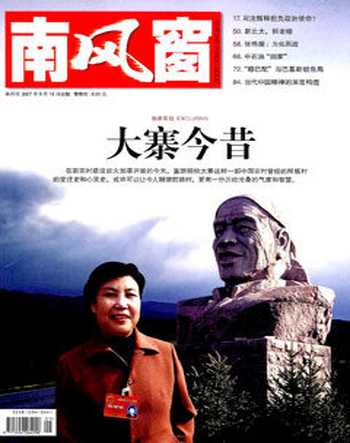商會的聲音:孤獨的博弈者
李北方
民間商會的勃興曾被認為是向以權力分立為特征的公民社會轉型的進步現象,商會某種程度上已經可以決定自己說什么、怎么說,但它是否能夠促進良性利益表達機制的建立,尚有待觀察,因為讓誰說的問題由不得它,博弈者不負責制造對手。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被媒體稱為“溫州最忙的人”,接受記者采訪時,一撥來自湖北仙桃的客人正在溫州,苦等周德文組織—些溫州企業家跟他們—道回去。
不僅我政府,還要找商會,這說明政府已經不是唯一可以組織經濟資源的力量。為企業解決發展難題,商會的確更有規模效應。比如促進會將各大銀行溫州分支機構的負責人全部聘請為副會長,共組貸審委,每年向會員企業發放兩億的貸款;促使政府出資推動建立貸款擔保體系。促進會的崛起還有一層內涵,一地之發展,常常要走各種鋼絲,僅僅由政府部門出面會有很高的道德風險,比如促進會就曾跟地下錢莊打交道,打政策的擦邊球,為資金流暫時出現問題的企業解決燃眉之急。
溫州的企業有99.9%是中小企業,平均壽命是3到4年,周德文打比方說,這些企業既不是白貓也不是黑貓,而是“野貓”。
1999年成立的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如今會員企業已達1000多家,在規模和活躍程度上都堪稱溫州的“第一大商會”。截至今年4月,溫州市共有商會400多個,其中市級商會131個。
游說
作為利益集團的一種,商會通過游說影響資源的分配是正常的,中外概莫如此,但方式卻有明顯的不同。政治生活中的游說,在英文中對應Lobby一詞,Lobby原指英國議會大廈中的一個面積并不算大的大廳,在這里,個人或利益集團的代表約見議員當面交流,或者將書面意見留給工作人員轉交給民意代表,通過將意見反映給議員來影響立法。
但在中國當下的政治體制中,游說的含義顯然不同于Lobby。首先,行政機關在政策制定和落實執行中占據主動;其次,作為利益集團的商會的代言人本身就具有民意代表的身份,商會并非通過影響民意代表來影響決策,而是直接使用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身份來爭取利益。

以周德文為例,作為民進溫州市委的副主委,他先后擔任了溫州市政協常委和人大代表。周德文向記者總結了為中小企業爭取利益的三種方式:一、通過向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的主管部門溫州市經貿委的領導定期匯報工作(每年三到四次),反映中小企業的呼聲:二、通過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身份參政議政,與政府相關部門進行交涉,對此,政府部門按規定是必須接待并予以答復的;三、通過中小企業促進會的紅頭文件向溫州的相關主管領導打報告,反映問題。
這些正規的渠道是溫州商會發揮影響力的實質性方式嗎?浙江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詩宗說,在研究溫州商會的過程中。他們從溫州的人大和政協調閱了商會遞交的提案,經過研究發現,這個渠道并不通暢,對很多提案和意見的反應和處理都是不及時的。在周德文稱為“熟人社會”的溫州,商會更多依靠的是人際關系和個人的影響力。浙江大學史晉川教授稱溫州社會為一張“不可觸摸的網”。
溫州商會一些活動常有突破常規之處。浙江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即指出,“合成革商會會員單位的環境污染、家電協會會員單位出售劣質音響、眼鏡商會會員單位未經認證擅用CE標志、家具商會會員單位違規運輸、金屬商會會員單位出售不合格鋼材等事件經有關政府職能部門查出并處以罰款,但后來經商會出面協調而輕罰或免予處罰。”
立法中的商會作用
本土的民間商會在立法過程中有參與并發表意見的機會,周德文說,2000年左右,全國人大在起草《中小企業促進法》草案時曾到溫州召開座談會,他參會并發言。至于意見在立法中起到了多大作用,周德文并沒有把握。
與之對比,外國商會通過游說等途徑影響法律的起草,一些已經在中國國家級的立法過程中發揮著相當的影響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中國美國商會(中美商會)在中國立法中發揮作用的成功案例,會長柏麥高認為首推《勞動合同法》。
在《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博弈過程中,有報道說,上海美國商會、歐盟商會等外國商會在給全國人大的建議中發出了撤資等威脅性暗示,要求改變對資方不利的條款。中美商會也難免面對這樣的詰問,到底以什么姿態來參與中國的政策制定和立法過程?
柏麥高強調,中美商會支持和歡迎《勞動合同法》的制定,他們堅持“建設性的介入”姿態,與中國政府的不同部門展開互利的協作。他說,經過包括中美商會在內的各方介入,相比一稿、二稿。最后通過的《勞動合同法》是“一部更好的法律”。柏麥高當然是指針對美國投資者的利益而言。也有人認為該法在對勞動者權利的保護方面相對于草案有退步。對此,柏麥高的看法是,在立法博弈中,“有人高興,有人感到不高興”是正常的。
從《勞動合同法》的一審—直到由全國人大通過,中美商會在不到一年時間內,邀請全國總工會方面的人士與企業進行對話交流等表達訴求的相關活動舉行了約10次。
各方在法律起草和修改過程中的博弈如何在最終法律文本的形成過程中發生作用,是一個難以探究的問題,我們只能尋找商會的建議在草案修改中得到的體現。這點和國內商會的遭遇類似。中美商會在對外發布的對《勞動合同法》的意見中宣稱,最終的法律比初期的草案更靠近商會的立場,比如一審草案規定,只有雇主向員工提供了最少6個月的脫產培訓,才可以在解約時向員工追索培訓費。中美商會在提交的意見中認為,脫產培訓是少有的,持續這么長時間的更少,二審稿就將時限縮短到1個月。
8月30日表決通過的《反壟斷法》也是中美商會密切關注的,柏麥高說,這是因為該法將影響到美國企業在中國的并購業務。在過去7年中,中美商會及其會員多次對草案提出了書面意見和建議。
商會作為中介組織要有效發揮作用,大多與政府部門保持良好的互動,在華的外國商會也不例外。而且這也是由外國商會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起到溝通中國和他國的作用決定的。
溫州商會因其區域性色彩,多能影響地方性法規的成文。在《浙江省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的制定過程中,周德文提出的增加法規的“干性”內容和將規定細化等建議就得到了很好的體現。溫州市一級的法規,很多就是由他提議并參與起草的。
缺角的良性利益表達機制
對民間商會發展的正面評價,主要來自對一個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的期待,這種理論視公民社會為—種以權力分立為特征的新型政治發育成長的基礎。事實并不像理論預期那樣樂觀,因為商會作為“被允許”存在者,無法左右權力多元化的幅度和進程。以溫州商會為代表的民間商會在適應性的發展過程中,只顯示出與政治權力有限的相對獨立性。
在與記者的交談中,周德文若干次不完整地引用了德國哲學家馬克斯·韋伯對國家的定義:政府是一個暴力組織,故而不可以與政府走得太近,否則就會有危險。但同時又強調,商會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商會的功能之—就是貫徹政府的意圖。
商會的發展有賴于政府釋放出的政治空間。商會從一開始就是政府對民間組織進行有選擇培育的產物,作為低政治風險高社會經濟效益的組織,商會“既被制約,又被縱容”,而政治風險相對較高的工會等組織,則—直處于沒有自主發展空間的狀態。
政府的“分型控制”導致了各類民間組織發展的不均衡。周德文不斷強調的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所代表的企業的利益,并非由企業家、勞動力和生產資料構成的整體上的企業,而僅僅是指企業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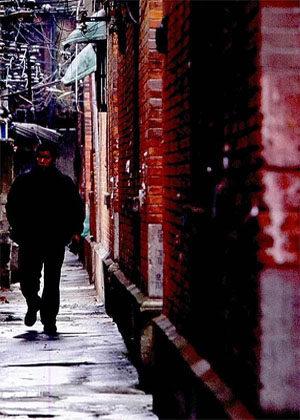
比如,他認為企業與員工相比,也是弱勢的,企業開除員工必須支付經濟補償,而員工違約離職,卻不用負擔任何責任;違反法律的企業也可以找到合理化的解釋,如按照《消防法》的規定,企業是不可以將員工集體宿舍與生產作業、物資存放的場所相連通的,即所謂的“三合一”企業是必須進行整頓的,溫州也確實發生過“三合一”企業發生火災釀成慘劇的事件。站在企業的立場上,周德文認為,溫州土地緊張,完全解決“三合—”問題是不可能的,完全按照法律要求,很多企業就要干脆關門,于是明知違法,商會還是通過關系向政府陳情,請求對企業從輕處罰。這無疑為未來埋下了安全隱患。
浙江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郁建興教授認為,商會存在的政治前提是權力的多元化,與商會相對應的最重要的民間組織應該是工會,由于沒有跨企業或跨行業的工會,小企業的工人無法加人工會;大型企業盡管組織了工會,但缺乏獨立性,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因此商會變成了經濟新貴們的游戲,在超時加班、拖欠工資、危險作業等違反《勞動法》的行為普遍存在時,較少看到工會出面維權。
王詩宗副主任說,有些鞋廠的老板在接受他們的訪談時就承認,其企業雇用員工的期限都不超過一年,到時間就要強制解雇,迫使工人在不同工廠間進行流動,這樣做的目的是避免惡劣的工作條件引起白血病的責任。溫州一名國有企業退休干部告訴記者,在他曾經調查過的97家民營企業,發現沒有一家企業有雙休日,工人每天的勞動時間平均在10至12小時。
在勞資博弈過程中,商會越是強勢,工人的地位就越是弱勢。商會力量的發展和強大,使得溫州模式創造經濟奇跡的光環被放大,卻掩蓋了高速發展的代價,即大批非溫州籍打工者的安全和健康問題。
商會在被“縱容”的同時,也受到限制,在“一業一會、一地一會”的規定下,雖然有些行業協會已經無法發揮作用,但新的商會組建卻得不到批準,如溫州市托運業商會已經10年沒召開會員大會和組織活動,去年有30多家企業要求成立溫州市物流商會,但為登記機關所拒絕。
外國商會也為類似的規定所制約,中美商會會長柏麥高就抱怨說,中國是一個大國,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到北京、上海以外的中西部投資,一家商會不能滿足需要了,但在外地建立分支機構卻得不到允許,
商會并非公益性的組織,而是有明確的利益訴求的,正如王詩宗所言,不能期待非政府組織是上帝派來的。與商會相對應或者可與之進行利益博弈的民間組織的缺位,使得民間商會在增進利益表達渠道的同時,也可能是對更廣泛的良性利益表達機制的—種損害。在這個方向上行進的商會勃興,對—個健康的公民社會的成長所能夠貢獻的力量,說到底仍然被政府釋放的政治空間所規約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