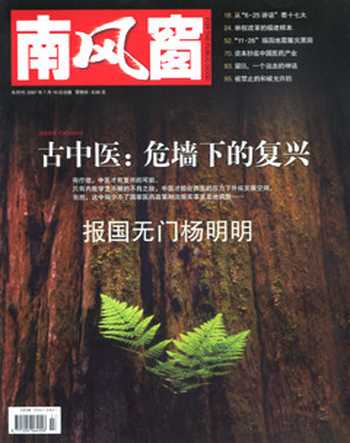中央部委的新角色
王大鵬
面對各種特殊的利益集團,我們的政府部門還無法做到更有效地超脫,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一說難遂人愿,這也可能就是政府機構改革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新人,新部長
當前,有兩位著名學者成了公眾人物,這不是因為他們的學識與榮譽,而是他們成了共和國的非中共黨員的正部長。一位是改革中國開放29年來,第一個出任國務院組成部門正職的無黨派人士陳竺。兩個月前,另一位黨外人士萬鋼,被任命為科技部部長,他是1972年傅作義辭任水利電力部部長后35年來,首位民主黨派人士出任政府部長。

雖然兩位非中共黨員的正部長身份引來了眾多好奇的目光,但是從中國所實行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制度來看,這并沒有任何的稀奇之處。中央文件要求,涉及行政執法監督、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聯系知識分子緊密和專業技術性較強的政府部門,必須配備黨外領導干部,有條件的可配備正職。大批的黨外人士一直都在擔任著從地方到中央的各級領導職務,從這個角度來看,此次兩位正部長的產生只是擔負了直接的行政領導職務,作為黨組書記的黨員干部則擔任了副部長。
當然,兩位非中共黨員的正部長的產生也并非只是簡單的職務任命。輿論普遍認為,黨外人才之所長有兩條,一個是擁有專業技能,一個是相對超脫的社會角色使他們易用專業眼光處理事務。
但擁有專業技能很顯然并非黨外人才之獨有的特長,那么相對超脫的社會角色可能就是一個關鍵詞。對一個部門首長來說,既要面對本系統利益的需求,也要面對各種利益集團的需求。“超脫”顯然不會僅僅是說超越于個人利益,而更多的是對這兩種需求的超脫,尤其是對最后一種。
那么,通過延攬社會角色超脫的黨外人才“入閣”,是否傳遞了一些未來中國政府體制改革的信息呢?
歷次政府機構改革要解決的主要矛盾
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政府機構改革大致每隔5年進行一次。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每隔5年開始一場調整或者精簡機構和裁減人員的改革。
第一次改革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所面臨的問題是,“文革”后開始啟動改革開放政策,整個國民經濟恢復建設和發展,許多老干部落實政策,官復原職,這解決了“文革”期間導致的各種各樣的歷史遺留問題,但也導致了許多新的問題:國務院機構數量達到100個,有些部門副部長達到20來個,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到達歷史最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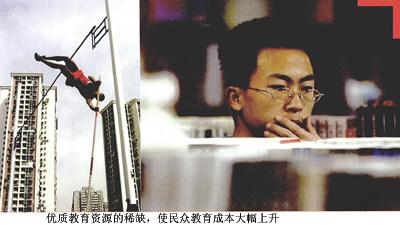
改革到了1987年時機構和人員已經迅速回潮。不過,由于當時的經濟體制已經開始轉軌,物資部門和流通部門開始通過雙軌制改革逐步進入市場化階段,這為機構精簡提供了職能轉變的空間。經濟改革,與組織人員精簡一樣成為機構改革的主要手段。
1993年,中國政府宣布正式開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由此開始,政府開始朝著市場經濟的方向轉軌。政府職能開始全面轉變。但當時因為一切剛開始,不可能很快到位,機構只能以此為基礎進行局部性的精簡,所以成果有限。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組織機構,變成了政府職能進一步轉變的障礙。計劃經濟政府部門的利益集團借助其組織機構的存在,阻礙著政府職能轉變和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
1998年春,國務院以強有力的手段,排除各種干擾和部門利益的阻力,雷厲風行地進行機構撤并,把計劃經濟色彩的經濟部門撤并,鏟除計劃經濟利益集團的組織基礎,給政府職能轉變提供組織機構的空間。這次改革,大多數經濟部門都合并到經貿委,成為經貿委下屬的若干個部級總局,集中等于弱化,總局等于是過渡。經過3年的過渡,2001年9個總局7個撤銷。1998年改革還大力解決吃飯財政問題,精簡人員。
1998年的政府改革進行一段時間之后,中央在反腐敗斗爭中發現,人事管理領域、行政審批領域和財政制度領域,最容易發生腐敗。鑒于這一認識,政府組織變革從組織機構和人員規模轉向人事制度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以及財政預算制度改革。
2003年3月,新一屆政府繼續進行政府改革,政府組織繼續調整,政府職能進一步轉變,上次改革沒有解決的遺留問題局部得到了解決。如外貿部,1998年因東亞經濟危機而保留,此次撤銷,和經貿委的一部分組成商務部,而計劃經濟委員會也被撤銷,與經貿委的一部分組成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這次改革,主要為調整內部機制。特別是為應對人世過渡期的即將結束,加快了法治政府的建設步伐。
2003年機構改革沒有大幅度精簡機構,也沒有大幅度轉變職能,并且還建立了國資委等特殊機構。在市場經濟不完善的情況下,廣泛的行政監督無法淡出,公共服務部門的改革剛剛開始,立法和司法部門發展不充分,無法替代國務院對行政部門比較獨立的直屬局進行有效的立法和司法監督。與此同時,全社會對公共服務的日益增加的需求使得政府體制仍然依賴于行政機關的復雜運作。國務院為首的行政機構的復雜性,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組織效率,但也在—定程度上減少了因決策失誤可能導致的消極影響。
簡單的分析可以看出,歷次政府機構改革都是針對當時行政管理體制所面臨的主要矛盾而進行的。或者是破除舊的經濟體制遺留的政府機構利益,或者是建立適應新政府職能的機構,或者主要解決人員膨脹問題。由此可以說,下一次政府機構改革主要是要解決現在所面臨的主要矛盾。
可能的路徑
中國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至今已有15年了,社會的利益分化已經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作為公共權力主體的政府應該成為為全社會提供公共服務、超脫于社會各種利益團體之上的公共權力機關,作為中央政府主體的中央部委更應該如此。但是,在現實的政府運作過程之中,我們經常能夠看到的是政府部門對于特殊利益集團的軟弱無力甚至個別部門和官員的推波助瀾乃至于沆瀣一氣。每當我們震驚于重大災難的時候,不管是礦難還是黑磚窯事件,在其后都能夠看到本不應該看到的身影,而我們應該看到的部門卻又不見蹤影。
一般來說,一個政府部門的非超脫性最壞的形式就是為自身的部門利益服務。以審批權為例,由于許多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過分迷信審批、許可的作用,把審批、許可看成是行政管理的法寶。把辦理許可視為給相對人“恩賜”,明示或暗示相對人給予回報,或暗或明搞權錢交易,行賄受賄。這種形式由來已久。并且常常比較多集中于政府部門具體辦事的層級。本屆中央政府繼續進行審批改革和推動以法行政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非超脫性最典型的是受制于特殊的利益集團,被它們的利益束縛,被動或者主動地置公共利益于不顧。很多腐敗案件的背后都有“保護傘”,這些部門和官員實際上已經成了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在中央部委一級中,前不久揭露出來的藥監局的集體腐敗案件,則充分暴露出一個國家級的監察機構及其官員是如何淪落為一些利益集團的同謀者,而置公眾的生命于不顧的。
又比如居高不下的房價問題是廣大民眾迫切關心的問題,也是政府關心的重中之重的問題,雖然中央政府出臺了很多文件,但是依然難以達到預期效果,中央政府的執行力被大打折扣。這里并非要把某一類利益團體置于社會的對立面,也并非要求政府過多動用行政手段解決問題,那樣的話,就與我們構建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背道而馳了,但是不同利益團體的利益的分配已經顯失公平。很多更有效也更合理的政策可能受制于特殊的利益集團而無法出臺。這樣的利益集團往往和一個部門系統存在各種聯系。隨著國務院對部委行政首長問責的完善,對于一個部門首長來說,怎么解決這種受制問題,完成當負的責任已經成為一個很大的挑戰。中央政府提高執行力,關鍵就是要讓部門真正地超脫于各種利益集團,在整個社會扮演協調和裁決的社會角色,用新公共管理的理論說,就是從一個劃槳者變為一個掌舵者。
政府工作績效的評價標準,已經開始由過去單純注重GDP向注重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方向轉變。各個社會階層的和諧相處已經是中國政府改革的一個基本的價值選擇。對各個利益集團的協調能力也就成為行政首長完成問責的一個必備條件。從人事調配層面看,選擇一些相對超脫的人員例如黨外知識分子擔任領導干部乃至正職,使得他們能夠多從專業的角度而不是從特殊利益集團的角度考慮政府的行為和政策,對提高政策的公共性是有好處的。當然,問題還會回來的:如何從制度上加以保證,使得新的領導干部不會又被特殊利益團體制約住。
從行政學的邏輯上說,具體解決手段還有很多,比如加強跨部門辦事機構的權威性,但畢竟是疊床架屋,提高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率。有時候人們甚至選擇一些特事特辦的方式,比如讓臨時性機構發揮作用。但短期效應太過明顯,長久來看對政府和民眾不利。從根本上說,還是應該找到有效容納利益集團博弈的制度框架。
面對各種特殊的利益集團,我們的政府部門還無法做到更有效地超脫,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一說難遂人愿,這也可能就是政府機構改革下一步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