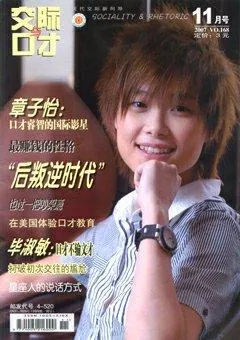細語雋言 情真意切
楊海亮
2006年10月,應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同學的邀請,當代著名散文作家、詩人趙麗宏作了題為“閱讀、回憶與思考”的演講。這次演講在學子們中間引起了強烈反響,趙老師對文學的熱愛和對人生的執著,讓他們深深感動。
亮色一:袒露心跡觸動人
趙麗宏老師十分樂意與年輕學子對話,所以,他能盡情地、毫無隱藏地、完全公開地把自己展示在學生面前。這種發自內心的話語在他的演講中隨處可見:“再這樣下去我會忘記怎樣說話,我會變成一個啞巴!”“我覺得自己就像那個黑奴一樣,一個人坐在一塊木板上,在海上漂浮,沒有前途。”這些傾訴傳遞出來的困惑、郁悶和痛苦,讓聽眾感同身受,不能自已。聽眾也不難明白:人的物質與精神兩個世界,如果失去精神,或者精神空虛,物質上再豐盈、再富足也是沒有意思的。相反,如果有了精神支柱,那是多么愜意:“不管白天干活有多苦、多累,只要想到在晚上,在草屋里的油燈下可以看自己喜歡的書,我就很滿足。”趙老師通過揭示自己最隱秘的內心世界,為學子們解讀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性格,也使他們從心底理解了他的情感和氣質。這種“我口說我心,我心表我情”的演講,當然會得到大家的認可。
亮色二:人生經歷吸引人
演講要充實、要具體、要豐滿,就得有材料,有內容。但在趙麗宏老師那里,不但有“米”,而且是“好米”。這“好米”就是他豐富的人生經歷。他以自己頗為曲折的人生經歷,給大家講述了自己艱難的心路歷程,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他通過苦讀、不斷進步、不斷充實人生的故事。在節選的片段里,他主要回顧了農民送書和巧遇書庫兩個故事。前一個故事對他來說,好比久旱逢甘霖;后一個故事對他而言,則如同錦上再添花。讀書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讀書豐富了他的內心世界。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用自己的喜憂苦樂與聽眾交流,沒有泛泛而談,而是娓娓道來,給我們帶來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啟示。
亮色三:美好語言愉悅人
綜觀趙麗宏老師的演講,其語言風格以質樸為主,華美為輔,兩者兼容,相得益彰。演講中時時處處閃現著清新淳樸的語言,這些語言不矯揉造作,不無病呻吟,為演講披上了一種“泥土”色彩,賦予了演講活的靈魂。比如,趙老師回憶那些農民時感慨:“知道我最需要書以后,沒有人號召,我所在的那個生產隊里的所有農民,只要家里有書,全都翻箱倒柜地找出來,送給我。”他是由衷地感謝那些農民,“假如現在死神走到了我的面前,他問我,在你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如果讓你見十個人,你想見的是誰?我閉上眼睛想一想,我發現,這十個人,十張臉中,大部分都是我在農村認識的那些農民。”而演講中,趙老師隨口吟誦的自己創作的詩歌,真實而真誠。此外,長句與短句交替使用,整句與散句變化表達,使語言極富參差美。
亮色四:意味深長啟迪人
演講應該有正確鮮明的主題,演講的主題最能體現演講的思想價值和審美品位,使演講具有深刻感人的藝術魅力。在《閱讀、回憶與思考》的演講中,趙麗宏老師談“閱讀”,談“回憶”,但歸根結底是為了談“思考”。他思考的結果是什么呢?我們從他的人生經歷早已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我希望你們當一個文學愛好者,多讀一點書,多讀一點有趣的書,肯定對你們非常有益”。為了表現這一主題,趙老師在談自己的經歷時已做了分析、概括、提煉和延伸,但為了讓年輕的學子更深入地去理解和體悟自己的心思,他又談及了自己與英國女作家萊辛的一次對話,借萊辛一個看似偏頗實則深刻的觀點來升華主題,可謂用心良苦。演講的最后,“希望你們和文學結伴,讓文學成為你們終身的朋友”這一殷切期盼使演講具有了一種雋永的感召力。
閱讀、回憶與思考(節選)
上海趙麗宏
我中學畢業那一年是1968年,正好趕上中央號召全國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于是我選擇去了我的故鄉崇明島。記得當時我是一個人背著簡單的行李到鄉下去的,去的時候心情灰暗,因為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將會怎么樣。面對著一群農民,我時常感到孤獨,因為我覺得我跟他們沒有什么話可以講。于是我就不說話,一天到晚埋頭干活、寫日記。我在日記中寫道:再這樣下去我會忘記怎樣說話,我會變成一個啞巴!潛意識里,我覺得我跟那些農民是不可溝通的。盡管他們很照顧我,同情我,經常送吃的東西給我,但是我覺得他們救不了我。我在日記里寫:善良的人們啊,你們救得了我的肉身,救不了我的靈魂,我的思想是無法跟你們溝通的,我心靈上的需要你們是無法給我的。
那時候我的腦子里經常出現這樣一幅畫面:一個體格非常健壯的黑奴,身上布滿帶血的鞭痕,手上戴著鐵鐐,赤身裸體地躺在一塊木板上,這塊木板剛好可以撐起他的重量,使他浮在海面上。那個黑人躺在木板上,瞪大眼睛看著天空,目光里流露出一種絕望。他沒有生路。在離他不遠的地方的海面上,露出來鯊魚黑色的魚鰭,一群鯊魚向他游過來。他的結局可想而知:或者是被鯊魚吃掉,或者是被太陽曬死,或者是被海浪淹沒。我覺得自己就像那個黑奴一樣,一個人坐在一塊木板上,在海上漂浮,沒有前途。我把自己當時那種絕望的感覺作了一首詩,記在日記里,我背給你們聽:假如坐上一艘小小的舢板/沒有舵把沒有篷帆/沒有船槳也沒有指南/頭上是呼嘯狠狠的風暴/身邊是劈頭蓋臉的浪山/只有海鷗凄厲的呼號/在灰暗的天空里時續時斷/只有鯊魚慘白的牙齒/在起伏的波浪間一閃一閃/你說,你說/我該怎么辦……
我還記得我是在一個小草屋里,在一個油氈上寫的這首詩。當時確實感到非常孤獨。幸運的是,這種狀況大概只延續了三四個月的時間,然后我的生活就發生了很大變化。
其中一個原因是,那些我曾經認為是愚昧的、無法交流的、無法溝通的農民,他們改變了我對生活的看法。那些農民,他們發現了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可能是我拿著一本書,或者一張報紙,躲在角落里閱讀的時候那種專注的、甚至是貪婪的神情,引起了農民的注意。他們說,城里來的那個小青年,他一看書就像變了另外一個人。知道我最需要書以后,沒有人號召,我所在的那個生產隊里的所有農民,只要家里有書,全都翻箱倒柜地找出來,送給我。我記得他們給了我幾十本書。有《紅樓夢》、《儒林外史》、《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孽海花》、《千家詩》、《福爾摩斯探案集》、《官場現形記》等等。農民認為只要是書,只要是印刷品,都給那個城里來的學生。我是來者不拒,照單全收。這些書,有的價值不菲,比如一個退休的小學校長送給我一套《昭明文選》,乾隆年的刻本,裝在一個非常精致的箱子里,現在十萬塊錢也買不來。有的雖然沒什么用,比如一個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的八十歲的老太太,送給我一本1936年的老黃歷,但卻讓我感動得落淚,而且至今難忘!我寫過一本書叫《在歲月的荒灘上》,記得書的前言是這么寫的:“假如現在死神走到了我的面前,他問我,在你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如果讓你見十個人,你想見的是誰?我閉上眼睛想一想,我發現,這十個人,十張臉中,大部分都是我在農村認識的那些農民。”
改變我的第二個原因是書,書改變了我的生活。除了農民送給我的書以外,我還意外地發現了一個書庫,這簡直就像一個童話一樣。有一次收工后,我生火做飯,有一個老太太來幫我,隨手扔給我一本書,說:“拿去生火吧。”我對書有一種本能的直覺,只要根據段落排序就能判斷是政治書還是文學書。我打開一看,憑直覺判斷那是一本文學書,我就拿起書,讀了起來……那老太太后來一看,還沒生火,她就跟我說,你不用著急,這些書還很多,就在學校里。后來我找到那個學校,果然有一個非常可觀的書庫,從泥地到天花板堆滿了書,而且每一本都是值得讀的書,這真是個奇跡。從鄉民那里我了解到,辦這個學校的校長,當年家里有很多田地,為了辦教育,他賣掉所有的田地,讓相鄰的所有孩子都能來上學。所以我看到的那些鄉民,盡管有一些土氣,但其實他們都有文化,都上過學,就是因為有這所學校。我在書庫里呆了整整一天,最后,我大概從那里拿走二百多本,足足裝了三麻袋,運回到我的住地。這些書對我的生活起了很大的改變作用。不管白天干活有多苦、多累,只要想到在晚上,在草屋里的油燈下可以看自己喜歡的書,我就很滿足……
那時候我在讀書之余,作一些筆記和寫作,當然,當時我沒有想過以后要做作家,寫的東西要發表之類的問題,只是用寫作來排遣寂寞的時光、來抒發我內心的情感而已。在我的筆記中,我寫我的生活、寫我周圍的人物,是用文字來給我周圍的人畫素描,同時也將我看到的大自然的變化描畫出來。有時候寫一些閱讀感受,為什么我喜歡這本書而不喜歡那本書。這些文字,在我現在看來仍然是非常真實的,因為當時從來都沒想過要用這些文字換取什么、取悅什么,只是在真實地表露自己的情感。去年《讀者》雜志告訴我,說轉載了我的一篇文章叫《雨聲》,這其實就是我那時在草屋寫的一篇日記……我想說的是,這些文字時隔將近四十年還有人喜歡,還有生命力,原因是什么?我覺得是因為它的真實和真誠。這是我人生的第一站,如果沒有這一站,也就不會有現在的我。
我的回憶就到此為止吧。我想在座的各位,你們未必都想當一個作家,但是不管怎樣,我希望你們當一個文學愛好者,多讀一點書,多讀一點有趣的書,肯定對你們非常有益。大概在十年前,我接待過一位英國的女作家,叫萊辛,當時她已七十多歲了,她對我說的一句話讓我大受震動,她說:“現在在英國,高學歷的野蠻人越來越多了。”我問她什么叫“高學歷的野蠻人”,她說:“這些人有碩士博士頭銜,他們懂得現在最精密的技術,但他們沒有感情,他們冷漠,為什么?因為他們從來不讀文學作品。”她的話有些偏頗,但不無道理。一個人的人文素養中沒有這樣的閱讀經驗,他的人生可能是殘缺的,他的精神也可能是殘缺的。所以我要送給大家的話是:不管你們將來做什么,相信你們都會有成功的人生,但希望你們和文學結伴,讓文學成為你們終身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