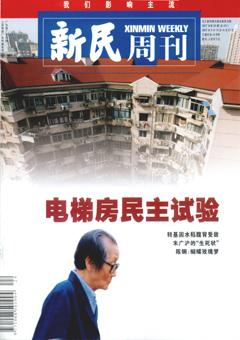“中國第一棟”前世今生
梅瓔迪 陳統奎

陸豐路2-4號實施綜合改造,加裝電梯,成為上海乃至國內首批加裝電梯的"老公房",被居民戲稱為"中國第一棟"?
40來歲的陳超娣拎著兩袋蔬菜走進上海市閘北區陸豐路一棟多層住宅樓?她從電梯門前走過,卻沒有去按下電鈕,而是徑直走上樓梯?爬上二樓她已經氣喘吁吁,但她不想"沾便宜"?
6年前,陳超娣所住的陸豐路2-4號實施綜合改造,加裝電梯,成為上海乃至國內首批加裝電梯的"老公房",被居民戲稱為"中國第一棟"?
然而,包括陳超娣在內的不少二樓居民強烈反對繳費使用電梯,他們寧愿每天爬樓梯,以省下每月平均不到10元的電梯費?于是在加裝電梯前,這些居民和物業公司達成協議,所有二樓居民不使用電梯,也不交電梯費?
"中國第一棟"是上海"平改坡工程"首個綜合改造試點?從上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初,為緩解住房匱乏的矛盾,上海曾建造了一大批火柴盒式的多層住宅?如今這些"老公房"公共設施不足,內外陳舊不堪?1999年起,上海開始對這些建筑的住宅性能和建筑外觀進行改造?
顯然,"中國第一棟"的試點意義重大,有關部門希望通過陸豐小區的試點成功陸續在全市推廣?6年過去了,記者卻發現,試點出現了諸多遺留問題?
通報會前后
居民們回憶起6年前的那個通報會,依然記憶猶新?他們說,今天出現的一些問題在那個會議上就有了端倪?
2001年6月末的一個黃昏,陳超娣和小區里其他居民們帶著疑惑,走向小區對面不遠處的上海電影技術廠的會議室?在這個老式居民小區,召開居民開會是件新鮮事?陳超娣不太清楚這是一個什么級別的會議,此前居民們從各種渠道打聽會議的主題,據說是一個政策發布會,有人于是抱怨"什么政策發布需要這樣的架勢?"
晚上6點45分,居民陸續閑聊著進場?會議室一排長臺前,面孔熟悉的居委干部坐在靠邊兩側,中間寬敞的位置留給了街道黨政負責人?物業公司和閘北區房屋土地管理局的領導?
會議直奔主題,幾位負責人向居民們發布政策:陸豐小區將進行"平改坡舊房改造工程"?與全市正如火如荼大力推進的"平改坡工程"有所不同的是,小區2號?4號樓將率先在舊房內加裝電梯,同時依居民原有面積進行增擴建?改造后,原先的6層樓將被加至7層,一樓居民上搬到七樓,將底層樓房騰空改成社區服務點?每戶居民平均增加約17平方米建筑面積,地段標價每平方米已達5000元,而居民增加的面積每平方米只需支付1295元?
大伙頓時興奮起來,陸豐小區居委會主任胡惠蓮和幾位負責人立即被他們圍住了,大家"問個沒完沒了"?然而,也有一些居民對這個項目毫無熱情,"開完會沒吱聲就走了?"4號樓101房的虞定康?陳曉寶老兩口即是一例,如果這個項目實施,他們不得不從一樓搬到七樓,而兩位那時已經快70歲了?4號樓103室的黃孝年也不樂意,他買下這個房子不過一年,剛剛花了近3萬元錢裝修,如果搬到七樓,裝修費豈不是白花了?
二樓?三樓?四樓?五樓……幾乎每一層都有居民不愿工程隊開進自己裝修過的住房?"態度堅決而冷漠,始終不同意政府動他們的房子?"時為項目負責人?現供職上海市住宅建設發展中心的徐堯認為,小區老人比較多,受益面比較廣,此番試點改造,政府特意最終確定在條件相對較差?收入水平較低的陸豐小區實施,"如果可以啃下條件比較差的'硬骨頭',試點成功后在更大范圍推廣會更容易"?
居民大會后一個星期,由區房地局?街道?居委會?物業等多方面組成的工作組來了,在距陸豐小區幾分鐘路程的一家小飯店包廂里建起了現場辦公室?此后40天里,胡惠蓮?徐堯等十余位工作人員每天下午4點起就蹲點現場,"一戶戶居民做工作,忙到半夜又熱又困才收拾東西回家"?
在居民大會上政府承諾,必須全體41戶居民全部簽訂協議后工程才能開工?3周以后,多數居民簽約了,只剩下為數不多的"釘子戶",虞定康?陳曉寶"榜上有名"?他們對于"面積增大,房子增值"毫不動心,說是不圖利益,就圖個方便?
"一戶居民上門十幾次很平常?"胡惠蓮說?75歲的陳曉寶告訴記者,當年項目辦屢次做工作毫無成效,就警告說他們家的天井是違章建筑,必須強行拆除?陳曉寶于是把天井里的物品搬了出來,告訴工作人員:"這個天井我們2年前買房子時就有了,的確是違章建筑,你們可以拆掉?但房子是私人的,天井拆掉以后,你們沒有權利再踏進這個屋子一步?"
矛盾激化,矛頭直指上門動員的胡惠蓮?"說什么的都有?有些居民指責我,說是我自己想改造才那么起勁拉大家一起下水?還有的話更難聽,暗暗懷疑我拿了好處?"胡惠蓮就住在4號樓五層,當時倍感委屈?憤怒和無奈?
制度困境

陳曉寶老人的強硬出乎意料,工作人員不愿強行拆除天井,再次激化矛盾?最后雙方妥協,兩位老人搬到403室?403室的主人是閘北區一位官員,他的積極配合化解了這場危機?然而,這個妥協卻留下遺憾,兩位老人的房產證至今無法更換?
103室的黃孝年是最后一個簽約的?他做毛巾批發小生意謀生,在103室的天井側旁開了扇邊門方便進出貨物,他很不情愿放棄這個便利?作為交換的條件,徐堯答應裝修時幫黃孝年擴建一下廁所?然而,裝修結束后黃孝年發現徐堯沒有實現諾言,他非常生氣地扣下1萬元工程款?令他吃驚的是,6年過去了,既沒有人來擴建廁所,也沒有人上門催款?據說,負責施工的徐堯為了順利開工,當初許下了各種諾言,然而爽約的不少?"居民意見難統一"是徐堯十分頭痛的問題,"只要一戶兩戶不讓你做,整幢樓都做不起來"?
記者問,為什么不讓業主委員會來協調?徐堯回答說:那時還沒有業主委員會?事實上,這個小區2000年已經成立業委會了?作為居委會成員,胡惠蓮知道這個事實,她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很巧妙:"我們撇開業委會是無意的?"
更耐人尋味的是,以維護業主利益為己任的業委會主任韓月秋不認為自己被"撇開",他說當時物業公司給他看了改造方案,他覺得這是一件利民工程,很爽快地簽名同意了?記者提醒他,如此重大的項目決策必須經業主大會授權,否則業委會主任無權"同意"?韓月秋回答說,一些居民意見很大,如果召開業主大會討論,這個好事可能就黃了?
韓月秋強調,他簽下自己的名字"有民意基礎",他是通過明察暗訪來了解民意的?徐堯也說,當時居委會的民意調查顯示,66%的居民支持改造?2號樓204室的何建平甚至表示:"90%的居民都是擁護改造的?"何家的房子改造后多了14平方米,衛生間和廚房亮敞多了,從二樓到六樓的居民家都是如此?從一樓搬到七樓的居民受益更多,房子面積幾乎增大了一倍?
事實上,這個試點項目與其他"平改坡"項目一樣,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路徑,即由上海市房地局資源管理局和區政府互相配合,項目所在地街道辦和居委會積極配合,"協調各類矛盾"?領導指示"把老百姓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作為如何改造的出發點",但沒有具體的居民參與程序,項目的決策權事實上由現場辦行使?
徐堯坦陳,2001年搞這個試點最大的挑戰是制度困境?此前,徐堯曾隨團去新加坡考察社區管理經驗?他告訴記者,新加坡的社區改造工程,只要三分之二以上業主同意,就可以推行,對持不同意見者可以依法實施?徐堯很欣賞新加坡的這套制度?記者提醒他,強制措施的前提是民主決策,徐堯點頭同意?他說曾在新加坡參觀了一個社區改造項目,工程僅需16天,但溝通?協調居民利益卻用了整整6年,才獲得"超過三分之二"的居民授權?
然而,當時徐堯卻沒有這樣一種民主協商?民主決策的制度,他不得不依靠"做好居民思想工作"的傳統套路來凝聚共識,讓居民服從和支持政府決策?當居民利益與決策者意志出現矛盾時,維護利益的居民就成了"釘子戶"?而對付"釘子戶",徐堯也沒有"強制措施",他為此倍感頭疼?
錢是個"偽問題"
"居民沒有信任感?"他們找不到公開的利益表達機制,現場辦也沒有透明的利益協調機制,徐堯的做法被一些居民稱為"暗箱操作"?
"這是政績工程不是民心工程",4號樓103室的黃孝年評價說?在很多居民記憶里,當時的街道辦事處副主任陳某上門動員居民犧牲利益顧全大局,她自己卻"拿好處"?原來,陳某拿到了一套房子,在2號樓的七樓?第七層是加蓋的,為的是把一樓的居民搬上去,空出一層來做老年人活動中心等公共設施?根據政策,如果一樓居民不愿意搬到七樓,二樓居民愿意的就可以搬?2號樓101室的主人不愿意搬,于是讓出一個機會,而這個機會本來屬于204室的何建平?搬到七樓面積增加近50平方米,只不過支付約10萬元,遠遠低于市場價格,開出租車的何建平,做夢都想得到701?沒想到,何建平去現場辦報名時,卻被告知已經有人預定了?改造工程結束時,何建平看到搬到七樓的是陳某,何建平傻眼了?至今,陳某如何拿到這套住宅對許多居民來說依然是一個秘密?記者登門造訪,正逢陳某外出講課?
電梯運行費方案的決策也缺乏公開性?由于二樓居民不樂意負擔這筆費用,物業公司干脆和他們約定俗成:"今后你們不繳電梯運行費,也不搭乘電梯?"這種私下交易并不能服眾,也為日后管理留下麻煩?據說仍有部分二樓居民"搭便車"?"有一戶二樓居民經常乘電梯上下,大家不多說,但樓上樓下彼此心照不宣關注著進出人員的'資格'?"住在三樓的一戶居民頗有微詞,"如果二樓不繳費也可以坐電梯,以后我們也不會再去繳費了?"
記者詢問韓月秋,當初制定電梯運行費方案,為什么不開業主大會討論后民主決策?韓月秋告訴記者,他有自己的工作方式?韓月秋的"說服"和居委會的"思想工作"異曲同工,他們似乎還不很適應與持不同意見者?利益攸關者公開對話協商這樣一種"工作方式"?
電梯運行費還曾發生過一段風波?時間回溯到2002年底,所有工程接近完工,居民喜氣洋洋地等待電梯開啟使用?然而,3個月里電梯卻如同擺設,"費用都沒有著落,電梯怎么開得起來?"物業公司林曉昇經理回憶說?
老公房新裝電梯后的開銷不是一筆小錢,而物業費標準依然按照舊制收取,每個居民上繳電梯運行費不過區區幾塊錢,"缺口不是幾百塊錢?"據徐堯介紹,一般新建的高層建筑,都有電梯水泵運行費,每月每平方米0.55元,其中居民承擔0.15元,另外0.40元從電梯維修基金中扣除?但老公房根本就沒有電梯維修基金,這就給物業公司出了難題?
這筆錢直接向居民收取不就得了?面對記者這個問題,徐堯苦笑:"以前管理費兩三元居民都不愿意出,更不要說電梯維修費了?"而有的居民卻說:"當初簽約沒提要付電梯維修費的問題,今后肯定不會支付一分錢?當然電梯也絕對不能停運,簽約到七樓的時候就說好有電梯的?"
"在政府主導的試點中,居民的參與度不夠",徐堯感慨不已?但物業公司不做賠本生意,到頭來,還是他出面解決,由物業公司的上級北方集團?區政府和市政府三家貼給物業90萬元,"10年電梯運行費用解決了"?至此,電梯才正式開始運行?
10年后怎么辦,徐堯"就不知道了"?他還向記者透露,后來政府又想在幾處試點給老公房加裝電梯,由于運營費問題都擱淺了,"中國第一棟"成了前車之鑒?
困擾物業公司的還不止是電梯運行費?小區改造完畢后,由原來的開放式改建成封閉式,物業公司的職責也在擴大?增設門崗配備4名保安24小時值勤,增配保潔員1名?按照最低工資標準800元計算,這5個人每月物業公司的支出就是4000元?
"每戶居民每個月3元保安費,3元保潔費,一共也就6元錢?整個小區136戶居民,滿打滿算全部收繳也就只有816元?何況現在收繳率只有41%?"僅這一個缺口,物業公司每年虧空近4萬元?
資金問題不僅困擾物業公司,作為主要出資方的政府部門也感到吃力?試點工程市區兩級政府?物業?居民等三方共同籌措資金300萬元左右?其中,居民付款應占150萬元左右?電梯安裝費?地基加固費等均由政府承擔?在300萬元的資金中,主要支出用于七樓加層建設?徐堯介紹說,上海等待改善的老公房還有5萬多幢,如果都以政府為主要出資對象,顯然難以為繼?
徐堯提醒記者,表面上"中國第一棟"的不可復制在于政府耗資巨大,事實上這是"偽問題"?徐堯算了筆賬,在目前房地產市場里,將一樓面積的三分之一市場化,就可回籠資金100萬元左右,完全可以沖抵部分工程資金;其余三分之二面積用于社區服務,政府承擔這筆費用理所當然?然而一樓的產權后來全部劃給了街道辦事處,由其添置公共設施提供公共服務?根據協議,街道辦事處要承擔一部分工程款,但他們根本拿不出這筆錢來?
根據"市里出一點,區里出一點,物業產權人出一點"的改造資金模式,居民作為"物業產權人"也要"出一點",但至今還有很多戶居民拖欠工程款?原因是居民們用公積金支付工程款的方式被拒絕了,因為在公積金二十多項提取資金項目中,并沒有公房維修這一項,"政策上跟不上,讓工程款支付拖延至今?"徐堯說?
"后來也不再有人來問我們要錢,我們想付也不知道該怎么付了?"不少居民對此很納悶,他們也為此付出了代價,許多人至今領不到房產證?
徐堯覺得這個項目自己做得太多了,應該發揮業主的作用,盡管召開業主大會可能吵作一團,利益協調過程時間漫長,但不能急功近利地忽略這個過程?"這個過程是小區學會和諧?學會民主的過程,一個街道主任告訴我說,舊住房改造的過程就是向民主凝聚的過程,向社會和諧發展的過程?"徐堯說?(注:文中部分居民使用了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