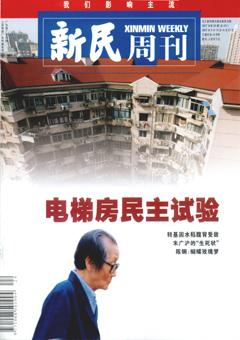薰衣草的氣息
俞曉夫

用"往東?往西"作為2007上海油雕院年展的題目,實在很好,它是一次游走之間景觀與心靈的摹寫,但又從更大的語境中揭示了當代油畫的探索現狀與中國油畫的源頭?我主持上海油雕院學術工作以后,根據上海油畫雕塑創作的實際情況,又聽取了不少藝術家的意見,認為提升上海當代藝術的水平,油雕院應該擔負起更重大的責任?而要走出象牙塔,有更大的作為,對藝術家而言,第一步就是走出畫室,融入更廣闊的世界中去?多謝上海文廣局領導給了油雕院藝術家們一次赴歐藝術考察的機會,還有老院長邱瑞敏和原創作室主任前半程的努力?藝術家在歐洲的寫生用了很大的心思,不僅用色彩,更用了思考,并從歐洲的文化環境中體悟到更耐人尋味的東西?我只是以召集人的身份將這次寫生的成果匯總起來,于是就有了這個展覽?現在,它在劉海粟美術館接受大家的評點?
自我接手主持院學術工作后,我倒是一直認為油雕院每年應該辦一個像模像樣的院展?并且認為這是對油雕院自身發展起碼要做的一件事,就好比踢足球,每年有賽季,如若不然,那我認為對油雕院來說無疑是一個嚴重的缺失?上海油雕院赴歐考察是建院以來的第一次,其學術價值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定會慢慢顯現出來?作為回報,出訪的油畫家被要求回來后在油雕院內部進行歐洲采風作品的觀摩?后來經過藝委會的討論決定升格為院展?經過一個階段的努力,畫家們以自己的風格,加上歐羅巴的熏陶,繪制出一批非常有趣的作品來,我稱之為一批散發出"薰衣草氣息"的作品,其中似乎有對歐洲經典寫實主義的敬重,也有對印象主義的懷念,也有對表現主義和抽象主義的追求,年輕的畫家甚至玩出了文獻展的那一套路數?不過,清醒的藝術家最終還是回到了"中國制造"這一原點?至于說到雕塑組,此次創作在學術上似乎更充分一些?集體的把握度也更強?由于當時院藝委會還尚在改選中,在學術上還一下子無法建立秩序,我當時并不太清楚這"藍本與創造"之學說主題產生的始末?不過拿來作為學術主題借用一下也未嘗不可?后來我是在看了雕塑家的作品后,方才明白其中之良苦用心?眼下,中國大地上的現代藝術之中國符號已被泛用,不管"文革"的,還是大清的甚至更早的,由于過于調侃,過于顛覆而形成泛濫之勢,幾乎成了老外審視中國當代藝術的一副老花眼鏡,所以不管怎么說這中國符號還是很實用的?也許油雕院的雕塑家們意識到了這一點,于是他們另辟蹊徑,在沿用中國符號的同時,十分注意把握度,尤其在直接借用中國古典藝術精品上還是舉足輕重,手下留情,指向性還是比較清晰,我以為在他們的作品里涌動著突破,衍生著自律,很有積極意義?另外,院里還有一些藝術家不一定都是這樣的?比如我畫的是人物創作:"歐洲歸來";何勇是通過人體寫生并以此為藍本,創造出自己"遇"的觀念;袁侃則照樣是他的"艷俗"話語;陳妍音和楊冬白是自我多元,靠實力說話,韓子健和石至瑩的心思則全在文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