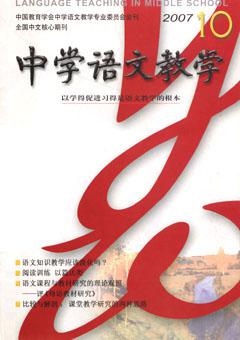《道士塔》新教
唐家龍
一
余秋雨先生在《道士塔》中,不厭其詳地列舉了許多年代,如:20世紀初年、1900年5月26日、1905年10月、1907年5月、1908年7月、1911年10月、1914年等。作者大寫特寫這些年代在敦煌歷史上發生的事情,學生在閱讀文章的時候除了了解敦煌莫高窟的發現及被掠奪這些事實,感受一下作者的憤慨之情外,是否還能夠有更深的思考,進而承擔更重的責任呢?于是,我先于學生們開始了苦苦的思考。
中西方對照!看看在這些時間點中國與西方列強分別在干些什么,靈光一閃,有了主意。
翻開中國歷史大事年表,我們發現:
1900年,即王圓箓道士發現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這一年,中國正發生著兩件大事:一為八國聯軍侵華,二為義和團運動高潮。
1905年,即“俄國人勃奧魯切夫用一點點隨身帶著的俄國商品,換取了一大批文書經卷”(見《道士塔》原文,下同)之年,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日俄兩大帝國為爭奪中國東北正進行著臭名昭著的日俄戰爭。
1907年,即“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疊子銀元換取了二十四大箱經卷、五箱織絹和繪畫”之年,在中國,秋瑾被殺。
1908年,即“法國人伯希和用少量銀元換去了十大車、六千多卷寫本和畫卷”之年,中國的光緒皇帝、慈禧太后相繼死去,不滿3歲的溥儀即位。
1911年,即“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難以想象的低價換取了三百多卷寫本和兩尊唐塑”之年,中國正爆發黃花崗起義、保路運動和武昌起義。
1914年,即“斯坦因第二次又來,仍用一點銀元換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經卷”之年,在中國,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會,廢除《臨時約法》,頒布《中華民國約法》,改內閣制為總統制,正忙于復辟帝制。這一年的秋天,日本借口對德宣戰,侵入我國山東,取代德國,并以支持袁世凱當皇帝為條件,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
將并不遙遠的百年前的中西方拉在一塊兒進行比較,對比鮮明,對學生產生了強大的沖擊力,他們感慨唏噓,激昂憤恨,開始深入思考。這時,老師再讓他們找找文中還有哪些對比,他們很快發現:
中國政府官員對中國優秀文化遺產的冷漠無知不重視,與歐美的學者、漢學家、考古家、冒險家的不遠萬里,不辭辛勞,不畏艱險,對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中的中國優秀文化遺產執著追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歐美的學者、漢學家、考古家、冒險家,來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以前以為它守護森嚴,此行將充滿風險的心理,與來后的暢通無阻,如入無人之境的實際情況形成對比。
愚昧的中國道士與狡詐的西方掠奪者也構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的道士不識貨,是一個愚蠢的敗家子:用石灰將展示著“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的洞窟壁畫粉刷一新以求屋子亮堂;用鐵錘將有著“婀娜的體態,柔美的淺笑”的洞窟雕塑敲碎重塑天師和靈官;賤價出賣——幾乎是奉送——祖國的優秀文化遺產;中國的道士被西方掠奪者欺騙卻不自知。“王道士頻頻點頭,深深鞠躬,還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稱斯坦因為‘司大人諱代諾,稱伯希和為‘貝大人諱希和”,“他依依惜別,感謝司大人、貝大人的‘布施。車隊已經駛遠,他還站在路口。”而西方掠奪者除了能用超低價購買之外,還把自己扮作“倒溯著唐僧的腳印,從印度到中國取經”的“洋唐僧”以打消王道士的猶豫。
運到京城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文物,與運到國外的命運也有鮮明的對比。前者“沒裝木箱,只用席子亂捆,沿途官員伸手進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兒歇腳又得留下幾捆,結果,到京城時已零零落落,不成樣子”。而從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運送文物回到國外的斯坦因們,“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他們的學術報告和探險報告,時時激起如雷的掌聲。”
對文物、對文化的態度——重視與否,公眾的參與度如何,知曉度如何——截然不同。兩種文明的命運、兩種國家的命運、人的素質差異由此可見一斑。
從文中,學生們還看到了當年的敦煌文物的“看管者”、破壞者、敗家子與當今為國爭光的敦煌學研究者之間的對比;當今的愛國者、愛這個國家的文化遺產的青年詩人、本文作者余秋雨先生與當年賣國的王道士之間的對比……
經過一系列對比,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不難看出,中國當時正處于內憂外患之中,腐敗的政府,“沒有那副赤腸”的拙劣的官員,愚昧的人民,自保尚且無暇,根本不可能對敦煌莫高窟提供有效的保護。敦煌莫高窟的劫難難以避免!這是民族的悲劇。
二
在進行了一系列的對比之后,面對列強的掠奪,作者寫道:
他們都是富有實干精神的學者,在學術上,我可以佩服他們。但是,他們的論述中遺忘了一些極基本的前提。出來辯駁為時已晚,我心頭只是浮現出一個當代中國青年的幾行詩句,那是他寫給火燒圓明園的額爾金勛爵的《我好恨》:
恨我沒早生一個世紀/使我能與你對視著站立在/陰森幽暗的古堡……決勝負于城下
對于這批學者,這些詩句或許太硬。但我確實想用這種方式,攔住他們的車隊。對視著,站立在沙漠里。他們會說,你們無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個地方,坐下來,比比學問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這么悄悄地運走祖先給我們的遺贈。
從這些話中,我們能看出作者余秋雨是怎樣一個人?他具有怎樣的品質呢?我拋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愛國的”“勇敢無畏的”“憂憤深廣的”“知識淵博的”“學術造詣高的”“自信的”,學生們七嘴八舌。
在肯定了學生們的答案之后,我又提出了一串問題:從這里能否讀出作者的優越感呢?如果作者真如詩中所寫“早生一個世紀”,他又該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他還會是享譽天下的大作家、大名人嗎?他真的和王道士有著天淵之別嗎?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改變了這一切呢?作者的優越感又從何而來呢?對我提出的這些問題,學生們興致頗高。
他們讀出了作者站在已經發展壯大了的當今中國(現實)觀照極度衰弱的晚清(歷史)時的優越感、憂憤感。
他們認為作者如果真的如詩中所寫那樣“早生一個世紀”,如果做官,余秋雨先生必和他在文中所叱罵的那些官員一樣拙劣,“沒有那副赤腸”;如果做了敦煌莫高窟的道士,余秋雨先生也必和“罪人王圓箓”沒有兩樣,因為王圓箓的眼界和思想水準就是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即我們的祖先)的眼界和思想水準,王圓箓的愚昧無知就是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愚昧無知。
余秋雨先生之所以成為余秋雨先生,全是因為時代變了,國家強大了,科學文化教育發展起來了,人們的思想覺悟、認識水平提高了,人們的視野開闊了。因此,作者余秋雨先生的優越感是這個時代給的,這個國家給的。
也許作者早就認識到這一點,他在文章的第四部分贊美了敦煌研究者,同時,也不露痕跡地贊美了這個國家。
總之,文章內涵豐厚,在不露痕跡中講了國之強弱、官之優劣、人之賢愚對文化遺產的影響。上好這一課,可以讓學生接受一次生動、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
重慶市37中 4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