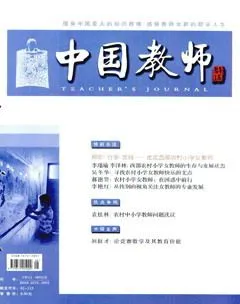讀史·史記
《史記》,由司馬遷(前145—約前86)撰寫,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史書。上起軒轅,下迄漢武,歷時數千年,包容了數百個歷史人物。本書在司馬遷逝世后才傳世,初名《太史公書》《太史公記》等,到魏晉時期,才定名為《史記》,實現了他“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宿愿。
《史記》首創我國紀傳體的史書體例,建立起本紀、世家、列傳、表、書五體結構。班固撰《漢書》,對其體例略加改動,將“本紀”改為“紀”,“書”改為“志”,去“世家”并為“列傳”,加“表”共四體,形成了“紀、傳、志、表”四體結構的斷代史史學體例,一直沿用到《明史》,成為“二十四史”的統一體例(其中有的史書有刪減),足見其影響之大。
《史記》,共一百三十篇。“本紀”十二,記帝王之事,并為各代之綱;“表”十,以列表說明各個時期的大事;“書”八,記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典章制度;“世家”三十,記諸侯、重臣等的事跡;“列傳”七十,記述各種代表人物及其他民族風情等。一部《史記》,不僅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而且為二十四史垂范。
司馬遷秉承他父親司馬談的遺志,繼任太史令。為了撰寫這部從軒轅黃帝到漢武的通史,他不但廣泛閱覽了藏書室(金匱石室)的圖書資料,而且周游全國廣泛收集有關資料和體察各地的風俗民情。正如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而歸。”回到京都之后,“仕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以后又隨從漢武帝巡狩、封禪,游歷了很多地方。這些社會實踐活動,豐富了他的歷史和社會生活知識,擴大了他的胸懷和眼界,接觸了下層群眾,增強了他與人民的聯系和感情,使《史記》具有了較強的社會性和人民性的特點。如他在《報任安書》中所講:“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其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在不幸因李陵事下獄后,他忍辱負重,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史記》的寫作中去,終于完成了這部史無前例的偉大巨著,實現了他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宏愿,完成了一樁千秋功業。
《史記》作為一部史書,不論是體例、還是內容,都是開創性的杰作;而且這樣一件巨大的工程,竟完成于他一人之手(雖少數為他人所補),這不只是空前的,也是后史無法超越的。《史記》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國外,都有著廣泛的影響,是中國人民對世界文化的卓越貢獻!這是中國人民的驕傲。現將其特點簡述如下。
一、首創紀傳體的史學體例,為后史學樹范
以人寫史,以史論人,是紀傳體的基本特點。通過紀傳體,把歷史編年和論事結合起來,使記事和論人更為完整,避免一事一人的分割和支離,給讀者以完整的概念和系統。《史記》中所寫的人物,包括了社會各個階層的人物,反映出社會各個方面的情況和問題。正如梁啟超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一書中對《史記》所作的評述:“后世諸史的列傳,多借史以傳人;《史記》的列傳,惟借人以明史。故與社會無大關系之人,濫竽者少。換一方面看,立傳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與社會各部分有關系之事業,皆有傳為之代表。以行文而論,每敘一人,能將其面目活現。又極復雜之事項——例如《貨殖列傳》《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等所敘,皆能剖析條理,縝密而清晰,其才力固自夐絕。”日本史學家齋藤正謙在《史記會注考證》中也說過這樣的話:“子長(司馬遷字子長)同敘智者,子房有子房風姿,陳平有陳平風姿。同敘勇者,廉頗有廉頗面目,樊噲有樊噲面目。同敘刺客,豫讓之與專諸,聶政之與荊軻,才一出語,乃覺口氣各不同。……讀一部《史記》,如直接當事人,親睹其事,親聞其語,使人乍喜乍愕,乍懼乍泣,不能自止,是子長敘事入神處。”(轉引自《西漢文學史參考資料》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434頁)這些評論是比較全面和中肯的。《史記》通過不同人物的描述和評說,勾畫出了一部波瀾壯闊的史卷,再加以“表”、“書”的整理和補充,使世系和典章制度更加系統化和概括化,建構起紀傳體完整的史學體系。
《史記》除了通過以人寫史,充分表現出對政治和文化的重視外,還專寫了經濟和技術等方面的問題,如《貨殖列傳》《河渠書》《平準書》等,這在當時來說,也是難能可貴的。
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除了贊揚他所作《史記》的“詳”和“勤”而外,并贊揚說:“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在贊揚他的突出特點和優點之外,還批評他是“是非頗謬于圣人,論天道則先黃老而后六經,敘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弊也。”班固的這些非議,正從反面反映出《史記》的反傳統的觀點和獨樹一幟的風格。
二、尊重事實,不為流俗的尊卑所限
在這個問題上,《史記》的表現是極為突出的。如“本紀”一般是寫帝王的傳記,但《史記》也給項羽寫了《項羽本紀》,與《高祖本紀》并列,而且無論是記事和行文都不亞于《高祖本紀》。如說項羽少時,棄書與劍,而要“學萬人敵”;直至寫到最后兵敗烏江,認為無顏見江東父老,自刎而終,其英雄本色躍然紙上。為什么要將項羽提升為“本紀”呢?因為從公元前209年起義反秦,到入關滅秦、封王,以及以后的楚漢戰爭,直到公元前202年項羽戰敗自刎,項羽在其中扮演著主要角色,因而對項羽也應寫“本紀”,以補秦楚之際的空間,這是歷史事實。這個問題,如果于司馬遷在世之時揭出,是要殺頭的,但為尊重事實,他卻置生死于不顧。
再如《史記》為陳勝、吳廣寫了《陳涉世家》,這也是一種超俗之作。“世家”原為春秋戰國時的諸侯和蕭何、張良等重宰以及如至圣孔子等人而作的。像陳勝吳廣這樣的庶民和隸卒在當時是難以入史的,但司馬遷卻把他們寫入“世家”之列,因為揭竿而起、首先發難反秦的是他們,還不是項、劉。如司馬遷在《秦楚之際月表》中所云:“初作難,發于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于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正是因為這樣,才為陳涉寫“世家”,為項羽寫“本紀”,這是司馬遷的“春秋筆法”與高尚史德的具體表現。
他為社會下層人物寫列傳和作評說的還有:如在《游俠列傳》中,稱朱家的“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郭解的“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以及游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諾必成,不愛其軀”等的描述,都寫得生動、真實、豐滿,而且飽含激情,使讀者如臨其境,如見其人,反映出司馬遷對社會下層人員的重視和反傳統觀念的高尚品格。
三、秉春秋筆法,敢于直言評說
整個《史記》,都表現出這種精神,現僅舉幾例來做說明。
在《史記》中,不但敢于斥責歷史上的暴君,而且敢于對當代的帝王評議其所短。如在《留候世家》中,寫了“沛公(即劉邦)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居留之”的貪財好色的惡習;借商山四皓之口批評劉邦“陛下輕言善罵”的不良作風。再如在《蕭何世家》中,記述了劉邦如何猜忌功臣;在《淮陰侯列傳》中,用韓信之口喊出“狡兔死,走狗烹”,控訴了劉氏對功臣的殘害。在《孝景本紀》中,在指出“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的同時,又指責漢文帝“賞太輕、罰太重”,以及反襯出景帝無能等問題。在《孝武本紀》中,說他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并通過《封禪書》暗示對漢武帝迷信的諷譏。如此等等,不勝枚舉。所有這些,都是在太歲頭上動土,會招致滅頂之災、殺身之禍的。他為了忠于事實,能講別人之不敢說,敢做別人之不敢為,表現出一位史學家的錚錚鐵骨和高風亮節。
四、文風樸實犀利,為散文進一步發展奠基
以人寫史,是《史記》的偉大創舉。在司馬遷的筆下,各種人物,無論是臧、是否,是褒、是貶,都寫得栩栩如生。如“鴻門宴”一節,無論是項羽與劉邦的對話,還是項莊舞劍,樊噲保駕,劉邦匿逃,張良獻斗,范增摔斗等,都寫得活靈活現。其中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典故,成為后世常用來說明“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諺語。如此等等,不勝枚舉。《史記》在散文方面,已達到空前的造詣,為散文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史記》在敘人敘事時,還夾著一些詩歌和諺語,更增強其行文的文學色彩,如荊軻刺秦在別燕太子丹時的易水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其悲壯凄涼,催人淚下。在《淮陰侯列傳》中,通過韓信的口講出“狡兔死,走狗烹”,形象地控訴了劉氏對功臣的殘害。再如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來對孔子進行歌頌和景仰;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來闡明對李廣將軍的追念和銘記。這些都成為后世常用的諺語,也為散文的創作創造了一條詩文結合的道路。司馬遷不止是偉大的史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文學家。“西漢文章兩司馬”,西漢有兩大文體,散文和駢文,如果說司馬相如是駢文的代表者,司馬遷則是散文的杰出代表者。魯迅對《史記》的評價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極為中肯的評論。其史德和文風,都為后世垂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