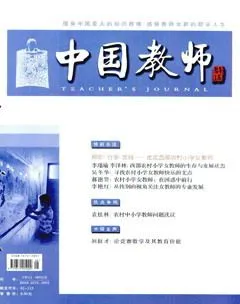“學(xué)為人師,行為世范”的歷史淵源
“學(xué)為人師,行為世范”是北京師范大學(xué)的校訓(xùn),它是啟功教授在1996年的夏天,響應(yīng)學(xué)校的校訓(xùn)征集活動(dòng)提出的。這一校訓(xùn)一經(jīng)提出,不僅立即得到了北京師范大學(xué)全校師生的高度認(rèn)同,而且很快引起了全社會(huì)的深切共鳴。除了社會(huì)各界人士在各種場(chǎng)合援用并稱贊外,很多學(xué)校尤其是師范學(xué)校的校訓(xùn)也仿效而制,表現(xiàn)出濃烈的依傍的印記。
這一校訓(xùn)之所以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它學(xué)行并重,突出了師范的意義,形式上簡(jiǎn)潔明快,恰切允當(dāng),言近而旨遠(yuǎn),辭約而意豐。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它繼承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弘揚(yáng)了中國(guó)教師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可以看做是中國(guó)兩千五百年優(yōu)秀教育傳統(tǒng)的厚積薄發(fā),也可以看做是一代又一代中國(guó)教師的鄭重誓言。
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對(duì)士人尤其是教師學(xué)和行的一貫強(qiáng)調(diào),形成了代代相傳的傳統(tǒng),結(jié)晶出眾多形式整齊、簡(jiǎn)潔明快的句式。說(shuō)到這樣的語(yǔ)句,一般都會(huì)舉列《世說(shuō)新語(yǔ)》中的那段話:“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世說(shuō)新語(yǔ).德行》)實(shí)際上,這里所標(biāo)舉的言和行,都可以歸并到行的范疇。在此之前,無(wú)論是就時(shí)間的早晚、內(nèi)容的全面,還是句式的典型而言,都另有先例。如在東漢初年,南陽(yáng)太守杜詩(shī)在向光武帝推薦伏湛的上疏中,就說(shuō)伏湛“篤信好學(xué),守死善道,經(jīng)為人師,行為儀表”。(《后漢書》卷五十六)東漢和帝之初,竇憲也上疏稱桓郁,“結(jié)發(fā)受學(xué),白首不倦,經(jīng)為人師,行為儒宗”。(《后漢紀(jì)》卷十二)漢朝末年的陳寔,在一篇碑文中稱頌主人“文為世范,行為士則”。三國(guó)時(shí)期的鄧艾,12歲讀到陳寔的碑文后,為其標(biāo)樹(shù)的境界和表述的精到而折服,“遂自名范,字士則。”(《三國(guó)志》卷二十八)與鄧艾同時(shí)的劉靖,在《請(qǐng)選立博士疏》中,建議“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jīng)任人師者,掌教國(guó)子”(《三國(guó)志》卷十五),以改變太學(xué)設(shè)立20年來(lái)少有成效的狀況。這幾則材料,都比《世說(shuō)新語(yǔ)》的說(shuō)法要早,有的要早三、四百年,而且賅括了學(xué)和行兩翼。
《世說(shuō)新語(yǔ)》之后,類似的說(shuō)法在歷史文獻(xiàn)中時(shí)有所見(jiàn)。如庾信稱頌陸逞“儀表外明,風(fēng)神內(nèi)照。器量深沉,階基不測(cè)。事君唯忠,事親唯孝。言為世范,行為士則。”(《庾子山集》卷十三)隋朝盧昌衡,在徐州做地方官時(shí),以能干著名,吏部尚書蘇威經(jīng)過(guò)考查之后,說(shuō)他“徳為人表,行為士則”,(《隋書》卷五十七)當(dāng)時(shí)以為美談。《舊唐書》的作者,贊頌唐文宗“文章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