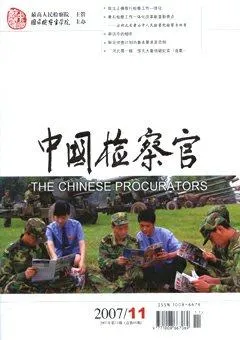我國存疑不起訴制度的若干思考
內容摘要:現行刑事訴訟法設置的存疑不起訴制度,隨著司法實踐的發展,制度本身的一些不完善之處,以及對檢制度認識上的模糊性日益暴露出來,通過分析存疑不起訴的制度價值和實踐作用,從而提出完善我國存疑不起訴制度的建議。
關鍵詞:存疑不起訴缺陷建議
現行刑事訴訟法增設了存疑不起訴制度,進一步完善了我國刑事訴訟的不起訴制度,使檢察機關公訴權的設置更趨科學、合理,公訴權的內容更加豐富、充實,更能適應復雜的公訴實踐。隨著司法實踐的發展,存疑不起訴制度本身的一些不完善之處,以及對該制度認識上的模糊性日益暴露出來,進而導致在適用法律時的不規范和混亂。
一、存疑不起訴的制度價值
(一)存疑不起訴制度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必要配置
無罪推定原則是現代刑事訴訟的一塊基石,其根本價值在于使被告人在訴訟程序上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實現一種訴訟對抗的平衡。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吸收了無罪推定原則的一些合理要素,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無罪推定原則。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基于無罪推定的證明責任分配,一般情況下,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始終由追訴機關承擔,并在不能證明被告人有罪的情況下,應當作出對被告人有利的判定。我國刑事訴訟的偵查、公訴、審判相對獨立的階段式訴訟結構,決定了在不能證明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情況下,各個訴訟階段的機關有權且應當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作出對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有利的判定,終止訴訟程序。具體體現為偵查機關可以作出撤銷案件的決定,在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可以作出存疑不起訴的決定,審判機關可以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二)存疑不起訴制度的設置是訴訟經濟和效率原則的必然要求
刑事訴訟活動不同于一般的認識活動,其證實或證偽的過程不但受一定的訴訟資源和訴訟手段的制約,而且必須在嚴格的程序法規范和限制下進行。刑事訴訟活動所查明或證明的案件事實只能是對原始案件事實的無限接近,而不可能絕對相同。刑事訴訟活動的特殊性決定了追訴機關不可能無休止地對案件事實進行查證。在案件經歷補充偵查,發現仍然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檢察機關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及時終止刑事訴訟程序,案件不再進入審判程序,可以避免有限司法資源的無謂浪費和訴訟過程的無謂拖延。
(三)存疑不起訴制度的確立符合現代刑事訴訟價值追求的基本趨勢
一切形態的刑事訴訟,都潛存著兩種基本的價值追求:安全和自由。前者追求保障社會和社會多數成員不受犯罪行為的侵害,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安全;后者追求保障社會成員個人的自由,核心內容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權利不受國家權力的非法干預和侵犯。存疑不起訴制度的設置,體現了對犯罪嫌疑人權利的保護,與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起訴制度(如起訴的條件要求)相結合,從而實現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任務。
二、存疑不起訴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的作用
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刑事訴訟的一般流程是偵查、公訴、審判、執行的前后相繼。從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模式和運作的實際情況看,庭審功能被嚴重弱化,庭審形式化傾向比較嚴重,審判前程序較之于審判程序來說對案件質量的保證更起決定性作用。
偵查活動是一項由結果探究原因的回溯性的活動,是對已發生的案件事實的再現,并且是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進行的,不但要受程序法的規制,而且受制于偵查的物質技術水平、偵查手段等客觀條件的限制。偵查活動的回溯性,以及認識主體在特定時空條件下認識能力的有限性,決定了偵查結果與案件原初事實可能出現不一致的情形。這種不一致通過偵查活動(特殊的認識活動)獲取的證據體現出來。在審查起訴階段,對于公安機關偵查終結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檢察機關經過審查得出的結論無非有三種:第一種是犯罪嫌疑人實施了某種犯罪行為,第二種是犯罪嫌疑人沒有實施某種犯罪行為,第三種是犯罪嫌疑人是否實施某種犯罪行為處于真偽不明的狀態。
在上列的第三種情況下,真偽不明的狀況實際上包括兩種情況:一是犯罪嫌疑人確實實施了某種犯罪行為,但憑現有的證據情況不能認定其有罪;二是犯罪嫌疑人確實未實施某種犯罪行為或犯罪行為并非犯罪嫌疑人所為,但根據現有證據情況無法認定其無罪。這樣的真偽不明狀況出現后,由于訴訟活動的特殊性,要求司法機關對業已啟動進行的訴訟活動及結果必須作出結論。具體到審查起訴階段,在既不能提起公訴又不能認定犯罪嫌疑人無罪的情況下,檢察機關又不能不作出結論,因此審查起訴階段需要設置存疑不起訴制度來解決這一問題。這在國外的刑事訴訟立法中也有所體現,如英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如果檢察官認為案件的證據不充分,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據資料統計,在英國經過檢察機關審查后的案件,決定不起訴的占12%,其中70%是因證據不足而決定不起訴。日本的刑事訴訟中,當案件欠缺訴訟條件及被疑事實不構成犯罪或沒有犯罪嫌疑時,檢察官應作出不起訴處分。從存疑不起訴適用的對象看,對于第一種情況,存疑不起訴制度可以起到保護犯罪嫌疑人權利的作用。既然無法從法律上判定其有罪,提起公訴后,法院也會對其作出無罪判決。為實現程序正義,不將此類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交付審判,可以使其早日從訴訟中解脫出來。雖說從事實層面不能否定他有罪,但給予其公正的訴訟待遇,使其享有應有的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對第二種情況,則可以起到防止錯誤起訴,錯誤交付審判情況的發生,最大限度地避免無罪的人受到錯誤審判,防止錯案發生,保護無辜的作用。
三、我國存疑不起訴制度的缺陷
(一)在配套制度的設計上,仍體現了強烈的追訴傾向,使存疑不起訴制度承載了其不應有的追訴職能
從立法邏輯上講,刑事訴訟法第三章已經規定了完整的起訴制度,檢察機關追訴犯罪的職能完全可以通過起訴制度來實現,存疑不起訴制度的設計目的是為了解決案件事實處于真偽不明狀態,犯罪嫌疑人罪與非罪無法確定,檢察機關又不能拒絕作出判定的問題。從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偵、控、審分工協作來看,在一般情況下檢察機關并不具有偵查權力(職務犯罪偵查、審查起訴階段的補充偵查等除外)。易言之,一般情況下,未經偵查機關偵查終結將案件移送審查起訴,檢察機關主動啟動刑事訴訟程序于法無據。檢察機關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從法律上即推定被不起訴人無罪,是終結訴訟程序而不是中止訴訟程序,此后,未經偵查,檢察機關直接提起公訴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在存疑不起訴制度設置之前,我國在司法實踐中的做法是疑案從無,疑案從掛,疑案從拖,極大地損害了訴訟活動的嚴肅性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威信。《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以下簡稱《規則》)規定檢察機關在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之后,在發現新的證據,符合起訴條件時,仍可以提起公訴,并且沒有規定是否受訴訟時效的限制。這就相當于一方面宣告被不起訴人在法律上是無罪的,但又同時告訴公眾檢察機關把無罪的人仍當作犯罪嫌疑人對待。無罪的決定已經作出,卻無法解除犯罪嫌疑人有罪的束縛,這是自相矛盾的。同時沒有追訴時效的限制,相當于雖然形式上宣告了被不起訴人無罪,但又沒有限制地將案件掛了起來,又似乎回到了以前的“疑案從掛”的老套路上,使存疑不起訴的公信力受到嚴重影響。
從實際情況看,在檢察機關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之后,極少有發現新的證據,符合起訴條件,再次提起公訴的情況發生。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規則》第二百八十七條的規定缺乏實益性和現實基礎。實際上,對追訴程序的啟動,完全沒有必要作出《規則》第二百八十七條這樣的規定。當有新的證據或證據線索時,在追訴時效期限內,可以由偵查機關依法啟動立案偵查程序,偵查之后作為新案件移送審查起訴,這時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則是名正言順的了。雖然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導致偵查資源的重復使用,但卻是程序正義和偵、訴機關權力配置的必然要求。
(二)對存疑不起訴案件被害人的權利保護規定的比較充分,而未規定被不起訴人的救濟權利
無論是刑事訴訟法還是《規則》都沒有規定被不起訴人的救濟權利。從前文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存疑不起訴的被不起訴人有些確實是無罪的,對其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從法律角度上來講,他就是無罪的。但從社會事實層面上講,他仍然戴著“犯罪嫌疑人”的帽子,《規則》第二百八十七條的規定使這頂帽子變得更加沉重。從法的感情上來講,被不起訴人對存疑不起訴決定是無法認同的。但法律并未賦予被不起訴人的救濟權利的途徑,這明顯是不公平的。
(三)現行存疑不起訴制度對司法工作人員可能利用存疑不起訴放縱犯罪嫌疑人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但對司法工作人員可能利用存疑不起訴侵犯被不起訴人的權利則關注不夠
從刑事訴訟法和《規則》的規定來看,無論是檢察機關內部的制約程序(如存疑不起訴必須經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還是外部的公安機關的要求復議、復核的權利,被害人的申訴和自行起訴的權利,以及須經補充偵查才可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的限制,都體現了防止濫用不起訴權力放縱犯罪的意圖。
但對司法工作人員可能利用存疑不起訴侵犯被不起訴人合法權益的情況,則明顯關注不夠。如沒有設置關于利用存疑不起訴侵犯被不起訴人合法權益的禁止性規定。司法實踐中,討論決定存疑不起訴時,往往是也從能否證明被不起訴人有罪的角度出發的,而不是從能否證明被不起訴人無罪的角度出發。《規則》僅規定了發現新的證據時檢察機關可以起訴,但新證據的性質應當有兩種:一種是證明被不起訴人有罪,一種是證明被不起訴人無罪。對發現證明被不起訴人無罪的新證據的情形,檢察機關應如何處理及處理的程序則缺乏相應的規定。
四、我國存疑不起訴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弊端
由于存疑不起訴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導致其應有的法律價值不能被正確地認識,甚至該制度被扭曲適用。部分司法工作人員有罪推定的思維慣性進一步被強化,把存疑不起訴作為一種追訴犯罪的手段使用,體現出強烈的追訴傾向,對被害人和被不起訴人的保護明顯失衡。刑事訴訟法對公安機關該立案而未立案的情況,賦予了檢察機關的立案監督權,但對公安機關不該立案而立案的外部監督制約則明顯不力。立案偵查環節的靠公安機關的自律而不是他律來制約的,這樣導致了刑事訴訟程序啟動時一定的隨意性,偵查活動的一定的肆意性。根據目前的實際情況,審查起訴不可能像審判環節那樣實行直接言詞原則(就是審判環節這一原則目前也未能徹底貫徹),審查起訴基本上是以公安機關移送的案卷材料為基礎進行的書面審查,信任偵查行為是一個潛在的前提。這樣部分被錯誤立案偵查的案件進入審查起訴階段,檢察機關在經過補充偵查后,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偵查的隨意性。有些地方,明明知道案件錯了,為了逃避上級部門的檢查和自己的責任,牽強附會地作出存疑不起訴決定。更有甚者,把《規則》第二百八十七條的規定作為對抗被不起訴人要求國家賠償的手段。
這種不完善嚴重扭曲存疑不起訴制度的功能,有損訴訟公正。確系無罪的被不起訴人雖然在法律上被推定為無罪,但在社會生活層面上仍然是“犯罪嫌疑人”,對這種“犯罪嫌疑人”法律沒有賦予任何的洗刷冤屈的途徑,這無論如何是不可接受的,最終也會損害存疑不起訴制度的法律的公信力,使這項制度背離正確的方向。
五、對完善我國存疑不起訴制度的幾點建議
一是立法和司法解釋不能背離設立存疑不起訴制度的根本目的,不能讓存疑不起訴承載其不應當承載的追訴犯罪的功能。
二是對于作出存疑不起訴的案件,即使發現新的證據,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由公安機關重新啟動訴訟程序而不是由檢察機關直接予以追訴,并且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應受追訴時效的約束。
三是在賦予被害人救濟權利的同時,應賦予被不起訴人救濟的權利,以平衡被不起訴人與被害人的權利,特別是在發現新的證據證明被不起訴人無罪的時候,應當給予被不起訴人申訴的權利,撤銷不起訴決定,使被不起訴人無論從法律上還是事實層面上均被宣告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