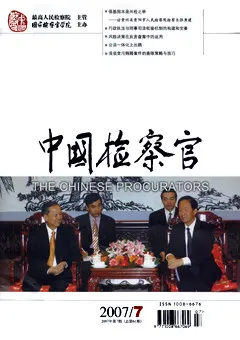論網絡環境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取證問題
內容摘要:網絡環境下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在取證方面存在著三個主要問題,即網絡搜查對象的概括性與司法令狀原則的特定性要求之間的沖突問題;網絡搜查的秘密性與令狀原則的權利救濟之間的沖突問題;網絡搜查的協助問題。
關鍵詞:網絡搜查 司法令狀 權利救濟
網絡環境下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已成為新形態的犯罪行為。尤其是在電子商務領域侵犯著作權犯罪的發展態勢不容樂觀。具體而言,其主要表現形式為:一是商業網站免費提供MP3音樂下載;二是盜版軟件公司通過電子郵件傾銷盜版軟件;三是商業網站提供免費下載他人享有著作權的軟件服務;四是商業網站抄襲他人網頁;五是商業媒體侵犯文字作品著作權,例如將傳統介質形式的文字作品上傳到網絡或是在網絡之間互載,以及將網頁上的作品下載到其他媒體發表。[1]電子商務與傳統的有形市場并無本質區別,而傳統的紙介質與網絡介質也沒有本質上的區分,網絡環境只不過是將紙介質作品以數字化形態存儲,變成軟盤、硬盤、CD-ROM,最后又把內容輸入到網絡空間組合成網頁,形成了網絡作品。借助計算機信息網絡技術,如傳輸、復制、上傳、下載等,將作品數字化轉化為網絡作品,同樣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網絡環境下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行為在本質上仍然屬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
在刑事偵查層面上,網絡環境下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與傳統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相比較,具有匿名性、隱秘性等特征,犯罪留下的證據少,涉案地區廣,并且犯罪嫌疑人通常采取加密的手段對證據加以保護,這為網絡環境下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偵查工作帶來了困難。取證對象是以數字化形式表現的“無形的信息”,犯罪嫌疑人容易毀滅證據,如果不能及時搜查和扣押,會影響到證據的證明力。鑒于此,各國紛紛在刑事訴訟法中對網絡環境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偵查活動做出特別的立法規定,通過立法明確規定電子資料的搜查、扣押,如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19條第4款規定,在具備法定情形下,警察對存儲于計算機之中且在該場所里即可獲取的任何信息,都可以要求將其轉化成有形且可讀的、能被帶走的形式予以扣押。我國臺灣地區2001年修改《刑事訴訟法》時,在該法第122條中規定物體(有體物)及電磁記錄(無體物)均構成搜查的客體,第133條再次明確規定,可為證據或沒收之物,得扣押之。對于應扣押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得命其提出或交付。所謂“電磁記錄”是指,以電子磁性或其他無法以人之知覺直接認識之方式所制成的記錄,而供電腦處理之用者。[2]當前,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法工作已提上了立法的議程,如何在新的《刑事訴訟法》中對網絡犯罪這種新型的犯罪形態的取證問題做出回應是立法者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具體而言,筆者認為網絡環境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取證活動在我國存在著三個方面的突出問題。
一、網絡搜查對象的概括性與司法令狀原則的特定性要求之間的沖突問題
司法令狀是法治國家中通過司法抑制偵查權的一種有效方式。強制偵查必須事先經過獨立的司法機關批準,在司法令狀限定的范圍內實施。網絡搜查與傳統偵查都是國家對個人基本權利進行干預的行為,因此都需要令狀予以約束。但令狀原則誕生之時,并不存在網絡搜查,換言之,設計令狀制度的最初目的是約束傳統的偵查行為,因此網絡搜查的產生發展必然對司法令狀原則帶來沖擊和挑戰。具體而言,網絡搜查對象的概括性與司法令狀原則的特定性要求之間存在著沖突。
特定性要求是令狀形式要件的主要內容。令狀的特定性就是要求所有的令狀必須有具體的范圍,需要搜查、扣押的人或物,執行搜查扣押的地點,以及令狀的有效期限。特定性要求的目的在于禁止簽發普通令狀(general warrant),以防止漫無邊際的強制偵查。傳統的偵查以物理侵入方式為主,其對象和范圍具有可預測性,因此執法人員易于事前確定,而技術偵查難以事前明確限定搜查對象,尤其是監聽和網絡搜查。對于后者,電腦網絡在跨地區處理、傳送大量資料時,為了保證傳輸過程中資料的秘密性,通常要將其傳輸信息采取加密措施,因此如果無法得知解密的程序,將無法判別其內容。電腦網絡是由多數人所共用,所以多數人的信息資料通常會在一起傳送,因此執行網絡搜查難免會影響到與案件無關的第三人的隱私權利。再加之,電腦內儲存的資料可能與其它的文件相混合,通過肉眼的直接觀察難以識別,因此其令狀的特定性難以與傳統偵查相比。所以在網絡搜查中如果嚴格遵守令狀特定性要求,將很難達到搜查的目的。
鑒于網絡搜查中搜查對象的特殊性,西方主要法治國家均將司法令狀的特定性要求做了靈活的調整,以加大打擊網絡環境下打擊犯罪行為的力度。例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例明確允許某種程度上對網絡電子資料進行概括性扣押,具體如在搜查令上以關于某特定行為的“通信文件、字條、帳冊或其他記錄”為對象,但根據該搜查令而扣押的少量的電子資料,法院同樣認可扣押的合法性。[3]日本的司法實務中也存在著類似的做法,日本的實務界和學界大多數觀點認為,從確保偵查搜查實效實質考量,應當承認網絡搜查的概括性特征。例如,日本大阪高等法院在1995年的一個判決中提出,因為在網絡搜查中現場確認內容具有技術性的困難,加上有遭受毀滅罪證的危險性存在,所以沒有在搜查令狀中明確記載扣押的電子資料,雖然屬于概括性的扣押,但仍然是合法的。
二、網絡搜查的秘密性與令狀原則的權利救濟的沖突問題
技術革命的重要內容就是信息技術革命,而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使政府能夠放棄利用身體的直接接觸而獲取信息的傳統偵查手段而采取更為精密和遠程的方式并且更為有效地得知密室里耳語的內容。[4]技術偵查往往是在相對人并不知情的狀態下進行的,因此它具有秘密性特征。網絡搜查屬于技術偵查中的重要手段,因此具有秘密性特征。鑒于此,網絡搜查無須直接接觸被偵查者,從而沒有對他人施以直接或間接強制力。由于最初的搜查行為主要表現為破門而入、翻箱倒柜,因此司法令狀原則的最初目的是通過嚴格的程序來約束具有直接強制力的物理性搜查行為。詳言之,令狀的救濟制度實質上就是公民在令狀簽發之后,或者令狀已被執行之后,或者在無令狀授權的前提下被執行強制處分之后,向法院申請對令狀和強制處分進行事后司法審查的制度。一般的住宅搜查中,有的國家規定了“敲門并宣告”原則,對被搜查者的知情權給予充分的保障。[5]在執行令狀過程中賦予被搜查者獲取律師幫助權和在場監督權是各國的普遍做法。如果需要對嫌疑人進行強制性手術以獲取體內的證據時,有的國家還在執行令狀之前給予嫌疑人多次聽審機會和上訴機會。[6]但是網絡搜查的秘密性決定了偵查行為實施之前以及實施過程中,被偵查人可能并不知情,因此無法獲知自己涉嫌的罪名、也無法享有沉默權、請求調查有利證據和獲取律師幫助以及表達意見的權利,更無法對令狀執行過程行使在場監督權。為了彌補事前司法審查(因為令狀的特定性不明顯)和事中監督的不足,更應當加強對技術偵查的事后監督和對被偵查人及相對人的司法救濟。例如規定在技術偵查實施之后及時書面通知被偵查人和相對人,書面通知中應記載令狀的主要內容,并告訴被偵查人和相對人其有權向法院申請撤消和變更技術偵查行為。此外,被偵查人和相對人有權獲取律師幫助,并有權聽取、查閱和復制技術偵查所記錄的相關部分材料,但法院如果認為可能妨害偵查目的或無法通知被偵查人及相對人時,不在此限,一旦原因消滅,應當及時補充通知。搜查、扣押行為本身可以在偵查行為相對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秘密進行,甚至在偵查行為結束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也可能仍不知情,因此,應當加強對網絡搜查的事后救濟保障,以防止偵查機關濫用網絡搜查權。
此外,網絡搜查扣押極易涉及各種秘密、侵犯第三人的隱私權和財產權,以及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造成損害,筆者認為,我國在修改刑事訴訟法時對上述問題應當注意四個方面:首先,必須明確偵查機關對于在收集電子資料過程中涉及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應當保密;其次,偵查機關收集電子資料,應當嚴格依據有關技術規范進行,注意保護當事人和相關人的合法利益;再次,在資料的利用和處理方面,應當注意保守秘密及保護當事人的合法利益。例如對不構成犯罪的,搜查、扣押的電子資料應當依法定程序予以銷毀或者返還等。最后,偵查機關違反法律規定或技術規范收集電子資料,致使當事人和相關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為此,立法應當明確受害人賠償申請的提出,受理機關、賠償義務機關及救濟程序等。
三、網絡搜查的協助問題
網絡上的侵權者處于隱秘狀態,其登陸的資料,提供的電子郵箱往往采取了保密措施,因此,和傳統的偵查取證不同,網絡搜查需要網絡營運商和專家的協助。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有義務按照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的要求,提供可以證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互聯單位、接入單位及使用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的法人和其他組織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保留有關原始記錄,并在24小時內向當地公安機關報告:發現有利用國際聯網危害國家安全、泄露國家秘密,侵犯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權益,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的;利用國際聯網制作、復制、查閱和傳播違法信息的,從事危害計算機信息網絡安全活動的;利益國際聯網侵犯用戶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等。公安部《關于執行<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中有關問題的通知》指出,有關原始記錄是指有關信息或行為在網上出現或發生時,計算機記錄、存儲的所有相關數據,包括時間、內容(如圖像、文字、聲音)、來源(如IP地址、EMAIL地址等)及系統網絡運行日志、用戶使用日志等。國務院《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發現其網站傳輸的信息明顯屬于禁止傳輸的內容的,應當立即停止傳輸,保存有關記錄,并向國家有關機關報告。因此,我國現行立法上針對了網絡搜查中電子資料易于更改和毀滅的特點特別強調了有關機關的協助義務,一方面強調偵查機關有權要求從事國際聯網業務的單位和個人提供信息、資料和數據,[7]另一方面還賦予了從事國際聯網業務的單位和個人、互聯單位、接入單位及使用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互聯網的法人、其他組織和個人發現犯罪時及時保留有關原始記錄并在規定時間內向公安機關報告的義務。[8]換言之,網絡營運商及其他單位和個人均不得以保護客戶的通訊自由或通訊秘密為由拒絕偵查機關的協助要求。這一點對于網絡環境下的犯罪偵查活動尤為必要。
但是,立法存在著過于寬泛的缺點,對網絡搜查中的特殊問題沒有做出具體回應,從而不利于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例如,網絡搜查、截取計算機網絡傳輸的信息需要專門技術及設備,而偵查機關并不享有強制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協助的義務,不能強制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協助打開網絡上的記錄,因此需要具有專業技能的人士在場,以協助警察進行網絡搜查。美國部分州規定隨行專家要列名在搜查令上,才能對網絡搜查進行協助,否則在其協助下
獲取的證據將被法院作為非法證據而排除[9]。
注釋:
[1]趙秉志、田宏杰著:《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頁。
[2]廖又生:《網絡著作權之刑事訴究問題》,載(臺)《圖書館學會會報》第72期。
[3]U.S.v.M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