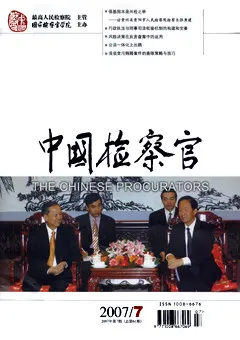論“公訴引導偵查”的實現途徑
內容摘要: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我國的檢警關系是“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但由于長期大公安為主導的慣性,在司法實踐中往往是公訴與偵查張力有余,配合不足,難以形成有力的“大控方“格局,導致了一定程度上的偵控效率低下、司法資源浪費和偵查權力失控。本文從我國偵訴關系的現狀出發,分析目前存在的問題,探討了偵訴關系的發展趨勢,由此為基礎論證了公訴引導偵查的積極意義,并對引導的有效途徑和方法加以構想,以期對司法實踐有所助益。
關鍵詞:偵訴關系 公訴引導偵查 實現途徑
根據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承擔公訴責任的檢察機關與最大偵查主體公安機關的關系是“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而審判模式又以“司法裁判為中心,控辯雙方進行有效對抗”為主線,這樣的審判模式對公訴機關提出了更高的舉證能力要求,但“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偵訴模式再加上傳統的“大公安”為主導的司法慣性,使得實踐中偵訴雙方往往配合不足,公訴部門對偵查機關也制約無力,進而造成了偵控質量不高、訴訟效率低下、偵查權利擴張等問題的存在。
一、我國現行“偵、訴關系”的弊端
根據《憲法》《檢察院組織法》的規定,承擔公訴責任的檢察機關是國家的專門法律監督機關,其對于刑事司法活動中的偵查機關進行法律監督是一項憲法性職責,但遺憾的是由于監督的范圍、方式、法律后果都沒有明確規定,而且現有法律并沒有明確賦予檢察機關對偵查活動的指導權,再加上我國警察機關因保障社會治安的特殊防范功能而形成的傳統強大地位,使得檢察機關的“監督”軟弱無力,造成偵查機關在偵查活動中自行其是,偏離服務公訴的目的,公訴機關對偵查機關難以制約,退補也時常發生退而不補的現象[1]。
偵查偏離公訴的目的,偵訴未能形成有機一體的大控方,從而引發一系列問題:
第一,部分案件的偵查質量仍然偏低,難以適應新的庭審要求。偵查機關作為偵查部門與庭審之間沒有直接聯系,對庭審的要求難以掌握,在缺乏公訴機關指導的情況下,往往發生偵查質量問題。具體表現在移送審查起訴案件所取證據達不到庭審控訴標準,退補率仍然居高,退補質量尚難令人滿意。尤其是對一些新型犯罪、疑難復雜的重大團伙或經濟類型犯罪等,偵查機關的取證時有偏離庭審證據要求的方向。
第二,犯罪嫌疑人地位被客體化,訴訟當事人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偵查由偵查機關單方實施、控制,偵查機關的偵查活動不可避免的以追求破案、懲治犯罪為目的,這種思想指導下且缺乏其他部門制約,必然導致犯罪嫌疑人的主體地位客體化,為保證所追求的效率,偵查機關會天然排斥辯護律師的參與,盡管我國現行刑訴法在修改時增加了偵查階段律師可以介入的規定,但在實踐中卻是會見難、申請變更強制措施更難,使得“律師介入偵查”制度形同虛設,從而遏制了辯護制度的發展,影響到訴訟當事人權益的有效維護。
第三,偵查機關的偵查活動缺乏合理控制,成為司法腐敗的潛在危險。由于整個偵查階段承擔法律監督職責的公訴機關都難以介入,所以進行監督往往只能在審查起訴期間對偵查機關取得的各種材料進行書面審查,這種事后監督書面監督的被動性使得監督效果大打折扣,偵查權力的潛在擴張性,使得個別時候異變為“法外特權”,另外在偵查中較大的隨意裁量權、處置權也成為誘發司法腐敗的潛在危險。
二、建立公訴引導偵查偵訴關系的理由與基礎
公訴引導偵查是指公訴機關以國家公訴人的法律身份,按照一定的規則和標準,引導偵查工作中證據的搜集、提取、固定及偵查取證的方向,提出意見和建議,并對偵查活動進行法律監督的,以保證偵查工作的公正、效率和質量的活動。實行公訴引導偵查既符合世界司法潮流,也符合我國實際國情和現行法律的規定。
(一)偵、訴關系的發展趨勢———折衷化
大陸法系的國家普遍用法律規定“偵、訴結合”的偵訴關系,即公訴機關在一定程度上領導、指揮和監督著偵查機關。公訴機關是法定的形式上的偵查主體,是偵查程序中的主導和中心,負責監督和指揮警察機關進行偵查,例如在德國[2]、法國[3]、意大利[4]等國家檢察機關對警察都有指揮的權力。英美法系國家則多從立法上建立“偵、訴”分離的模式,即公訴機關一般不直接行使偵查權,偵查權與控訴權相對分離,偵查機關與公訴機關也相對獨立,例如英國、美國[5]等國家公訴機關與偵查機關就在法律上處于平等地位。兩大法系的國家由于歷史傳承的區別、文化背景的差異在立法中各自選擇了不同的體制,但司法實踐的不斷校正卻使得各個國家紛紛轉向了折衷化的選擇,因為偵、訴結合雖然使控方力量強大,節省司法資源有利于打擊犯罪,但控辯力量的失衡使嫌疑人的人權保障存在潛在缺陷;偵、訴分立模式則使嫌疑人的訴訟主體地位得到保護,但缺點則是偵控之間脫節,訴訟效率低下,偵查活動缺少監督,容易發生偵查機關濫用職權或怠于追訴。因而偵訴結合的國家逐漸加入“分立”的因素,例如德國就宣布對于中等以下的刑事案件,均由警察獨立進行偵查,案情基本確定以后,才交給檢察官。與此同時,許多偵、訴分立的國家也出現了要求檢察機關更多的參與偵查、提出偵查建議和監督偵查等強化指導的呼聲,例如英國的皇家刑事司法委員會已提出建議,要求檢察機關在偵查階段給予警察必要的司法建議,指導警察收集和發現充分的,能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據[6]。
(二)建立“公訴引導偵查”的偵、訴關系是我國現行法律框架下的現實出路
1.公訴引導偵查的必要性。在刑事訴訟中,偵查機關、控訴機關具有相同的任務———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為此公安機關需在偵查階段發現、收集、固定證據,公訴機關則需要對偵查所得的證據加以審查、鑒別、運用,不難看出,證據是二機關參與訴訟活動圍繞的核心,新的庭審方式更是要求公訴機關能夠在當庭以充分有效的證據說服合議庭以獲取勝訴從而實現對犯罪的追訴。因此,偵查、公訴機關必須在訴訟證據的收集上加強配合,形成合力,才能共同完成追訴犯罪的任務,公訴引導偵查正是公安、檢察機關相互配合的切入點,從而有效的改善偵查質量。
公訴引導偵查能夠提高司法效率,節約訴訟資源。刑事發案率逐年上升而司法資源的投入在一定時間內必然有限的客觀現實決定司法活動在追求公正的同時必然追求效率,公訴引導偵查因為公訴人員的介入與幫助可以縮短偵查辦案期間,避免重復性偵查活動,從而提高訴訟效率。
公訴引導偵查可以更好的實現檢察法律監督,保障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公訴機關對偵查的引導可以防止偵查機關非法取證,介入偵查后的監督與案件偵查終結移送到公訴機關進行審查時再啟動的事后監督相比,效果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2.公訴引導偵查的可行性。在筆者從事的審查起訴工作中,經常遇有偵查人員要求退補提綱列得細一些或在偵查案件階段就某方面問題與公訴人進行探討;再例如筆者所在公訴部門曾經在2007年就本地區販賣到盜版光盤案件數量激增,而公安機關對嫌疑人是否具有音像制品經營許可證的證據普遍調取不力的情況進行取證的引導,得到公安機關的歡迎,這些表明公訴機關對偵查進行指導是必要且有可行現實基礎的;而談到法律基礎,根基在于我國《憲法》賦予了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權利,明確規定檢察機關為專門法律監督機關。《刑事訴訟法》第140條第1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機關提供法庭審判所必需的證據材料。這里的“可以”實際上是賦予檢察院享有可以引導取證的權力。同時該法第140條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