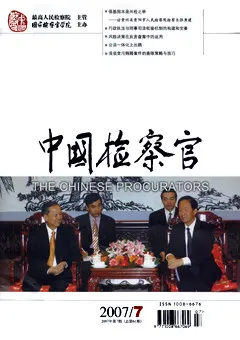論緊急避險中危險源的限制
內容摘要:關于緊急避險的危險源,我國《刑法》中缺乏明確規定,導致刑法理論界和司法實務中對此存在一些認識上的分歧。緊急避險危險源的正確界定的關鍵在于自招危險的處理。對此問題,應該結合自招危險的具體情形加以具體分析。
關鍵詞:緊急避險 自招危險
根據我國現行《刑法》第21條的規定,緊急避險是指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發生的危險,不得已而采取的損害另一較小合法權益的行為。可見,客觀存在“正在發生的危險”是適用緊急避險的前提要件。對于危險的來源,我國刑法學界通說認為主要包括四種:(1)自然的力量;(2)動物的侵襲;(3)非法侵害行為;(4)人的生理、病理過程。[1]上述危險源如果是由于他人或外界條件所導致的,則毫無疑問行為人具備了緊急避險適用的前提要件。但是如果上述危險源是由行為人自己所引發或招致時,即理論上所稱的自招危險情形,能否也可以適用緊急避險呢?該問題即涉及到緊急避險中危險源的限制問題。由于該問題直接關系到緊急避險的適用與否,即直接關系到行為人的行為合法與否,因此,對該問題的研究具有較強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相關刑法理論學說及其分析
關于緊急避險的危險源這一問題,其核心問題就是自招危險能否成為緊急避險的危險源?對此,我國現行《刑法》第21條第1款關于緊急避險的規定并沒有對危險的來源進行任何限制性規定。因此,刑法理論上對此問題認識不一,司法實踐中對此問題也存在認定的分歧。
對于自招危險的緊急避險適用問題,我國刑法理論上也有幾種代表性主張:
有的學者認為,在自招危險的場合,如果行為人是無意間的行為或過火行為導致危險的發生,一般應當允許實施緊急避險。但是,如果行為人是出于某種非法目的,故意地實施某種行為而引起危險發生,并以此為借口實行“避險”行為以實現其非法目的的,不能成立:緊急避險。[2]
也有的學者傾向于“相當說”,主張根據具體情況判斷是否允許緊急避險:意圖利用緊急事態招致危險的,理當不允許緊急避險;對由于其他原因而自招的危險(包括故意與過失),通過對法益的比較、自己招致的情節、危險的程度等進行綜合評價,需要進行緊急避險的,應允許緊急避險。[3]
還有的主張肯定說,其理由是:導致危險發生的原因對緊急避險的成立并不起決定作用,只要某種危險對合法權益構成現實而又緊迫的威脅,在不得已的條件下,即可實行緊急避險。無論是行為人自已的過失行為還是故意行為引起的危險,只要其無忍受這種危險的義務,均可成為緊急避險的危險來源。如某人想自殺,引火自焚,著火之后痛苦難忍,基于求生之本能,沖出火海,結果撞傷他人。在此例中,大火燒身之禍固然是行為人自己有意引起的,但其生命安全還應該受法律保護,不讓其實行緊急避難,聽任大火將其燒死,既不人道也為法理所不容。允許行為人劉白招的危險實行緊急避險,并不意味著其可以不承擔任何刑事責任。相反,對緊急避險前的行為,通常要負刑事責任、,如前述案件,雖然對行為人沖出火海撞傷他人的緊急避險行為不以故意傷害罪追究刑事責任,但對其點火自殺的行為本身,通常要根據具體案情定罪量刑,如果點火自焚的行為危害了公共安全引起或足以引起火災后果的發生,就應當按放火罪定罪量刑,如果點火自焚行為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僅僅是避險行為造成了他人重傷的后果,在其主觀上有過失的情況下,應按過失重傷罪定罪量刑。[4]
對于行為人出于犯罪目的,意圖利用緊急事態實施犯罪而自招危險的,理當不允許緊急避險,這是上述學者的共同認識之處。因為在此情形中,“避險行為”只是行為人實現犯罪的丁具,行為人主觀上也毫無避險意思可言。例如,甲見自己的仇人乙即將路過自己門前,于是故意放火燒屋,等到乙剛好經過門前時,甲用力沖出門外,從而將乙撞成重傷。對于這種自招危險,顯然不能以緊急避險論處,而應直接按相應故意犯罪承擔刑事責任。
第—種觀點實際上是根據行為人自招危險的主觀心態不同來決定是否適用緊急避險,即故意招致的危險不適用緊急避險,但無意間的行為或過失行為導致危險的發生,一般應當允許實施緊急避險。但該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因為根據該說,當行為人的故意行為引起了重大法益危險,但其實施避險只是造成輕微法益的損害時,也不能成立緊急避險。例如,行為人在旅館里企圖用煤氣自殺,但中途又后悔了。此時,是讓行為人呆在房間等死呢?還是允許其把比較貴重的門窗打壞呢?根據該觀點,行為人不能緊急避險,如果打壞門窗,則還應承擔毀壞財物的刑事責任。顯然該種結論不合理。
第二種觀點實際上是“相當性說”。該說雖然具有根據具體案情靈活處理的優點,但也有不足之處:“相當性”的具體內容如何來界定,即“相當性”這一概念過于抽象,并沒有提出具體的解決方針。尤其在目前我們整個司法環境還不夠理想的現狀下,該說容易增加司法的隨意性,從而造成司法適用的不統一。
第三種觀點實際上主張緊急避險的危險源無限制,即不管是故意招致還是過失引發的危險,都可以成為緊急避險的危險源。但是該學者的論證也是有待商榷的,即主張將招致危險的行為和避險行為分開評價,認為允外行為人對自招的危險實行緊急避險,并不意味著其可以不承擔任何刑事責任。相反,對緊急避險前的行為,通常要負刑事責任。換句話說,在白招危險情形中,自招行為是違法的,要承擔刑事責任,但避險行為是合法的。然而,自招危險中的避險行為是以自招行為為前提的,所以把二者分開進行評價是十分困難的。如果承認避險行為是緊急避險的話,就會出現結果有價值的情況,那么,也就會出現造成此種結果的自招行為也變成結果有價值的情況。例如,在該學者所舉的前述案例中,既然行為人沖出火海,撞傷他人的行為是合法的緊急避險行為,那么該行為造成的致人重傷的結果也是合法的,因為給無辜第三人造成一定損害本來就是緊急避險的要件。如果對行為人以過失重傷罪定罪量刑,豈不是把法律所允許的損害結果又作為犯罪結果加以評價,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因此,該說也不可取。
二、問題解決的構想
對于自招危險能否成為緊急避險的危險源這一問題,筆者認為,不能單純地根據故意與過失類型加以分別適用,應結合行為人的主觀方面以及其自招行為與法益侵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等問題來具體分析。具體而言,可以分為兩種情形討論:
(一)行為人基于故意或者過失自招危險時,如果其主觀上已經預見到危險的發生或有預見的可能性,客觀上該法益侵害的結果也可歸責于行為人時,則應否定緊急避險的成立,行為人應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事實上,對此種自招危險情形,我國司法實踐也是否定其可成為緊急避險的危險源。1999年12月12日上午7時許,西安市碑林區苗現房駕駛232路中巴車在運營時,位于其右側稍前、同向行駛的余某駕駛的527路中巴車因前方突然出現障礙而向左打方向。苗現房便也向左打方向,越過道路中心黃線駛入逆行車道,因車速過高,剎車不及,與對面正常行駛的一輛出租車相撞,致司機李某當場死亡。后經交警部門認定,苗現房當時車速約為67.6公里(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條例>對該類車輛50公里的限速),并違規越過黃線,在事故中負主要責任,駕駛527路車的余某因未注意觀察路況負次要責任,死者李某無責任。公訴機關以苗現房涉嫌交通肇事罪對其依法提起公訴;辯護人認為:苗為避免二客運中巴車相撞、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才不得已向左打方向,后雖與出租車相撞,造成了一定的損害后果。卻保護了兩車乘客的人身安全,因此苗現房的行為應為緊急避險,不構成犯罪。碑林區法院經審理認為,緊急避險具有排除社會危害性的性質。苗現房當時車速為67.6公里,已超過最高限速,且苗在超速行駛的情況下與余某的車輛并行,其行為不僅使自己的車輛處于危險之中,也給正常行駛的車輛帶來危險。因此苗現房的違規行為使其本身具有社會危害性,在此情況下發生事故,緊急避險所應具備的前提條件不存在,仍構成交通肇事罪。因此,該院以交通肇事罪判處苗現房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在日本也存在類似判決。在日本有這樣一個案件:被告人自己駕著車不減速飛快地行駛,這時候從對向駛來的貨車的右側跑出一少年,為了躲避他,行為人慌忙向右打方向盤,結果把正在步行的少年的祖母掛倒致其死亡。法院基于以下理由作了否定緊急避險適用的判決:“刑法37條規定的緊急避難,這種行為之所以不被追究刑事責任的,這是立足于公平正義的觀念,為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得已侵害了他人正當的利益。對于其危難是行為者因其有責任的行為自己招致時,如果按照社會的通常觀念不能承認其為不得已而進行的避難行為,這種情況不適用于緊急避難。”[5]
筆者較為贊同上述法院的判決。也就是說,此種自招危險不能構成緊急避險的危險源,應否定緊急避險的成立,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此種情形中應將從招致危險的原因行為到最終的法益侵害結果發生這一系列經過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因為后面的“避險行為”確實是以自招為前提的,把兩者割裂開來分析是不合理的。這正如原因自由行為理論一樣,如果只看醉酒人在醉酒后實施的行為,很難得出醉酒人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結論。
第二,行為人主觀上也預見到了或者應當預見到自己所實施的客觀構成要件行為會發生的危害結果,而且最終發生的法益侵害結果也可歸責于行為人。例如,前述案件中,雖然苗現房的行為確系為避免發生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危險,并客觀上也確實是犧牲了較小的利益保護了更大的利益。但從因果關系看,苗現房所避免的危險恰恰是其先前行為引起的,即其無論是選擇與中巴車相撞還是選擇與出租車相撞,該危害結果都是其交通違章行為所創設的危險的實現,可以歸責于行為人。同時,行為人在實施交通違章這一招致危險的行為時,其主觀上對于交通事故的發生也有預見的可能性。因此,根據《刑法》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對本案應以交通肇事罪論處。
第三,讓行為人承擔刑事責任也不會出現否定其“避險行為”價值的不利后果。也許有些學者擔心讓行為人對此“避險行為”引起的法益侵害結果承擔刑事責任,會導致行為人放棄救援較高合法權益的不利后果。筆者認為,這一擔心是多余的。雖然行為人要承擔刑事責任,但行為人積極采取將危害結果減小的措施,從而避免fd2942ddd31b07a0d801185e3b9f31e42f9f4991461521548e7a81f199f62638了較大危害結果的發生,這會直接影響到行為人刑事責任的減輕,并不是對其作出法律上的不利評價。因為危害結果的大小是影響刑事責任程度的重要因素。
(二)行為人基于故意或者過失自招危險時;如果出現了其主觀上事先沒有預見到的、并且沒有預見可能性的新的危險,則應肯定緊急避險的成立
在此種自招危險中,由于對于新出現的危險行為人主觀上事先沒有預見或沒有預見的可能性,因此,不能將自招行為與避險行為造成的法益侵害結果之間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例如,在日本也有類似案例,該案事實是:被告人在駕車右拐彎的時候,差點與一輛同時從左方向開來的客貨兩用車相撞。在繼續開車中,該客貨兩用車在被告人的車前停了下來,下來了幾個象暴力團的小伙子。由于這些小伙子對被告人車體又揣又砸,被告人感覺到自己和乘客的人身安全有危險,于是,其在沒有看清前方的情況下就向右拐彎逃走,結果撞到了相向而來的被害人駕駛的摩托車,結果導致被害人死亡。大阪高級法院1995年12月22日的判決中,檢察官主張:“由于被告人沒有合理開車差一點與客貨兩用車上是其開端,故使車體受到暴行是自招危難。”法官認為,被告人在向右轉彎逃走之際的行為屬于過失行為,因為其在右轉彎之際完全有可能看清前方,因而否定緊急避險,而肯定業務過失致死罪的成立。但是,筆者認為,這并不能以自招危險為由否認行為人行使緊急避險的權利,即該種自招危險可以成為緊急避險的危險源。該種自招危險中,雖然危險狀態的出現與行為人先前的自招行為有一定關系,但該種危險的出現卻是行為人實施自招危險行為時沒有預見到的或不應當預見到的。因此,該自招危險既不能成為行為人所保護價值減少的理由,也不能導致行為人忍受危險程度義務的提高。如前述案例中,雖然行為人對于交通肇事可能存在過失,但對于自己人身法益會遭受對方侵犯的危險卻不可能預見。因此,此種自招危險,可以成為緊急避險的危險源,即可以適用緊急避險。
結語
綜上所述,對于緊急避險的危險源這一問題,雖然我國相關的刑事立法沒有作出明確規定,但危險的來源并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也就是說,在以下兩種情形中,行為人自己招致的危險不能成為緊急避險的危險源:(1)有犯罪目的的自招危險。所謂有犯罪目的的自招危險,是指行為人以實現某種犯罪目的為意圖,而故意引起某種危險,然后假借緊急避險之名而對他人合法權益實施侵害,從而實現其犯罪目的。(2)行為人實施自招危險時,其主觀上預見到危險的發生或有預見的可能性,客觀上該法益侵害的結果也可歸責于行為人。對于這兩種自招危險情形,都應排除緊急避險的適用,直接按照相關犯罪定罪量刑。
注釋:
[1]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頁。
[2]馬克昌主編《犯罪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86頁。
[3]張明楷著:《刑法學》(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頁。
[4]劉明祥著:《緊急避險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杜1998年版,第30-32頁。
[5]轉引自[日]大垛仁著,馮軍譯:《犯罪論的基本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