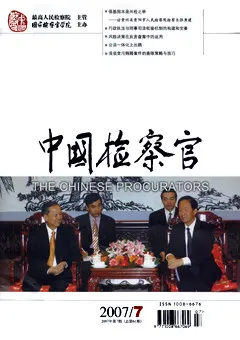離職后取走工廠貨款行為的定性
一、基本案情
2004年4月,徐某在東莞市斗寅塑膠廠擔任出納。同年9月,徐某應斗寅塑膠廠客戶三皇玩具廠的要求,向三皇玩具廠提供了一個以斗寅塑膠廠廠長金某名義開設的銀行賬戶,接收三皇玩具廠付給斗寅塑膠廠的貨款。2004年12月,徐某辭職離開斗寅塑膠廠,離職前未將其保管的金某存折交還廠方(內有存款余額100元),企圖日后支取三皇玩具廠匯入的貨款。2005年1月至6月,三皇玩具廠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仍然按照原有付款方式將貨款匯入金某的存折。徐某憑借金某的存折和密碼先后共取走存折內的76100元,并揮霍一空。2005年6月,斗寅塑膠廠發現事情真相,向公安機關報案。2006年5月24日,公安機關在吉林省延吉市將徐某抓獲。
二、分歧意見
對徐某行為的定性,本案存在以下三種典型的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應當以盜竊罪追究徐某的刑事責任。理由是徐某雖然占有該存折,但存折及存折內貨款的所有權始終歸斗寅塑膠廠。徐某離職后,斗寅塑膠廠對其的職務授權自行終止,其未經斗寅塑膠廠同意,在斗寅塑膠廠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支取存折內76100元貨款據為己有,屬于秘密竊取他人財物的行為,構成盜竊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徐某的行為構成侵占罪。理由是徐某雖然離職,但負有代為保管該存折、隨時將存折返還斗寅塑膠廠的義務。徐某未履行該義務,反而取走存折中的巨額貨款,其行為符合刑法第270條第1款“將代為保管的他人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的侵占罪特征,應當以侵占罪追究徐某的刑事責任。
第三種意見認為,徐某的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徐某基于擔任斗寅塑膠廠出納員的職務便利,持有和保管該貨款存折,徐某離職時帶走該存折,實際上就是利用職務之便,侵占了存折。該職務侵占行為具有一定的延續性,直到徐某支取了存折內的貨款據為己有,該行為才最終侵害了斗寅塑膠廠的財產權益,實現既遂。在徐某的整個行為過程中,不論是占有存折、還是取款時使用的密碼,都是利用擔任出納員這一職務帶來的便利,因此應以職務侵占罪追究其責任。
三、評析意見
筆者贊同第三種意見,認為應當以職務侵占罪追究徐某的刑事責任。為了論述方便,筆者擬通過對盜竊罪、侵占罪觀點的否定分析,層層推進,進而得出該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的結論。具體分析如下:
(一)徐某的行為不成立盜竊罪
根據刑法的規定以及相關的刑法理論,盜竊罪的本質是指盜竊他人占有的財物,而對自己占有的財物不可能成立盜竊罪。本案中,徐某離職前身為斗寅塑膠廠的出納員,享有合法占有、保管該貨款存折的權利。由于徐某知曉存折密碼,而銀行取款只需存折、密碼的規定,使徐某對存折內的貨款在法律上具有了支配力。也就是說,該存折和存折中的貨款,所有人雖然始終是斗寅塑膠廠,但徐某卻是合法占有人。徐某離職時故意不交出該存折,本質上就是將自己合法占有的財物非法據為己有,這種行為顯然無法成立盜竊罪。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徐某離職前存折內僅有余額100元。因此,不少持盜竊罪觀點的同志認為,在徐某離職前,其合法占有的僅為存折及存折內的100元,徐某雖然無法對該100元成立盜竊罪,但徐某離職后,三皇玩具廠匯入的76000元貨款,就不是徐某合法占有的財物,對于這76000元徐某可以成立盜竊罪。筆者認為,該觀點將存折和貨款完全割裂,背離了有價支付憑證的本質特征。所謂有價支付憑證,它的本質特征是具有財產利益,而且其權利的行使不以所有為要件,而以占有為要件。活期存折就是這樣一種有價支付憑證,只要占有人占有存折并知曉密碼,除非所有人將存折掛失使其作廢,否則占有人都可以支取存折內的財產,這種財產不僅包括存折內現有的利益,還包括將來得到的利益。在本案中,徐某離職前占有存折及知曉密碼,即對存折內的100元及將來可能得到的貨款都形成了法律上的占有,這種占有是整體性的,不能因為貨款到賬時間的先后變成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占有。徐某離職時將這種占有轉化為自己所有,是不構成盜竊罪的。
(二)徐某的行為也不能定性為侵占罪
從表面看來,徐某離職后仍應保管存折,徐某違背該義務,將存折內貨款據為己有,似乎符合侵占罪的特征。但是,筆者認為,以侵占罪追究徐某的刑事責任,將面臨兩個無法逾越的問題:第一,如何理解徐某離職時不交還存折的主觀心態?第二,如何界定職務便利在本案中的作用?
本案中,徐某離職前即產生了不交還存折、以便將來支取存折內貨款的故意。仔細分析不難發現,徐某的這種行為與直接取走工廠巨額貨款、攜款潛逃,并沒有實質的區別。斗寅塑膠廠基于對徐某的信任,將存折交給徐某保管,徐某離職時故意留存該存折,實際上就直接侵害了工廠與徐某之間的雇傭委托關系,而這種雇傭委托關系恰恰是職務侵占罪保護的對象。假設另外一種情況,如果徐某離職時只是忘記交還存折,離職后發現存折才產生將存折內貨款據為己有的意圖,那么其行為的性質就發生了改變,此時徐某代為保管該存折,乃是出于基本的道德義務而非雇傭關系,如果徐某未履行該義務,那么其行為侵害的就只是一種普通的保管關系,這種關系才是侵占罪保護的對象。本案中,徐某的行為侵害的顯然不是這種保管關系,也就無法成立侵占罪。
此外,在徐某的行為中,職務便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職務侵占罪與侵占罪是有著本質區別的,除了犯罪主體、犯罪對象不同之外,其中一個重要區別就在于是否利用了職務之便。在一般的侵占罪中,行為人根本不存在任何職務上的便利,也根本無須利用職務便利。本案中,徐某得以在離職時不交出存折,并非出于普通的保管關系,而是基于擔任出納員、保管存折的職務之便。徐某離職后憑密碼支取了存折內的巨款,其能夠獲知存折密碼,也完全是基于其擔任出納員、直接開設賬戶并設立存折密碼的職權。綜上而言,不論是占有存折還是最終憑密碼取款,在整個行為過程中,徐某都利用了職務便利。這使得本案顯然不同于一般的侵占罪。
有一部分持侵占罪觀點的人也提出這樣一種見解,認為徐某離職時存折內只有100元余額,徐某利用職務之便只侵占了100元貨款,由于100元錢的數額較小,該部分無法構成犯罪;但是,對于剩余的76000元貨款,徐某承擔的是一種保管義務,其違背了該義務,將76000元貨款據為己有,應當構成侵占罪。這種觀點同樣割裂了存折與貨款的關系,背離了有價支付憑證的法律特性,也進一步將一個整體行為人為地割裂為兩個行為。較為相似的一個案例是:甲得知乙的家人會給乙匯一筆錢,盜走了乙的存折,后憑借存折和偶然獲知的密碼,取走了存折內的200元余額及乙的家人后來匯入的2000元。這里,甲的行為顯然已經構成盜竊罪,而且盜竊數額應當以2200元計算,而不能認為甲僅盜竊了200元,后來的2000元是成立侵占罪的。
(三)徐某的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已經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占有活期存折者即具有支配存折內款項(包括將來入賬的款項)的能力,這使得徐某這個始終保管存折的人無法成立盜竊罪,也不能使徐某的行為因為款項到賬時間的先后被強行分割為職務侵占行為與盜竊行為或侵占行為。第二,徐某離職前即產生了故意截留該存折的故意,基于這種犯罪故意實施的犯罪行為,直接危害了工廠、員工之間的雇傭信用關系;第三,徐某的整個行為過程中,職務便利具有決定性作用。基于以上理由,筆者已經敢于給出最終的結論,但是這里,筆者仍然愿意從正面進一步分析徐某的行為。
我們仍然以上述甲盜竊乙的存折,后支取該存折內2200元的案例為例。假設甲盜得存折后,心生恐懼,打消了取錢的念頭,這時,甲實際上僅盜得了一本存折,其行為該如何評價呢?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0日頒布的《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實際上已經給出了答案,其第5條第(2)項規定:“記名的有價支付憑證、有價證券、有價票證,如果票面價值已定并能即時兌現的,如活期存折、已到期的定期存折和已填上金額的支票,以及不需證明手續即可提取貨款的提貨單等,按票面數額和案發時應得的利息計算。如果票面價值未定,但已經兌現的,按實際兌現的財物價值計算;尚未兌現的,可作為定罪量刑的情節。”也就是說,甲盜取存折時,存折內的200元是能即時兌現的,雖然甲未去支取這200元錢,但仍應以200元計算甲的盜竊數額,只是由于數額不大,危害性小,不入罪而已。至于乙的家人是否匯款是不確定的,而且甲也沒有將匯款實際支取,因此該筆匯款的數額可以作為甲定罪量刑的情節,實踐中一般也不對甲進行定罪。但是如果甲支取了200元和后來的2000元,則應按實際兌現的財物2200元計算其盜竊數額,這時數額達到法定標準,必須追究盜竊罪的刑事責任。
基于以上原理,在本案中,徐某基于保管貨款存折的職務便利,離職時帶走了該存折,實際上對存折及存折內的100元錢實施了“職務侵占”,對于這一點理解起來并不困難。若徐某的行為到此為止,那么該行為本身危害不大,不可能追究刑事責任。但是,若徐某支取了存折內的100元余額和76000元貨款,實際上就已經兌現了該活期存折的利益,并將該利益據為己有,就必須“按照實際兌現的財物價值”計算其職務侵占的數額。也就是說,徐某的行為從職務侵占存折開始,直到取走76100元貨款,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行為。其中,后續的取款行為進一步改變了計算職務侵占財物數額的方式,從而將所有的76100元計入其犯罪數額,使得行為危害性加大,必須入罪。
許多同志指出,徐某取款時已經不再是斗寅塑膠廠員工,因此徐某不符合職務侵占罪主體要件,不能構成職務侵占罪。這一觀點看似非常有道理,但通過前文的分析,可以知道該觀點是無法成立的:徐某離職時侵占了公司貨款存折,存折的特殊性使得徐某的職務侵占行為已經成立。徐某離職后的取款行為必須結合該侵占存折的行為,才具備評價的基礎,人為地割裂前后兩個行為顯然沒有任何意義。徐某最后支取了76100元,改變了徐某犯罪數額的計算方式,使徐某的職務侵占行為形成較大的社會危害性,從而構成犯罪。與本案相似卻性質不同的一個案例是:甲是某工廠倉庫管理員,離職時故意保留了一把倉庫鑰匙沒有交還廠方,離職后用鑰匙打開倉庫,運走工廠貨物倒賣謀利。在這個案例中,甲留存鑰匙,可以視為“利用職務之便,侵占了一把倉庫鑰匙”,但是由于取得鑰匙不等于取得了對倉庫貨物的支配權,鑰匙與財物之間還需要管理倉庫的職權作為媒介,甲失去了這一媒介,其行為就不能認定為職務侵占罪,而只能構成盜竊罪。但本案中,徐某職務侵占了存折之后,只需要存折和事先知道的密碼,就能實現對貨款的非法占有,所以徐某職務侵占存折的行為,對本案的最終定性具有風向標的作用,無論身份或取款形式如何改變,徐某的行為只能認定為職務侵占罪。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應當全面考慮徐某行為的整體性及存折這一特殊有價支付憑證的法律屬性,在徐某的整個行為過程中,其職務便利都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且其行為也損害了工廠與員工的雇傭委托關系,應當以職務侵占罪追究徐某的刑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