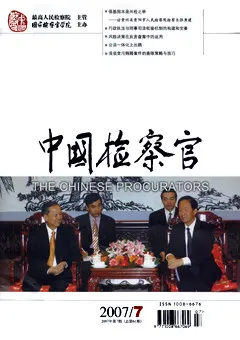盜走自己抵賬車輛的行為如何定性
一、基本案情
邵某因借李某18萬元逾期未能歸還,故將其作價18萬元的車輛連同相關車輛票證抵賬給李某,但未過戶。后邵某與另一債權人金某商議盜出該車,以抵金某之債,遂由邵某提供車鑰匙并指認李某停放車輛地點,金某伙同他人采取鋼鋸鋸鎖等手段將車盜走。后邵某告知李某,車已開走,并承諾繼續償還18萬元的借款。
二、分歧意見
對本案中邵某竊取自己抵賬的車輛應如何定性,存在以下二種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邵某既已將車輛抵賬給李某,雖未過戶,但李某已擁有了該車的占有、使用權,能夠成為盜竊罪中的盜竊對象,在李某占有車輛期間,任何人將車輛盜竊,都會給李某造成損失,邵某的行為符合盜竊罪的犯罪構成要件,邵某事后告知屬犯罪既遂后的行為,不影響其盜竊罪的構成,只能做為量刑因素考慮,其行為構成盜竊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抵賬車輛不能成為其本人的盜竊犯罪對象,邵某的行為沒有給李某造成財產損失,邵某的行為不符合盜竊罪的主觀構成要件,其行為應屬民事行為,不構成犯罪。
三、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理由是:
首先,本案中邵某抵賬給李某的車輛不能成為其本人的盜竊犯罪對象。根據法律規定,車輛的買賣、轉讓必須到車輛管理機構辦理過戶登記,車輛所有權才發生移轉。本案中,邵某雖然將車輛抵賬給李某,但還未過戶,因此,從法律上而言,邵某仍具有對該車的所有權。邵某將車抵賬給李某,在辦理所有權轉移手續前,只是轉移該車的占有權,邵某并未喪失對該車的所有權,而在民法上物權的效力要優于債權。換言之,如在辦理車輛過戶手續前,邵某清償18萬元債款,根據“物權破除債權理論”,李某仍有義務將車歸還邵某。
其次,邵某的行為沒有給李某造成刑法意義上的損失,不具有社會危害性。在判斷一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時,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該行為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本案中,雖然邵某將抵賬給李某的車輛竊取,又抵賬給金某,但邵某事后告訴李某詳情,并承諾還債。因此,李某與邵某的債權債務關系依然存在,其仍具有民法意義上的追償權,李某債權未受刑法意義上的損失。盡管邵某的行為在客觀表現上具有盜竊罪的某些特征,但最關鍵的一點是:盜竊罪并非行為犯,而是情節犯,只有盜竊達到一定的數額才構成犯罪。而在本案中,邵某的行為實際上并沒有給李某造成刑法意義上的物質損失。
再次,邵某沒有盜竊犯罪的主觀故意,不符合盜竊罪的主觀構成要件。第一種意見認為邵某為將車輛再抵賬給金某,而與金某共同將車盜出,其主觀上具有竊取他人占有財產的故意,并認為邵某事后告知的行為不影響本案定性。對此,筆者不敢茍同。盜竊罪的主觀特征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而判斷行為人是否是有這一目的,則必須遵循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加以分析。本案中邵某在盜走自己的車輛后即明確告訴李某,承諾繼續償還債務,說明邵某并沒有盜竊的主觀故意,他并沒有利用竊取手段來滅失與李某債務的動機,也沒有利用這種手段來牟利的意圖,其動機只是想優先償還金某債務。李某受到損害的只是優先受償的民事權益,這與盜竊罪主觀方面的構成要件是明顯不相符合的。
筆者認為:邵某與金某的行為是使金某取代李某獲得代物清償權的惡意串通的民事行為。本案屬典型的機動車代償合同糾紛,所謂機動車代償合同又稱機動車代物清償合同,是債務人以機動車輛抵償所欠債權人的債務的合同,即民間俗稱的“頂車”合同。機動車代償合同屬于代物清償合同的一種,其目的是通過機動車代償,從而完成債務的清償。本案中,車輛雖已交付,但未登記,所有權未轉移,李某只是實際上占有了該車。因此,邵某私自開走該車并承諾繼續償還債務的行為可視為撤銷了對李某代物清償的還債方式,代之以其他可能的還債方式。李某將車抵賬給金某,則是重新選擇代物清償對象的民事行為,當然這是以損害李某可能實現的債權為前提的,因此,李某可以通過提起民事訴訟的方式追究邵某的民事責任,但不能采取刑事訴訟的途徑來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