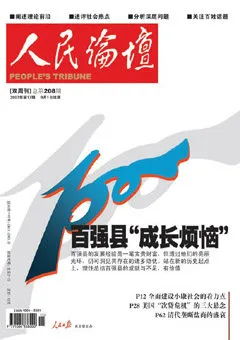“刑罰崇拜”思維值得警惕
近日,有兩則領導干部揮霍國家資財的報道十分引人注目:一是安徽省檢察院副檢察長徐文艾率團公款出國旅游,結果因為邀請函系偽造而被芬蘭遣返,最終受到嚴肅查處;二是今年以來,監察部牽頭督促各地區、各部門嚴格執行中央關于厲行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的有關規定,嚴肅查處違反財經紀律、揮霍浪費國家資財的案件,上半年共有4866名黨政干部因此類問題受到黨紀政紀處分。
公款揮霍作為一種久已存在的腐敗現象,當然不是新聞,不過這兩則報道之所以引起輿論強烈反響,卻緣于如何遏制公款揮霍的見解差異:就安徽省副檢察長被查的消息,某報紙發表《公費旅游能否以貪污罪論處》的社論,隨之該報又發表對著名刑法專家陳興良以及一位知名律師的訪談,兩位專家一致認為公款旅游不適合以貪污罪論處,結果這一消息很快招來幾乎眾口一詞的批評甚至圍攻。
反駁者均認為公款揮霍之所以屢禁不止,就因為對這一腐敗現象僅認定為違紀,只給予黨紀政紀處分,而不是將其列入刑法罪名或者視同貪污等罪名,課之以嚴厲刑罰,因而沒有對揮霍公款的腐敗分子形成嚴厲的打擊和強大的威懾。甚至有論者因情緒驅使,將兩位專家定性為同腐敗官員、行賄商人一起構成外電所謂“貪腐鐵三角”的“無良學者”。
其實,媒體輿論一致炮轟兩位專家的意見,乃在于雙方所占據的立場角度迥異:陳興良等純粹從刑法學專業角度解釋為何公款旅游等揮霍公款行為還不能以貪污罪論處,媒體評論則是站在社會學現象角度要求通過“入罪上刑”來遏制這一日趨蔓延的腐敗頑疾;前者依據的是對犯罪構成的主客體、主客觀方面等四大精確要件,后者依據的是腐敗現象之間的粗略類比和定性。正因為雙方的立論依據甚至議論焦點都不在一個層面上,所以媒體對兩位專家的炮轟顯然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最終都將對公款揮霍這一腐敗現象的深惡痛絕,一股腦兒遷延到學者的學術結論上,“無良學者”等人身攻擊型語言的出現就不足為怪了。
從刑法學角度看,一項新罪名的立法確認需要對新型違法現象進行深入論證,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從提出、論證到立法等環節都需要以慎之又慎的態度科學研討,這一點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從法治的角度看,“慎刑罰”不僅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觀點,也是現代法治精神的應有之義。在各項論證并不充分的情況下草率開展新罪名立法,或者在民眾情緒驅使下任意地將違法行為向刑法條款掛靠,都是對“法律應有明確性、穩定性”等法治精神的背離,也有違“司法獨立”這一法治的基本原則。
這種民憤驅動下對揮霍公款“入罪上刑”的喧囂聲浪,實質上仍不過是“嚴刑峻法”、“亂世用重典”等古代法家思想的翻版,而決不是現代法治思想指引下的嚴謹推斷,最終必將落入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而這種“罪刑依賴”甚或“刑罰崇拜”觀念,反映出的并非法治意識的提升,恰恰仍是法治精神的貧瘠和匱乏。
更何況,“入罪上刑”是否就能遏制公款揮霍現象呢?正如貪污受賄等刑法業已明晰的罪名無法有效阻遏貪污受賄的蔓延一樣,公款旅游、吃喝等揮霍行為,也很難因為“入罪上刑”而得到根本遏制。
其實,對于包括公款旅游等在內的揮霍公款腐敗,從源頭上說,需要規范的公共財政預決算制度加以防范把關;從過程中說,需要新聞媒體監督,乃至包括投票、罷免等在內的公民權利直接監督;法紀懲處,雖然有力,畢竟是事后的追懲,這種監督的有限性、滯后性是顯而易見、眾所周知的。源頭上沒有強有力的預防、阻擋,中上游沒有有力的攔截、分流,那么,面對公款揮霍這股已然洶涌澎湃的惡浪,黨紀政紀也好,刑罰罪名也好,任是再堅固的堤壩,又豈能抵擋得住?(作者系首都經貿大學公共管理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