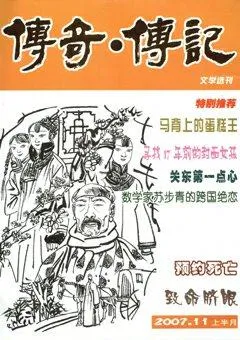致命臍眼
一
血雨腥風的夜。稀稀落落幾點星,慘淡地懸掛夜空;一彎新月,幽幽地隱沒云層。敵人來了,從七曜山上來,一路嘻嘻哈哈著,叫罵著,撲下山來,人人手提長刀,腰裹紅巾,赤裸著脊背殺來。
山下,便是那名叫林莊的莊園。眼望星星點點豆油燈鬼火似飄搖的莊園,一個尖尖的嗓門呷呷大笑:“林海生啊林海生,三年前你奪我田莊,搶我妻女,今天我定教你林莊灰飛煙滅!”
呷呷尖笑的那人是賊匪的頭目,名叫婁阿鼠,他們是七曜山上的一伙賊匪。
三年前,婁阿鼠還不叫婁阿鼠,他叫魏求,是與林莊隔河相望的魏堡堡主的三公子。魏堡占據著竹溪河畔上千畝的良田,年進千擔課租的沃土早讓林海生暗暗覬覦。可林魏兩家是世交,多少年來,一直沒有斷絕姻親往來。有一天,林海生竟然財迷心竅,買通官府,捏造了一個把柄,說魏堡堡主魏明天勾結七曜山上賊匪,密謀造反,一紙訴狀將魏堡給告上了衙門。
于是,官兵來了。官兵封凍了魏家所有的田莊,抓走了魏明天與兩個兒子,只有三公子魏求僥幸逃脫。逃走時,魏求遙望魏堡,灑了一地眼淚。看著林莊莊主林海生從官府手中接過田契,魏求便明白了事情的起因。魏求發了毒誓,三年后不將林莊夷為血地,他魏求枉來人間。魏求一把刀,一根竹篾火把,深夜上了七曜山。七曜山,十二關口,飛鳥難越,多少年來一直是山匪們的聚居地。站立十二關口,魏求凄凄惶惶地大笑了三聲,從此隱名埋姓,將自己改名叫婁阿鼠,拉起七八十名弟兄,日夜操練,只等下山血洗林莊的那一天。
三年后,婁阿鼠帶著七八十名弟兄來了。七八十名弟兄,一路鼓噪吶喊,聲勢震天,頃刻間,林莊的各廂房、廚房、茅房均燃起了熊熊大火。一把把刀,直將林莊的莊門剁得鏗鏗鏘鏘響。
林莊的養心殿前,一個聲音在仰天長嘆:“早知今天,何必當初啊!”嘆氣的這人正是林莊的莊主林海生。莊外,賊們的喊聲是越發的大了,林海生的臉色也便越發的蒼白。在賊們的噪聲中,他顫顫地叫了一聲:“蘭心!”聲過,身前立即站過一個發髻整齊、面容姣好、手拉一個約兩三歲孩童的女子。林海生看了她一眼,又嘆了一聲氣說:“蘭心,我深知魏求那人心狠手辣,絕對不會放過我的,只怪我一時財迷心竅,惹下這奇天大禍,連累你們母子倆了。這里有一地洞,僅留一人棲身,望你帶上臍眼,速速逃走吧。”
女子身形抖了抖,兩行清淚悄然滑落。
眼望這對母子,林海生淚流滿面地說:“蘭心,我只是不甘心,林家就這樣毀在我的手中了。如果你還是我林家的人,盼你好好將臍眼養大成人,重新奪回林莊,替爹爹報仇啊!”說罷,搶過一把刀,從那把紫檀木的太師椅上一躍而起。殿外,十幾名家丁隨這團身影一齊殺出。莊門在一聲“吱呀”聲中破響,兩塊板栗木的門板隨即轟然倒地。
好一場惡戰啊。火,熊熊地燃燒;椽檁瓦片,在火光中嗶嗶剝剝暴響。惡戰中,婁阿鼠一直在笑。看著那火光,那林莊越發多了的尸首,呷呷呷地大笑。
惡戰中,林海生死了。林莊的所有莊丁、丫寰們全都死了。僅逃走一個名叫蘭心的女人和一個名叫臍眼的三歲孩童。
三天后,巴陽,一個距七曜山十二關口三百余里的古鎮上,新添了一個女人。女人拖著一個孩童,面容憔悴,眉間隱含一絲幽怨。她就是蘭心。蘭心說:“臍眼,娘帶你來到這個窮山惡水的地方,娘是希望你躲過仇家的追殺,快快長大。娘只希望你長大后,殺上七曜山,血洗林家的冤仇。”
說這話時,蘭心幽幽地嘆了一聲氣。未嫁時,娘告訴她,在家從父,出家從夫,夫命就是天令。她想起了林海生的臨終遺言,惟有悲涼地搖頭。
二
白龍廟,一座距巴陽古鎮三十里的古廟,冷清,蕭殺,卻隱藏一位高僧。高僧須發皆白,叫弘法。這天,蘭心肩背臍眼,跪倒在弘法的腳前,無聲的淚水讓高僧銀眉微顫,佛心悸動。
“阿彌陀佛,敢問女施主跪倒佛前,所求何事?”弘法寒聲相問。
蘭心嗚嗚咽咽地哭了。哭聲中,她斷斷續續地講了那個七曜山賊匪血洗林莊的故事。蘭心悲悲戚戚地說,雖然林海生一時財迷心竅,可他魏求也不該恃強凌弱濫殺無辜呀!
弘法大師沉默了。沉默過后,弘法方說:“亂世多賊匪,老衲早聽說七曜山上有個婁阿鼠,自恃武功高強,肆殺成性,連官府也奈何他不得。要想除掉他,難啊!除非……”
蘭心凄涼地一笑說:“只要能讓我完成夫君的遺愿,縱死無憾。”
于是,弘法將目光轉向了蘭心背上的臍眼。瞅瞅那個正熟睡的孩子,弘法搖搖頭,輕念一聲阿彌陀佛,遞給蘭心一封發黃的密笈……
從此往后,巴陽古鎮一間破落的茅屋多了一個女人。女人手牽一個孩童,白天,給古鎮的張官爺、李老爺家漿洗一些衣物打打雜工,夜晚,當鎮上最后一盞燈火熄滅時,則拉過孩童開始熬煮一鍋藥湯。白炭文火,藥湯熬好之后,女人將濃濃的湯汁傾進一只瓦盆中。這個時候,她會用尖尖的五指插進藥湯,去測試湯液的溫涼。然后,女人撥下孩子的衣物,將孩子整個兒泡進瓦盆中。欲進不進的時候,女人的臉上往往會爬上一絲凄惶。短暫的三分鐘過后,女人的淚便流下來了,她用白皙的左手護住孩童的臍眼,右手則揚起木瓢,將溫熱的藥湯從孩子的頭頂淋下。于是,孩子渾身沾滿藥液,發出快活的喊叫聲。那封發黃的密笈,就擺放在女人的膝前。女人對一眼密笈,潑一瓢藥湯,再對一眼密笈,再潑一瓢藥湯,神情專注又虔誠。夜夜如此。夜夜,當那孩童風雨無阻地被那藥湯浸泡過后,女人會對他說:“臍眼啊,媽媽給你練的這種功夫,是一種江湖上不死的傳說,名叫金鐘罩,又叫護體童子功。它用三百六十味神秘中草藥熬成,藥味辛辣而又有巨毒,長期用它浸泡,會練成金剛不壞之身,刀槍難入。當你長大成人,你便可以獨上七曜山,拿了仇家首級,祭奠你爹的亡靈了。”
女人就是蘭心。蘭心沒敢告訴孩童她用手罩住他的臍眼不讓藥液浸入的原因。
三
一晃十多年過去。巍巍的七曜山頂,白雪漫裹著每一個山頭。十二關口,一幢幢石砌的古寨在白雪中幽幽地放出銀光。一座寨門緊閉的石寨里,婁阿鼠正跟幾名弟兄圍著一盆炭火,口中哈出一團團頃刻間便會凝成一團寒霜的熱氣。就在這一天,天,奇冷,那個早已因寒雪封山的山徑讓人踏出一串足跡。深深淺淺的赤腳窩子在雪中一點一點,給雪山留下星星點點的瑕疵。然后,是寨門被拍響的聲音。砰砰砰砰,激烈的聲音讓一伙伙賊匪似乎早已閑靜的心也隨那砰砰聲一起顫動。
伴隨著這種響聲,婁阿鼠一躍而起。他明白,有人踩盤子來了。立即,牛角的號響,嗚嗚咽咽地響徹在十二關口的每一個山頭。七八十名山賊,也隨之呼擁而出。他們倒要看看,是哪一個不要命的家伙吃了熊心豹膽敢獨上十二關來!
寨門開了,一團黑炭似的人影凸現眼前。那是一個啥樣的人啊?渾身赤裸著,僅穿了一條褲衩,古銅色的身子油光光、滑膩膩,在雪地里絲絲縷縷地散發出茶色的光。看他那一瓣瓣如巖棱般隆起的肌肉及寒天里紋絲不掛卻不抖不顫仿佛天人一般的模樣,不禁讓婁阿鼠等人倒抽一口涼氣。婁阿鼠驚呆了:江湖中不死的傳說出現了!能夠在冰天雪地中赤裸著茶銅色的身子的功夫不是金鐘罩又會是什么?
婁阿鼠寒聲問道:“敢問壯士姓甚名誰?”
赤身人冷冷答道:“臍眼。十三年前被你血洗林莊僥幸逃過一劫的林莊林海生的犬子臍眼。”
婁阿鼠笑了。婁阿鼠甚至問了聲:“臍眼,十多年來,你跟你娘究竟躲藏在哪里?”
赤身人呵呵呵地怪笑。怪笑聲中,赤身人說:“我知道這些年來你一直在找我們娘兒倆,你想斬草除根。哼哼,只可惜,皇天庇佑,讓你落了空。”說罷,亮出了刀。
婁阿鼠也亮出了刀。他的嘴唇嚅了嚅,想說什么,終沒有說出。七八十個弟兄都亮出了刀。婁阿鼠說,只準捉活的,誰若違令,剁下十指。于是,七八十個弟兄一齊呼嘯著,包抄過去。
人未近身,七八十把刀,頃刻間卷成一把把鈍刃。七八十個山賊全都呆了,果然神奇的金鐘罩啊,刀槍不可近身的金鐘罩!赤身人揮刀狂舞,立即,山賊們尸橫遍野。婁阿鼠嘴唇嚅了嚅,想說點什么,又沒有說出。這時,他的眼中已凝聚一團殺氣,冷森森說了聲:“殺無赦!”便帶頭揮刀殺入。剩下的弟兄們也發出一聲喊,加入戰團。
呵呵呵呵,赤身人依然在笑。一把閃著寒光的刀,在他的手中,如風般滑過。七曜山的黃昏,雪,依然在飄。漫天的雪花中,七八十具尸體,已如冰般漸漸僵硬。
雪野,僅僅還有兩個活物在蠕動。一個是赤身人,另一個便是婁阿鼠。婁阿鼠算是親歷了那個江湖上不死的神話的神奇與險惡。任他每一刀每一式,在赤身人那里,都不起絲毫作用。婁阿鼠慘慘地笑了。多次,將到嘴邊的話語,卻終于沒有說出。
也許,今天是在劫難逃了。忽地,婁阿鼠怪笑了一聲:“臍眼,假如我是你的娘舅,你還會步步逼命嗎?”赤身人呆了呆。就在這一呆中,婁阿鼠已覷出了赤身人身上的異點了。那個異點,正是赤身人肚腹上的臍眼。赤身人周身如炭,惟有臍眼處有巴掌大一塊灰點。婁阿鼠慘慘地笑了。婁阿鼠說:“臍眼,你娘還是那樣善良,沒有改變你的臍眼模樣。其實,你的臍眼處,涌動著的有我們魏家的脈血啊!”
赤身人又愣了愣。忽地,赤身人大笑了,他感到面前的仇敵已經不是一個敵人,而是一個瘋子。“殺掉婁阿鼠,完成你爹爹的遺愿呀!”上山前,母親的話語又回響在他的耳旁。赤身人手腕一抖,刀,帶著風聲,疾風般地向前飛去。他的臉上浮現出一種復仇的快感,他仿佛看到了仇人臨死前的慘狀。
一聲慘叫,就發自于婁阿鼠的口中。就在這時,一支袖箭也從婁阿鼠的手中發出,不偏不倚,正正飛向赤身人灰色的臍眼。赤身人眼一瞪,一股鮮血,立即噴涌而出。
那枝袖箭,正從赤身人灰色的臍眼插入,沒入箭羽!
赤身人怪怪地笑了,說:“娘騙了我,江湖中并沒有不死的傳說。你也不是我舅,我舅不會害我。”
婁阿鼠也怪怪地笑了,看著赤身人緩緩倒地的身影,慘笑著說:“你娘沒有騙你,江湖中的確有不死的傳說,只不過你娘太善良,給你留下致命的弱點。我也是你真正的娘舅,正因為跟你娘一樣,承襲了魏家的弱點,所以招來今天的殺身之禍。”
赤身人呆呆地望著,迷惘。
婁阿鼠慘慘地說:“知道嗎,正因為你娘是我的親妹妹,我才沒有斬草除根啊!”說罷,一團帶血的影子轟然倒地。
四
三天后,七曜山頂來了一個女人。女人從赤身人裸露的臍眼中拔出了那支袖箭。女人目光癡迷,神情呆滯,喃喃地說道:“臍眼,是娘害了你,是娘的溺愛害死了你啊!”
那本發黃的密笈,就翻動在女人的膝前。密笈中記載,練取金鐘罩不死的神功時,有毒的藥劑會從臍眼透進,那將是對一個練習者最大的考驗。每一次的透進,練習者都將如萬箭鉆心。這也是每次練習時女人護住孩童臍眼的原因。她是怕孩子忍受不住那萬箭鉆心的疼痛啊!沒想到正是這個沒有被藥功浸過的臍眼成了她兒子致命的弱點。
女人又爬向婁阿鼠的腳前,搖晃著那具大睜著眼的尸身,慘然說道:“哥,別怨蘭心,要怨也只能怨我們的娘,娘說,夫命就是天令啊!”
風,夾著女人的哭聲,嗚嗚咽咽,悲涼,幽怨,只給七曜山頂更添一層凄涼……
〔責任編輯 方 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