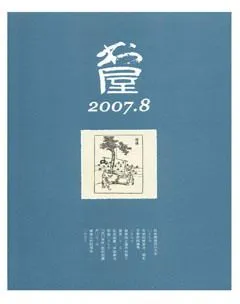作為晚明記憶的訪墓
秦燕春在《我亦東林復社孫:冒鶴亭與冒辟疆一段隔世情緣》(見《書屋》2007年第4期)一文中,曾經談及1911年冒鶴亭為其祖冒辟疆選擇的慶生雁集之地夕照寺,與萬柳堂、袁崇煥墓一起被當作晚清宣南士人聚會當中一條固定旅游線路。其文有未竟之處,在此稍作彌補。
1943年以通敵賣國的罪名被民國政府槍斃的才子黃秋岳,在他的名著《花隨人圣盦摭憶》中曾經訕笑“吾國史例,承平則修墓祭掃,亂離則發冢取物”。而被黃列為南方修墓之舉代表人物的還是這個晚明情重的冒鶴亭:“(冒)前既覓得河東君墳,其后居京,又數祭杜茶邨墓,嘗于酒座,歷數其訪求名墓事,同人戲稱以上墓專家。”以為“發墓摸金,固當科罪,修墳題詠,亦止增掌故”。然而此際文人積習如zgB7LdH1eH3Bntu+be+EMjf0Z9ea+0nXCEp8/BAW9rw=此,又何止冒氏一端。
例如同在京師宣南,陶然亭畔有所謂“香冢”者,似乎也是清末民初居于帝鄉的文人慣愛憑吊的一處歷史風景。在南社詩人周斌所著《題香冢二絕》中,該冢也被一廂情愿地當成了明季遺物。詩前題記,作者先如斯斷言:“陶然亭左,有香冢焉。一抔黃土,石志無名,相傳是勒方琦葬某妓遺物處,惟石古字勁,短銘悲壯,絕不類瘞玉之辭,疑中系殉明難者,恐觸當時忌諱。借香冢以寓言耳。”接下來的題詩則繼續將此種毫無道理的歷史想象廣而大之:“杜鵑含淚亦嫣然,艷跡消沉三百年。今日泉臺應一笑,短歌重續月重圓。”這首讓作者認為古勁悲壯的墓志全文如下:“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煙痕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為蝴蝶。”老實說,其中很難看出任何與晚明有著特殊記憶符碼的痕跡關聯。
顯然,晚明記憶在清末民初如此發達與風光,至于“無報不談明末事”,宣南“香冢”得以橫空出世,也正是此種且“奇”且“艷”且“節烈”的想象空間能夠滿足當時文人重構晚明的多層需要。
此類故事當然不止發生在京師,那個時間段內幾乎全國上下都在跟風趨潮,諸如梅花嶺吊史閣部、西湖邊吊張蒼水,于此際文人筆下不勝枚舉。特別是最能在聲色趣味上大做文章的秦淮八艷的墓址遺蹤,更是倍受關注,如蔣同超《遇西神山錦樹林吊玉京道人墓》之類。此中心理,恰如丁傳靖書寫陳圓圓、吳三桂的傳奇《滄桑艷》第二十回“訪墓”中書生阮仲容夫子自道:“當日讀梅村圓圓曲時,緬想香蹤不僅神往,不意今日親自滇中,得見艷跡,好生僥幸也。”按照況周頤《陳圓圓事輯》(發表于1915年11月《小說月報》第6卷第11號)中提供的線索,這位慕色尋芳的阮公子原型應該是阮元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