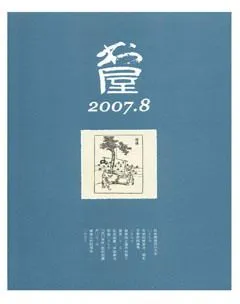也寫白話的劉師培
該怎么“蓋棺論定”劉師培?這個年僅三十六歲就夭亡的文化天才不僅留下七十四種著述,更因其腦筋急轉彎般的政治變節而為當時與后世詬病:從弱冠之年算起,由熱心科舉的試子到提倡“光復”的志士,再到出賣革命友朋的清廷密探,乃至躋身擁戴袁世凱恢復帝制的籌安會六君子,“晚歲”職掌北大教習則領銜《國故》月刊對抗新文化運動……真真“翻臉如翻書”。無怪乎馮自由會擬之為“揚雄華歆之流亞”,難怪通達愛才如蔡元培雖深許其“勤敏可驚”也要抱憾其沒有委身學術。儀征才子似乎有著對“背叛”行為本身的癡迷?比背叛行為本身更加不能被原諒的,甚至還有對背叛自我不肯自我承載,“外恨黨人,內懼艷妻”的說辭或許可以算作時人愛才的有意護短,但1907年劉師培自家“輸誠”的《致端方書》中解說自己誤入“排滿”歧途,也是一股腦把“誘脅”行為歸因在蔡元培、黃興等人賬下。好一個被教唆犯罪的清純少年。
劉師培出身文化世家,其家三世傳經,申叔堪稱集其大成,所謂“家傳樸學,奕世載德,蘊蓄既富,思力又敏”。清學殿軍章太炎(枚叔)不是容易服人的人,但對于劉氏經學一直稱賞有加,“海內二叔”交誼洵為佳話。學問好外還有文章好,能把勸進陳情的《君政復古論》都寫得鏗鏘有力、字潤腔圓的劉師培,在《清儒得失論》、《南北文學不同論》、《中古文學史》中溢彩流光的不僅是眼光識力,更有詞采華茂。
劉師培也正經寫過白話文章,主要集中在他投身反清革命的時期。作為《中國白話報》的寫手,發表在該刊的系列文章以1904年第八期《論激烈的好處》最為學者關注。但第六期、第七期經學天才兩篇“白話明儒”也相當有趣,這就是署名“光漢”的《黃黎州先生的學說》與《王船山先生的學說》。兩文前者其實是針對黃宗羲名著《明夷待訪錄》的白話演說,將《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方鎮》、《閹宦》諸篇用白話“一層一層的演說出來”,“這書上說的話,句句是說自由平等的,但是這書說自由平等,都是實在有道理的,共現在新黨說兩句自由平等空話,卻是大大不同”,不能說作者此語單純是在“厚古薄今”,學術自有淵源的劉師培不滿“空話”的論斷自有其意旨。有意思的是,年華未及雙十的小經師即使寫作這樣通俗的白話文字,也要動輒上法三代、于秦漢以前尋求救國攘夷之道,亦算特點非常鮮明。
劉師培白話版本的梨洲學說雖然主要立意也不脫以民權對抗君權的大要,但“此前的人,不曉得這部書的好處”,只有到了現在,在西學的引導之下黃宗羲才被重新發現:“外國的人都是個個謀民權的,所行的法子,也是共黃先生說的差不多。”小經師的與時俱進乃至急功近利,其實已顯端倪。在他這一期間另一白話文章《中國排外大英雄鄭成功傳》(《白話報》1904年第二十期)中,劉賦予鄭成功種種近代化特征,例如開設學校、臺灣自治、聯絡友邦……似乎鄭一身作為就可以解決晚清遭遇的所有問題,實行泰西各國的政治,進而建設海外新中國。
記憶中的劉師培倡論晚明學術,多是那個下筆行云、以為“顧、黃、王、顏,修身踐行,詞無迂遠,民生利病,了若指掌,求道德之統紀,識治亂之條貫”、“以濟世之弘才,抱艱貞之大節,而說經稽古亦深,兼具儒材節義”,但這個熱衷于白話啟蒙的不乏好奇矜異的“光漢子”也不應該被忘記——算起來那時節他十足是個孩子(劉生于1884年),甚至他開始“政治失足”的時候也只有二十三歲,他沒有長到“不惑之年”就死了。
“千枝燈帽白如霜,郎照歸朝妾倚廊。叫起守關銀甲隊,令人夫婿有輝光”,劉成禺詩中所言,是劉師培擔任袁政府參議時日暮歸家的體面場面,這位“憑欄逆之”的女子就是被稱為“通文翰而淫悍”卻又艷名甚噪的劉太太何震。如果劉成禺的詩行不是謔虐而是紀實的話,看來這位號“志劍”、曾在日本主持過《天義報》的新女性的確不是一盞省油的燈,有些虛榮?做她的丈夫如果不講究一點利勢嗜欲而僅僅“皓首窮經”,也許真的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