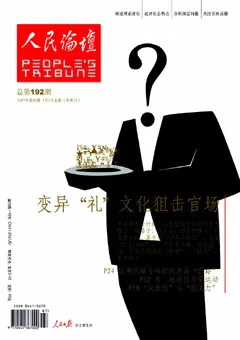避免公共財政“神化”運動
編者按
本刊2006年11月A期刊發的《公共財政和諧之路》一文引起了一些讀者的關注,下文作者通過對前文的簡短點評,回答了該如何正確認識公共財政“公共性”這一問題,值得細讀。

矯正公共財政“公共性”的認識偏差,是為了向公眾特別是財政官員闡述公共的價值,使其認識到為何根據個體的理性判斷,“公共”是值得信賴和堅持的理念,且可以轉化為切實可行的財政經驗。
《人民論壇》2006年11月A期刊發許力攀的《公共財政的和諧之路》一文,通過對公共財政特質及其潛在規范力的闡釋,描繪了從公共財政的基本建制通向和諧社會的藍圖,足見作者希望解除決策者思想困惑的良苦用心。也正是懷著“人類的認知將在漸進中成熟”的信心,我們有必要準確地界定什么是公共財政的“公共性”。
從“財政”或“國家財政”到“公共財政”,這是我國財政改革在觀念上取得的重大進步。既然是公共財政,“公共”便是它區別于其它類型財政的標志,于是,準確把握公共財政的公共性便成為理解公共財政本質的關鍵。
另一方面,在當代的財政實踐中,盡管政府在上個世紀末就承認了建構公共財政體制的必要性,目前看來,不只是財政官員,就連財政學者也依然戀戀不舍“國家分配”時代的榮光。
由此不難看出,觀念的變革往往比制度的突破更難實現,更何況政治對新事物的反應又經常會出現時滯性,事實上,當代政治家、政府官員接受的思想、理論很可能是幾十年以前的,而這顯然不是簡單地批評“觀念落伍、思維僵化”便可以解決的。話雖如此,我們還應承認,認知的成熟是在一系列持久的觀念沖突中逐漸實現的。
公共財政的“公共性”并非財政共性,而是公共財政的特性,正是“公共”使公共財政名副其實
目前我國財政學界的普遍觀點是,“公共性”不是公共財政的本質特征,而是財政的共性,它自財政產生之日起就具有了。也就是說,無論是處于自給自足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奴隸制財政、封建制財政,還是處于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乃至計劃經濟條件下的資本主義財政、社會主義財政,都具有公共性。
問題是,如此寬泛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公共性”,不僅僅流于形式上的粗糙和內容上的武斷,還直接促使人們以不求甚解的心態對待我們目前正在建設中的公共財政體制,既然“公共”沒什么特別的,那么“公共財政”也不過如此。但在筆者看來,公共財政的“公共”具有政治上的規范意義,其實任何關于稅收和支出的分析都是建立在政治理念的信仰、政治的預先設定的基礎上的,而在西方政治哲學中,政府是選民的代理人而非統治者,從這個角度看,政府的代理人角色恰好充分地詮釋了公共財政的“公共性”或“公共精神”。也正是因為“公共”所具有的政治規范力,使其得以成就一個從“個體利益”到“公共利益”的通道。為何這樣說?
首先,公共不是化私為公,而在于公私分明。因此,“公共”可以與“私有”并存,它非但不反對“私有”,相反是因為對“私有”的重視如私有產權保護,使得“公共”不再流于形式上的理想主義而具有實質性的內涵。西方的財政研究關注的是財政體制是否有助于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是否有助于約束政府官員的行為,是否有助于維護納稅人的利益和滿足納稅人的集體訴求,等等。這表明,公共財政中的“公共”既承認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又強調保持私有經濟獨立性的重要性。
其次,“公共”明確了財政行為主體的變遷。從“國家財政”到“公共財政”,并不只是表述上的變化,更是財政主體的變遷,表明財政不再只是政府的事務,還是眾人的事務。現代財政理論主張建立收入與支出的聯系并不只是出于財政運行合理性的考量或是對財政量入為出原則的重復,更在于它強調了政府與納稅人“自愿交換”的政治經濟倫理,即認為稅收是個人為了交換政府提供的服務而自愿支付的費用,并且與個人對這些服務的評價相對應。這意味著,政府的收支不再是政府之事務,而是與納稅人的利益息息相關的財政行為,財政的公共性也因此大大提高。若是從這個角度理解“公共”,那么,深受“國家分配論”觀念影響的財政官員的確有必要重新定位了:“財大氣粗”并沒錯,至少是人之常情;問題是,如果財非己有,而是替人保管,不應自我決定財之去留,那就沒有必要自以為是大款了。
即便可以將公共財政的“公共性”理解為“市場性”,但“市場性”也不是“為市場經濟服務”,而是指財政的市場化運作
雖然國內財政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公共性是財政的共性,因此沒有必要強調,不過與此同時,也有不少學者注意到了公共之于公共財政的特殊性。在他們看來,“公共性”其實就是“市場性”,市場性意味著政府的財政運作不應妨礙市場的正常運轉,而且要保證市場經濟的正常存在和運轉,政府的活動領域只能限于市場失靈的領域,等等。簡而言之,公共財政是“為市場提供公共服務”,或“作為市場經濟的輔助,應對市場失靈”。
將公共財政的“公共性”直接等同于“市場性”,大抵是經濟學者對市場根深蒂固的偏好所致,本來這也無可厚非。如果說“公共性”與“市場性”之間可以劃一等號,而且很可能是一個真命題,那么研究者至少要向讀者清楚地闡明市場性為何是公共財政的本質屬性。
首先,“市場性”指的是公共財政的市場化運作。例如,讓民主選票和公共選擇發揮著類似自由競爭市場的功能,用于調節資源分配、獲知消費者(納稅人)的需求偏好并據以確定公共產品與服務的相對價格。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市場性的確與公共性相輔相成,可以說,正是“市場性”成就了公共財政的“公共性”,也即公共財政通過具有類似市場精神或市場作用的民主政治程序或集體決策規則來實現“公益”和“公利”。因此,公共財政的“市場性”要義在于規范政治市場的操作原則,至于“不應妨礙市場”、“保證市場的正常存在和運轉”,則是這一“市場化操作”對“私人市場”的客觀影響。必須看到,盡管市場經濟的發育與市場力量的壯大有利于財政的制度變遷,但“市場性”與市場經濟并非直接對應關系,公共財政與市場經濟只是一種相互適應、動態演進的關系,而不是充分或必要、包含或被包含的關系。
其次,市場性構筑了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自愿交換關系。這種交換不僅涉及政府與納稅人,還發生在不同個體之間,他們有著不同的知識和不同的需求,但都有權表達各自的利益主張。無疑,這種交換將是復雜的,不過也正是復雜性使得公共財政具備了自由競爭市場中的一些特征。在這個市場中,選擇和交換是其支柱,說白了,公共選擇和平等交換是自愿交換的前提,它們也因此規范了公共財政各行為主體的行為準則。因為是交換的,所以稅收不能是政府強加給納稅人的,而必須征得納稅人的同意。這也是為何西方公共財政分析的邏輯起點不是征稅,也不是支出的分配,而是政府與納稅人、納稅人內部的平等交易,而稅收和支出都只代表交易的某一方面。
解讀公共財政的公共性、矯正我國財政學界在公共財政“公共性”上的認識偏差,并不是為了追求公共財政的純粹性,而是為了探求公共財政的基本建制、原則規范。無疑,這是提高財政認知能力的基礎。當然,客觀理性地分析公共財政的“公共性”,也是為了避免出現公共財政的“神化”運動,提醒決策者做到心中有數的同時,還應保持清醒的認識,務實行動,不做一廂情愿的美好設計。(作者單位: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