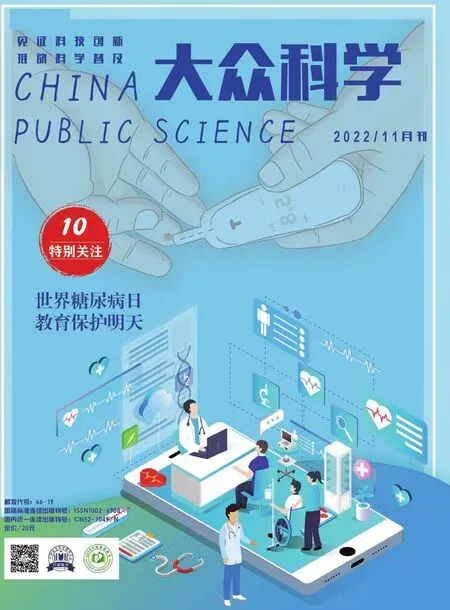滴,請通行!ETC快速通行的原理是什么?


ETC(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不停車收費系統(tǒng),作為一種先進的路橋收費方式,以其高效的通行效率受到司機的喜愛。當其他車輛在高速收費站排起長龍時,裝有ETC的車甚至都不用停車,迅速在隊伍一側通過。當我們談及ETC時,很多人都覺得是安裝在車上的類似讀卡器的東西,其實不然,它只是ETC整個系統(tǒng)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那么,ETC是由哪些部分組成的,它能夠實現(xiàn)快速通行的奧秘又在哪里呢?
ETC系統(tǒng)是依托無線通信進行信息交換的無人自動化通行系統(tǒng)。一般來說,它主要由車輛自動識別系統(tǒng)、信息庫管理系統(tǒng)以及相應的輔助設備組成。我們通常見到的放置在車輛前擋風玻璃上類似讀卡器的東西是車輛自動識別系統(tǒng)中的車載單元(OBU即On Board Unit的縮寫),又稱為電子標簽或應答器。OBU中儲存著車輛的身份信息,是每輛車可以通過收費站的“通行證”。
除此之外,車輛自動識別系統(tǒng)中還包含設置在收費站處的路邊單元(RSU即Road Side Unit的縮寫)及埋藏在車道下的環(huán)路感應器等硬件設備。信息庫管理系統(tǒng)則是ETC系統(tǒng)的“大腦”。信息庫中儲存著大量注冊車輛及用戶的信息,這些信息與車載單元中車輛及用戶信息相匹配,從而能夠準確判斷來車的身份。輔助設備包括車道欄桿、費額顯示器、闖卡報警器及通行信號燈等。
當車輛到達收費站處,車道下的環(huán)路感應器感應到車輛通過,將信號傳遞給路邊單元。路邊單元向車輛發(fā)出詢問信號,車載單元感應到路邊單元的微波信號,做出應答,將車輛信息上報。信息庫收到車輛信息,根據(jù)車牌號、車型等信息與庫中注冊車輛信息相匹配,完成車輛的識別。
若識別通過,欄桿抬起允許車輛通行,路邊單元完成與車載單元中IC卡的通信,進而完成扣費的操作。若識別不通過,闖卡報警器發(fā)出警報,直至車輛退出環(huán)路感應器。這整個過程看似復雜,但其實系統(tǒng)反應時間很短,車輛不需要停車等待,極大提高了通行效率。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車載單元中是裝有放拆開關的,不能私自拆卸。一旦拆卸,固定在車載單元后的防拆開關啟動,此車載單元失效,再次通過收費站時系統(tǒng)會報警,不能正常通行。這時候,我們就需要到辦理ETC的銀行對車載單元進行重置,這樣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