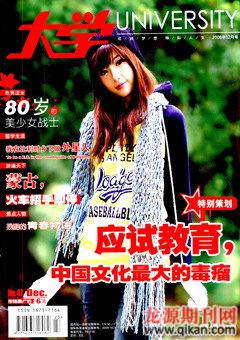殘酷的青春物語
王利彬
2008年的中國政法大學注定不平靜,“楊帆門”引發師生關系的大討論,“抄襲門”又引發學術腐敗的大爭鳴,但2008年10月28日中國政法大學昌平校區顯得格外不平靜。
是夜,夜涼如水,法大校園燈火輝煌,昌平校區端升樓201教室,學生有的在看書,有的在小聲聊天。講臺上教師程春明埋頭整理教案,從包里拿出手機看了看時間,離上課還有2分鐘。當他正準備對坐在下面的19名學生開口說“我們開始上課”的時候,教室后門突然被撞開,沖進來一個風風火火的學生。程老師還沒來得及看清那個學生的模樣,就措手不及地被那學生連砍兩刀,倒在了血泊由……
那名學生叫付成勵,22歲,中國政法大學2005級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國際政治專業學生。如果沒有開頭的那一幕,他本應該順利地度過大學校園中的最后一個年頭,畢業后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可如今的付成勵卻在冰冷的鐵窗內,等待著法律的裁決。作為政法院校的大學生,付成勵很清楚自己的行為將帶來的后果,事發后是他主動打電話報的警,被抓后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但毫無悔意。
事發后,很多人都在問到底是什么讓他毅然地走上了這條不歸路?
我們現在無法直接聽到付成勵的解釋。對社會過分關注此案造成的攪擾,中國政法大學師生們選擇了集體沉默,無人愿意再向外界就此事談及一二。付成勵身邊的同學對付成勵何以至此的原因避而不談,被害人生前好友對此則是諱莫如深。
在信息極其有限的情況下,想耍弄清楚付成勵的行為動機,我們或許可以借助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大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論,嘗試著找到事情的源頭。弗洛伊德認為,無意識動機是行動的原因,任何特殊事件隱蔽的動機,都可以像夢的分析那樣,通過自由聯想來揭露。無意識動機是構成無意識(潛意識)的那些個人的原始的盲目沖動、各種本能以及出生后和本能有關的欲望。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學》一書中。搜集了幾百個關于無意失言、無意錯誤和不由自主動作的實例,用以說明或多或少隱蔽的動機。同理,或許付成勵成長中的幾件小事可以折射出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來。
案發當天中午,付成勵的好友去了一趟他的宿舍,看到的付成勵,上身套著一件棉襖,下身穿著一條洗白的藍色牛仔褲,臉一直對著自己的筆記本電腦屏幕,也不理睬他。“也不知道付成勵在干什么,我叫他,他就只應了一聲”,好友略微感到付成勵有些不耐煩,抓了一把他桌上的花生米。沒待多久,就轉身走了。下午,與付成勵要好的一個女生與他有過簡單的通話,在16:53分左右,付成勵打電話給她,問有什么事情。那女生說,沒有什么事情啊?付成勵說,那你打電話給我干嗎?女生現在已記不得當初是不是自己打過電話給付成勵,含糊說可能是撥錯了號,付成勵還約那女生一起吃晚飯。
付成勵像很多在校大學生一樣經常上網關注各方面的信息,并在校園網內開通了名為“地主”的博客,里面有500名好友。博客的最后更新日期是今年的10月6日,這一天的博文轉載的是大導演張藝謀領銜策劃的情景劇《印象·麗江》的主題曲《回家》。如果我們純粹從欣賞音樂的角度看待這篇博文,只會簡單地認為《回家》只是一首曲調優美的歌曲。當我們揭開《回家》的面紗,探尋背后的故事時,我們就會發現這首曲子可能是弒師的前兆。
《回家》是作為《印象·麗江》中《天上人間》部分的背景音樂出現的,講述的是一對納西族情侶殉情的故事。小伙子和他心愛的女子騎著白馬,去那傳說中的玉龍第三國,尋找永生的愛情與幸福。玉龍第三國在納西語中譯為“舞魯游翠閣”,在納西族古老的傳說中,是東巴愛情守護神。相傳,當人們的感情和傳統社會道德相沖突。無法面對現實時,人們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換取的一個生存空間。一個理想的國度。
我們看到一段文字或是一幀照片,而或聽到一首歌,當這些東西多多少少反映了我們內心里某種無以言傳的東西時,我們就會產生一種共鳴,進而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因此,我們才會收藏或是保留這些東西。從付成勵轉載《印象·麗江》的主題曲《回家》中,可見他對于情感的純粹化和理想化態度。而這種水晶球般的情感在現實中最容易破碎。
另外一個生活中的實例更加印證了我們的判斷。在大一上學期的一個晚上。班里有同學突然患病,被送到區醫院,付成勵回來比較晚,聽說之后執意要趕去醫院,可宿舍樓下的大門已經鎖了,結果他從三樓跳窗出去趕到醫院。早上5點,同學醒來看見他趴在床邊很驚訝,知道詳情后感動得哭成淚人。
由此,我們似乎窺見了他最后的心跡,也似乎什么都沒有看到。以轉載的樂曲《回家》作為映射付成勵的心理活動,可能顯得有些“隔”,我們還需要更多的無意識動機。作為折射心理的話語,最直接的證據當然是能閱讀到人物自己寫作的一些文字。弒師案發生后。互聯網上廣泛流傳著付成勵寫的詩作《2006年祭,懷念我過去的一年>。我們古人認為:“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用我們現在的通俗說法就是“言為心聲”。通過解析付成勵寫下的這首詩,或許可以管中窺豹,略見其一二。
作者在詩作中對于“這一年”,像“花”“草”“吃飯”“睡覺”“上課”“腦袋”“成績”等等日常生活,所作的評價是“依舊”。詩中一連運用了九個“依舊”。足見寫詩的人對于現狀的“厭倦”與“不滿”,似乎“渴望突破”。詩作發生轉折的詞匯是“懂得”:“有些事終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貪財和好色只是人的本能/本無所謂男人和女人”,“偉大的男人通常要具備兩顆心,一顆心滴血,一顆心寬容”,“人本來就是孤單的個體”,“人是可以不必為任何事情做解釋的”,“人活著大多數時候都是被別人玩偶爾玩玩別人”,“世界和生活的舞臺是大家的/作綠葉的時候也要盡心盡力”,“卑鄙往往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常常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詩作前面兩部分基本上可以概括為“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的生活。有形的物質層面的日常生活,表面上平靜如水,一切“依舊”,但無形的精神生活卻暗藏潛流,波濤洶涌。
兩年前的付成勵19歲,入大學滿一年,正是世界觀、人生觀的形成時期。我們無從知道究竟經歷了什么,使付成勵“懂得”。但從“懂得”的“道理”中我們可以反推出青春的殘酷:“有些事終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不是在說明歷經千辛萬苦,渴望成功之時,換來的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的苦澀;“貪財和好色只是人的本能/本無所謂男人和女人”——如果是一個男人使其“懂得”,就沒有必要出現“本無所謂男人和女人”這一句了,可見該“道理”的所指指向的是“女人”。也正因為是一個意料之外的“女人”使其“懂得”如此“道理”,這一層的傷害可能來得更深沉更強烈。緊跟著的一個“懂得”更加肯定了我們的猜測——“偉大的男人通常要具備兩顆心/一顆心滴血,一顆心寬容”,一顆心傷痕累累被分裂為兩瓣,一瓣在“滴血”,一瓣在“寬容”,借以寬慰自己的是自詡為“偉大的男人”。在追求女人方面的挫敗,使其“懂得”“人本來就是孤單的個體”。回歸到個人本位的個人主義之后,并不是說徹底“與世隔絕”,眾人的詢問與質疑目光需要澄清,但付成勵認為“人是可以不必為任何事情做解釋的”,因為他“懂得”“人活著大多數時候都是被別人玩偶爾玩玩別人”。
將付成勵的兩篇博文并置在一起閱讀,似乎可以看到他成長過程中一些“一以貫之”的東西。正是這兩則青春物語,使我們看到付成勵成長中的一些模糊影子。成長的青春被人生的風霜刀劍弄得遍體鱗傷。更殘酷的是建立在其上的世界觀、人生觀,因為這會伴隨著人的一生。我們用付成勵詩作的結尾作為本文的結束:時光已逝/無以為紀,謹以此志/慎祭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