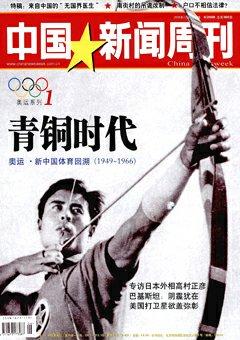戶口不相信法律?
韓 永 劉麗綺
擁有外地戶口的張勇夫婦知道,起訴不給兒子上戶口的派出所,“贏的幾率幾乎為零”。但“我就是想知道,法院以什么理由判我輸”

將派出所告上法庭,事先并不在張勇為解決剛出生兒子的落戶問題所設定的各種計劃里。
與很多夫妻雙方均沒有北京戶口的家庭一樣,這樣的計劃無非有二,一是讓新出生孩子的戶口隨父或者隨母,二是斥巨資在黑市為其買一個北京戶口。
但張勇認為,這兩者均非完美的解決方案:要么就承受骨肉長期分離的痛苦,要么就要有一筆足以摧毀他們幸福生活的巨額資金投入。
現在,張發現可能有第三種方案。這個方案源于一個法律的發現——根據這個法律,他認為兒子的戶口落在北京,只需要相關的部門“依法行事”即可——但問題是,“依法行事”恰恰成了問題。
落戶的掙扎
張勇來自遼寧鞍山,妻子王女士來自河北魏縣,兩人均非北京戶口,按照現行的慣常做法,他們的孩子碩碩出生后將沒法在北京落戶——要么隨父,要么隨母。
落在父母老家的一個現實問題是孩子在哪兒接受教育。在老家上學,“這不現實啊,”張勇說:“誰愿意把自己的孩子扔在一個沒人照顧的地方?”張勇2002年7月份來北京工作,2005年與王女士結婚并在昌平的佳運園小區買房后,更是將母親接來與自己同住,老家只剩一個形式上的概念。
而要在北京就讀,公家設立的借讀費和各校私自設立的贊助費必須要交。前者在政府的干預下有逐漸下降的趨勢,但從小學到高中一路走下來,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按北京市政府的相關規定,如果從小學一直借讀到高中畢業,這筆費用為17400元。
但這筆費用比起私下的贊助費,甚至可以忽略。張勇一位朋友的兒子在北京讀了6年小學,平均每年的贊助費高于1萬元。如此讀完高中,贊助費可高達10多萬元。
這還沒算上學前教育。張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家附近的一所幼兒園,一年的贊助費高達3萬多元。這樣算下來,一個沒有北京戶口的孩子,在北京從幼兒園到高中讀下來,光“額外”的教育費用就得一二十萬。
“如果能一直這樣買下來,倒也是好事,”關鍵是從頭到尾在北京借讀了十幾年后,到高考的前夕也不能“轉正”——在每一年北京市高考的報名條件中,最后一條總是:具有本市正式戶口。
在北京生活學習了10多年卻要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參加考試,與環境磨合的難處可想而知。更為關鍵的是,由于目前許多地方高考是各省自己命題,內容大不一樣,在北京所學未必能在其他地方派上用場——正是與囿于這種現實的壓力,很多家長選擇在孩子初三畢業后回老家讀高中,但這同樣導致親子兩相離。
要獲得北京高考的一張準考證,只好求助于戶口黑市——也曾經有人向張勇介紹過這里的行情——新生兒落戶的報價10多萬元,而為外地籍的孩子買一個北京戶口則要20多萬元——不能不驚嘆市場定價機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如果將一個非北京籍孩子從幼兒園到高中因戶口而支出的額外教育費用計算以后就會發現,這個價格比后者略高,而教育正是戶口在北京最大的價值籌碼。
張勇承認,他曾經在很長時間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去為孩子買戶口。
但他最終放棄了。在過去的一年,國內的一些省市啟動了戶籍改革,戶口不再成為外來人在當地接受教育的一種障礙,這些變化深深激勵著張勇。“誰知道十幾年以后的事呢?”
推動著張勇最終走出黑市困擾的,是一條有關法律的傳聞。一位朋友告訴他,好像有一部有關戶口的法律,根據該法律,只要在北京有常住地,任何一個外地人在北京新出生的嬰兒都可以在京落戶。
“這不可能,”這是張勇的第一感覺。但朋友建議他去找一個人問問,這個人與張勇住在同一小區,叫程海。
“維法”運動
程海,安徽籍律師,2007年因本人的戶口遷移問題曾將北京和合肥兩地的公安機關告上法庭,從而為媒體和公眾關注。
程海2003年10月份來北京發展,每年要去派出所辦一次暫住證,這種狀況到了2005年3月其在北京佳運園小區買房后也沒有任何改變,換領身份證、辦理出國護照,都要跑回千里之外的老家合肥;裝網通公司的固定電話,竟然需要有北京戶口的人提供擔保。他開始感覺這種“長期暫住”的制度有問題。
于是他開始翻閱有關法律,他當時的想法是:“如果沒有一部有關戶口的像樣的法律,就提出一個制定此類法律的公民建議;如果有關的戶口法律本身有問題,就提出一個修改法律的建議。”
結果查下來一看,“我們不僅有這樣的法律,而且內容還不錯,”這部法律就是1958年出臺、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下簡稱“《戶口登記條例》”)。“這是我國至今仍在生效的唯一的一部戶口法律。”他說。
該法第六條規定:“公民應當在經常居住的地方登記為常住人口,一個公民只能在一個地方登記為常住人口。”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公民因私事離開常住地外出、暫住的時間超過三個月的,應當向戶口登記機關申請延長時間或者辦理遷移手續。”
程海據此認為,在北京生活了3年多時間并已經在此買房的事實,足以說明北京是自己的常住地——常住地的含義在最高人民法院在1992年7月14日發布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被明確闡明為,“公民的經常居住地是指公民離開住所地至起訴時已連續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程海據此認為自己常住地所屬的昌平公安分局和其派出機構東小口派出所應該為自己登記戶口。
而根據該法第十六條第一款,他在北京的暫住時間已經超過3個月,上述登記機關應有為自己辦理戶口遷移手續的義務。
于是,2007年3月12日,他向昌平區公安分局和東小口派出所寄去書面申請,要求為他辦理常住戶口從合肥市遷入北京市的手續,次日,他又向現戶籍所在的合肥市廬陽公安分局及其派出機構三牌樓派出所寄出了戶口遷出申請。
3月26日,北京市昌平公安分局回函,拒絕他遷入,理由是他不符合北京市有關戶口遷入的政策;4月13日,合肥市也拒絕了他的戶口遷出申請,理由是根據公安部的規定,需遷入地先開出戶口準遷證。
遷戶申請遭到拒絕后,程海于4月18日和19日先后將合肥市廬陽區公安分局和北京市昌平區公安分局告上法庭,要求兩者為他辦理自由遷移手續。自此開始,一系列針對戶口的訴訟案件陸續展開。
結果并不盡如人意。在合肥,廬陽法院先是以其告錯對象為由駁回了第一次起訴,在程海將被告由廬陽公安分局改為三牌樓派出所后,又以被告“已盡職責”為由,判決駁回程海的訴訟請求;在北京,昌平法院以“昌平分局不具有為起訴人程海辦理戶口遷入的職責”為由,行政裁定不予受理,隨后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的上訴也以其所訴事項“不符合行政立案條件”做出維持原來裁定的終審裁定。
在2007年6月份被受理的程海訴北京市公安局的案件,因過程曲折而備受關注,最終也以“不屬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圍”的理由被駁回,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也以同樣的理由做出不予受理的終審裁定。
但這樣的結局并沒有打擊到程海,或者說,這本就在他的預料之內。
在他看來,這些看似鋪天蓋地的敗訴或者被駁回,援用的卻是同一個理由:按照有關戶口登記的文件,程海不符合戶口遷移的條件,而程海恰恰認為,正是這些被援用的下位的戶口登記文件,對上位的《戶口管理條例》構成了非法的侵犯,顛覆了該條例的自由遷徙精神。
他努力尋找更多的案源,以求對這些“犯上”的戶口文件構成圍剿之勢——程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些“犯上”的戶口文件主要侵犯了五種人群的權利,新出生孩子的落戶問題正是其中之一。所以當張勇找上門來時,程海形容其兒子碩碩是“上天送來的寶貝”。

被訴方“怯戰”?
程海告訴張勇,《戶口登記條例》第七條規定:“嬰兒出生后一個月以內,由戶主、親屬、撫養人或者鄰居向嬰兒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報出生登記。”
程海告訴張勇,按照此項規定,其已在北京買房2年的事實,足以讓他的孩子合法獲得北京市戶口。
于是,下面的程序變得淡如流水:在碩碩出生后一個月之內,張勇做了兩件事情:先是拿著《嬰兒出生常住戶口登記申報書》,去其常住地所屬的東小口派出所申請為孩子登記戶口,遭到預料中的拒絕后,又將該申報書通過特快專遞的形式寄給該派出所,同樣被對方以其不符合北京市有關落戶的條件而遭到拒絕。
在走完戶口登記申請的程序并收集到相關的證據后,得到張勇全權委托的程海于今年1月11日將東小口派出所告上了昌平區法院。
讓程海頗感欣慰的是,這次的起訴比他于去年4月份在該法院提起的訴訟的狀況“前進了一大步”:不僅得到受理,還在預定的2月18日的開庭日期前收到了傳票。“這表明法律已經開始起作用了。”他說。
一種樂觀的情緒開始蔓延,他甚至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這場官司會贏”——雖然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的專家幾乎沒有人相信這種論斷。
這樣的希望在2月15日的法院之行后化為泡影。當天,程海和張勇的妻子一道,按照昌平法院在年前發出的傳票的時間如約來到該院,卻拿回了一張駁回起訴申請的裁定書。
駁回起訴的理由似曾相識:“原告的訴訟請求不屬于行政審判權限范圍。”
起訴連吃“閉門羹”的滋味可想而知,但程海認為,剝開那些表面上的理由,這一系列行為的背后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相關部門“不敢”在法律的規則下在法庭上應戰。
專家認為,法院以不屬于自己受理范圍而駁回起訴其實容易理解,戶口這么一個全國人關注的問題,對法院實在是難以承受之重——有時還要受同級公安部門長官“間接領導”的準下級單位,怎么可能對連自己的準上級都無法下結論的問題貿然做出決定呢?
這種態度的一個合乎邏輯的解釋,可能是被起訴方對訴訟的結果不甚自信。在程海看來,《戶口登記條例》第七條的規定再明白不過,一旦在法庭上得以采用,派出所為新生兒辦理戶口登記的義務就在劫難逃——同樣是該條例,在第三條明確規定“鄉、鎮人民委員會和公安派出所為戶口登記機關”——程海依據此條認為,前幾次訴訟時法院在駁回裁定中所說的理由“被告沒有職責為原告辦理戶口登記”根本不成立。
“他們沒有職責,誰有?”程海說。
關鍵還是以哪個法律為據。如果按照相關文件,程海和張勇的兒子的確都不符合在北京落戶的條件,于是公安派出所也就“沒有職責”了,但為什么要依一些下位的法律文件來劃定他們的職責,卻放著現成的上位的法律不依,特別是在下位法屢屢“犯上”的情況之下?
現實是,管制顯然是一種更便于實施的行政模式。另外,還可能節約行政成本,在有些戶籍改革已經啟動或行將啟動的地區,就已經聽到了一些政府部門的抱怨,比如醫保的基數太大、治安壓力驟然增加等等。
事實上,有些人包括一些網友并不完全認同程海對《戶口登記條例》相關條款的理解,也就是說,即便是走上法庭,相關政府部門也大有為自己辯護的余地,但他們不去爭取這些對自己可能有利的局面而選擇閉門不出,讓人覺得氣短的同時,可能還隱藏著其他的考慮。
換句話說,相關政府部門即便通過各種可能的手段取得了訴訟的勝利,也很難享受到一種勝利者的感覺。因為在戶口的弊端大有可陳的今天,改革似乎成了民眾唯一能接受的話語。
政府部門內部似乎也存在分歧。據《中國日報》1月23日的報道,一份來自國家發改委的要求取消戶口制度的提案已經產生,提案表示,應當在今后的3到5年內,取消戶口制度。但主管戶籍的公安部到目前為止的口徑是,戶籍制度不會取消,但戶口遷移將繼續放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