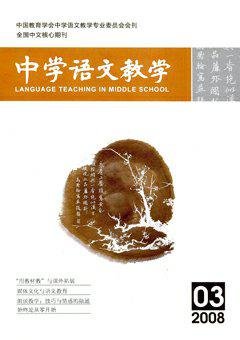兩手分書 一喉異曲
陸精康
互見法是司馬遷首創(chuàng)的紀傳體史書特有的一種敘述史事的方法。這種方法將傳主的生平事跡,事件的來龍去脈,分散記于數(shù)篇之中,參錯互見,最大限度地彌補了以記人為中心的紀傳體史書的不足。“史臣敘事,有缺于本傳而詳于他傳者。是曰互見。”①簡言之,本傳不載或略載之傳主事跡,略見或詳見于其他傳記,這就是互見法。其運用之妙,“有似兩手分書,一喉異曲,則又莫不同條共貫,科以心學性理,犁然有當”②。了解紀傳體史書人、事互見這一特點,對全面準確認識歷史人物是十分重要的。
本文以入選江蘇版選修教材《〈史記〉選讀》的《高祖本紀》《項羽本紀》及與之相關的其他人物傳記為例,說明司馬遷是如何運用“互見法”,完整、準確、生動地塑造劉邦、項羽形象的。
一、評、傳互補:塑造劉、項形象的基本手段
《高祖本紀》敘述了劉邦由起兵反秦,到楚漢相爭,到建號稱帝的全過程。傳主劉邦這一開國君主的行跡在本傳中得到充分反映。劉邦的一些優(yōu)秀素質(zhì),如順應時代,收攬人心,知人善任,恩威并用,團結(jié)內(nèi)部,分化敵人等,本傳作了具體描繪。史家向有避諱傳統(tǒng),漢高祖被西漢統(tǒng)治者頌為“大圣”,本朝人寫本朝史事,司馬遷對開國君主的個人缺陷,在本傳中是刻意作了回護的。
劉邦進入咸陽,受降子嬰,成為秦帝國的終結(jié)者,這是本傳給人們留下的深刻印象。然而,劉邦究竟在滅秦過程中發(fā)揮了多大作用,本傳的記載并不明朗。事實上,在相關評論中,司馬遷并未肯定劉邦在推翻秦朝歷史進程中的決定性作用。《太史公自序》談到《高祖本紀》的寫作目的:“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fā)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yè)帝,天下唯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司馬遷創(chuàng)作《高祖本紀》的宗旨是說明“漢行功德”始能統(tǒng)一天下。《高祖本紀》側(cè)重敘寫劉邦打敗項羽,除暴安天下,“改制易俗”的歷史作用。但是,滅秦之功,第一應歸于陳涉之發(fā)難,揭竿而起;第二應歸于項羽之繼業(yè),擊潰秦軍。強大的暴秦主力實由項羽“力戰(zhàn)”滅之。《史記》表稱“秦楚之際月表”,而不名以“秦漢之際月表”,是寓有深意的。陳涉首事,項氏繼業(yè),浴血苦戰(zhàn),推翻暴秦,才為劉邦統(tǒng)一天下掃清了道路。評、傳互補,表、傳互足,還歷史以真實,表現(xiàn)出司馬遷忠于歷史事實的卓越史識,而這一點,僅讀《高祖本紀》就很難體認。
《項羽本紀》歌頌了項羽在反秦斗爭中建立的偉大業(yè)績,也揭示了項羽失敗的原因。司馬遷重點寫巨鹿之戰(zhàn)、鴻門之宴、垓下之圍三大事件。巨鹿之戰(zhàn),項羽破釜沉舟,奠定了滅秦基礎。鴻門之宴挑開了楚漢相爭的序幕,也是項羽事業(yè)的轉(zhuǎn)折點。垓下之戰(zhàn),項羽走向窮途末路,悲歌別姬,東城決戰(zhàn),讓讀者目睹了舉世無雙的英雄項羽的風采。項羽最后自刎而亡,令讀者悲嘆惋惜。至此,一個頂天立地的蓋世英雄的形象躍然紙上。
《項羽本紀》是《史記》中寫得最成功最具文學色彩的史傳,其主旨是揭示項羽的蓋世英雄性格和悲劇結(jié)局,因此,項羽的許多個人缺點乃至暴虐罪行,在本傳里或是一筆帶過,或是略而不載。對此,太史公用一篇《項羽本紀贊》作了全面補充。一方面稱頌項羽是“近古以來未嘗有也”的英雄,另一方面也從大處著眼,對項羽的歷史罪行作了嚴肅批判:第一,分裂天下,引起爭斗;第二,背關懷楚,失去地利;第三,放逐義帝,引發(fā)叛亂;第四,自矜功伐,不行仁政;第五,專恃武力,喪失民心。司馬遷的這些直接評論,思想深刻,褒貶得體,引導讀者對項羽有一個全面準確的認識。
評、傳互補是“互見”的一種方法。在不失歷史之真的條件下,司馬遷有意識有目的地對劉、項形象作了回護,而在相關評、贊中客觀評論了劉、項的歷史功過,完善了人物形象。所以,僅僅據(jù)《高祖本紀》和《項羽本紀》分析劉、項形象,顯然是不夠的。評、傳互補,方能對劉、項形象有全面準確的認識。
二、兩傳相足:使劉、項形象完整的重要手法
秦王朝滅亡后,劉邦集團和項羽集團是反秦隊伍中的兩大軍事集團,兩個軍事集團進行了長達四年的楚漢戰(zhàn)爭。楚軍起初處于絕對優(yōu)勢,但由于項羽缺乏遠見,剛愎自用,殘忍暴虐,不擅用人,優(yōu)勢轉(zhuǎn)為劣勢,項羽兵敗自殺。劉邦一開始就否定割據(jù),順應潮流,善納諫言,知人善任,遂由劣勢轉(zhuǎn)為優(yōu)勢,最后打敗項羽,統(tǒng)一天下。劉、項勢力,此長彼消,劉、項二人,如影隨形,《高祖本紀》中有項羽,《項羽本紀》中有劉邦,這是讀兩篇傳記產(chǎn)生的強烈印象。
劉邦事跡與項羽事跡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在材料組織上,太史公往往運用詳此略彼手法記錄重大事件。顯然,在考慮兩篇本紀的布局時,司馬遷“對于材料如何安排更合理、更重要,是費了多番考慮的。盡管是一部規(guī)格龐大的書,也必然體現(xiàn)出篇與篇之間錯綜離合,彼此關聯(lián)的精神”{3}。
“鴻門宴”是劉、項成敗的轉(zhuǎn)折點,是劉、項本傳中不可缺少的重大事件。這一事件,如果在劉、項傳記中都詳細描述,會造成文章的累贅;但如果只在其中一篇中敘述,另一篇中忽略不提,則不能全面真實地反映歷史,而且也無法表現(xiàn)傳主的全貌。司馬遷的安排是,在《項羽本紀》中作詳盡描寫,而在《高祖本紀》中僅寥寥數(shù)語:“沛公從百余騎,驅(qū)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這樣,既避免了重復冗贅,又使史事敘述條理分明。劉邦、項羽對峙成皋,《高祖本紀》詳載劉邦歷數(shù)項羽十宗罪之詞:“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于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強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弒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上列言詞在《項羽本紀》中僅以“漢王數(shù)之”一語帶過。認真思考一下,不難發(fā)現(xiàn)司馬遷這樣安排材料的用意。“鴻門宴”重在突出項羽的“自矜功伐”“婦人之仁”,故雖記劉邦,須載《項羽本紀》。“十宗罪”重在表現(xiàn)劉邦的順天應時吊民伐罪,故雖寫項羽,須載《高祖本紀》。如果材料反過來擺放,就與創(chuàng)作兩傳旌表傳主的宗旨舛違了。這兩件事,司馬遷在本紀中的處理“錯綜離合,彼此關聯(lián)”,顯示了高超的藝術(shù)。這就是歷史學家評論的“互文相足”:“一事所系數(shù)人,一人有關數(shù)事,若為詳載,則繁復不堪,詳此略彼,則互文相足焉。”{4}
另一方面,太史公有意將不便記入本傳的傳主事跡納入了對手傳記。“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劉邦為了逃命,竟忍心將自己的親生骨肉推墜下車,為人殘忍如此,當然不便記入本傳。“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面臨父親被烹殺的危險,劉邦竟說出這樣的話語,為人無賴如此,當然也不便記入本傳。這兩件事,本傳只字不提,有意安排在《項羽本紀》之中。
而從《高祖本紀》又可觀照項羽。且看各方面人物對項羽的評說。“懷王與諸老將”的評論:“項羽為人僄悍滑賊,諸所過無不殘滅。”關中百姓的埋怨:“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高起、王陵的觀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zhàn)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對手劉邦的分析:“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高祖本紀》載錄的各種評判之詞勾勒了項羽的形象。雖有一范增,項羽不能用,劉邦的這一分析,尤其一語中的,指出了項羽覆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成皋之戰(zhàn)中,劉、項對峙廣武,劉邦一籌莫展,乃用反間計離間項羽、范增關系。范增走后,項羽立刻陷入被動,不斷鉆進劉邦的圈套,終至走上窮途末路。《高祖本紀》中有項羽,項羽的缺點、過失、罪愆恰恰是從《高祖本紀》中看出的。司馬遷這樣寫,是有意識地維護《項羽本紀》中項羽“悲劇英雄”的形象。
運用互見法組織材料,史傳內(nèi)容兩兩對照。從《高祖本紀》和《項羽本紀》中可以明顯看出史公采用的對比手法,這也是一種“互見”。鴻門宴上劉邦的狡詐和項羽的坦率;彭城戰(zhàn)敗后劉邦逃命的狼狽,垓下之圍中項羽別姬的灑脫;項羽殘民,劉邦撫民;項羽勇武,劉邦智計;項羽由強變?nèi)酰瑒钣扇踝儚姡詈笥饻鐫h興——皆對比見義,相反相成,令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三、他傳側(cè)記:使劉、項形象豐滿的特殊技巧
在從起兵反秦到漢楚相爭的歷史進程中,劉、項集團中涌現(xiàn)出許多叱咤風云的人物。司馬遷為這些人物立傳,從他們與劉、項的關系中,可以進一步看出劉、項的個性。《高祖本紀》和《項羽本紀》是有明確主題的人物傳記,作者有意識地把那些與主題無關或關系不甚密切,甚至與主題抵觸的材料寫在別的傳記里。本傳不載,他傳發(fā)之,既體現(xiàn)了歷史的真實性,又保持了人物的形象性。在評價歷史人物時,不能僅限于本傳提供的材料,必要時還要聯(lián)系他傳提供的資料,否則,劉、項形象就不夠豐滿了。他傳側(cè)記,顯示了太史公使劉、項形象豐滿起來的特殊技巧。
如果說,《高祖本紀》側(cè)重寫劉邦的“圣主”形象,那么,從活躍在楚漢戰(zhàn)爭中相關人物的列傳中,讀者可以看到劉邦品質(zhì)的另一面。《酈生陸賈列傳》寫其流氓品性:“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秦末儒生在西漢立國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對待儒生,劉邦態(tài)度何其倨傲!《張丞相列傳》寫其蠻橫作風:“(周)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我何如主也?”部下面前,劉邦作風何其粗俗!《季布欒布列傳》寫其忘恩負義:“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結(jié)局悲慘的丁公在戰(zhàn)場上救過劉邦之命,劉邦心地何其歹毒!《淮陰侯列傳》寫其巧言令色:“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韓信求封齊王,劉邦惱怒萬分,張良、陳平附耳躡足,劉邦猛然警醒,變臉又何其迅速!總之,司馬遷掌握了許多表現(xiàn)劉邦無賴惡劣品行的材料,這些材料不便集中寫在《高祖本紀》中,遂曝光于他傳。
如果說,《項羽本紀》側(cè)重寫項羽的英雄悲劇,那么他傳中頂羽的個性弱點得到了更深刻的反映。《陳丞相世家》:“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潔好禮者多歸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淮陰侯列傳》:“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玩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陳平、韓信及其他人物對項羽的評論角度不一,褒貶不一,顯示出項羽形象的復雜性。“‘言語嘔嘔與‘喑噁叱咤,‘恭敬慈愛與‘僄悍滑賊,‘愛人禮士與‘妒賢嫉能,‘婦人之仁與‘屠坑殘滅,‘分食推飲與‘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違,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5}。“相反相違,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正體現(xiàn)了項羽的性格特點。項羽這一形象之所以給人以全面的立體的有血有肉的鮮活感覺,就在于司馬遷寫出了項羽性格的多面性和矛盾性。《史記》寫人物性格,無復雜錯綜如項羽者,體現(xiàn)了《史記》刻畫人物的高度技巧。
把握《史記》述史“互見”這一特點,還可以通過他傳讀出被本傳“掩蓋”的歷史真相。《高祖本紀》記彭越之反:“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僅讀此篇,恐怕真會以為彭越謀反,被誅理所當然。但是,只要讀一讀《彭越列傳》就會發(fā)現(xiàn),事實完全不是如此。《彭越列傳》:“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愿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于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劉邦猜忌功臣,往往以子虛烏有的“謀反”罪名除掉心腹之患,功臣彭越即遭此厄運。由此可見劉邦呂雉之狠毒陰鷙。這樁歷史冤案,僅讀本傳,無法察覺,他傳發(fā)之,始見真相。這種情況,正如李笠所云:“避諱與嫉惡,不敢明言是非,不忍隱避史事,故互見耳。”{6}
司馬遷筆下的劉、項形象有血有肉,呼之欲出,形象豐滿,又不失歷史之真,應歸因于互見法的巧妙運用。本傳著意刻畫人物形象,集中描寫和敘述矛盾最尖銳、斗爭最激烈的事件,突出人物的主要精神面貌。在此基礎上,將人物負面的次要的事跡載于他傳。“兩手分書,一喉異曲”,是司馬遷塑造劉、項形象的重要方法:傳、贊相補,用以表述理性的評判;重復累書,用以突出事件的意義;細節(jié)描繪,用以凸現(xiàn)人物的個性:遂使劉邦、項羽不僅是真實的歷史人物,而且是不朽的文學典型。
①{6}李笠《史記訂補》,轉(zhuǎn)引自安平秋等主編《〈史記〉教程》,華文出版社,2002.3 ②{5}錢鐘書《管錐編》第一冊,中華書局,1979.8 {3}張舜徽《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靳德俊《史記釋例》,轉(zhuǎn)引自張大可《〈史記〉研究》,華文出版社,2002.1
(江蘇省南通市第三中學 22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