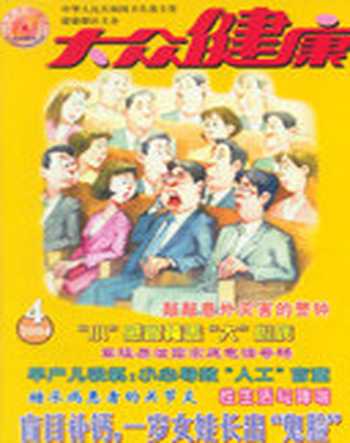多種防血栓食品
李家盈
臨床觀察證明,80%以上的心臟病與腦中風的急性發作,與動脈血栓形成有密切的關系。以下食物有稀釋血液、降低血液黏稠度與血小板的凝聚性的作用,可避免血栓形成。
黑木耳
黑木耳中所含的腺嘌呤核苷,具有抑制血小板凝聚的作用。實驗證明,吃黑木耳8個小時之后,血液依然難以凝聚,其作用強而持久,血液黏稠度高的患者,可多吃些黑木耳。
生姜
生姜中所含的姜油酮、姜烯酚等物質具有抗凝血功能。實驗證明,進食牛排、奶酪和奶油等食物,能促進血小板凝聚,加速血栓形成。如果同時吃一些生姜末或姜粉,血液就會保持良好狀態,不易出現血栓。
大蒜
大蒜中所含的阿霍烯是一種天然的血液稀釋劑,其效果明顯而持久。這種物質還可增強心臟的收縮力量,降低動脈血管的阻力,使血液循環通暢,預防血栓形成。
洋蔥
洋蔥中所含的槲皮酮具有神奇的作用。它能抑制血小板凝聚,對抗血栓形成。它還能阻止自由基對動脈血管的損害,使動脈血管內壁光滑,富有彈性。
海魚
多脂肪的海魚,如金槍魚、沙丁魚、大馬哈魚等富含N-3脂肪酸,這種特殊的物質能降低血液黏稠度及甘油三酯含量,使有益的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升高,從而減少動脈血栓形成的風險。
蔬菜與水果
蔬菜與水果中所含的維生素C及纖維素,能有效地阻止血小板凝聚,降低血液黏稠度,預防血栓形成。蔬菜與水果所含的葉酸、葉綠素、類黃酮、β-胡蘿卜素等,對心腦血管系統具有保護作用。
綠茶
綠茶具有十分明顯的對抗血栓形成的功能,其效果不亞于阿司匹林。實驗證明,飼以高脂肪高膽固醇的大鼠,同時飼以茶水,其主動脈內壁光滑通暢,而飼以同樣飼料、飲普通水的對照組大鼠的動脈血管壁則出現斑塊,受到嚴重損害。
紅葡萄酒
紅葡萄酒中所含的白藜蘆醇,能降低血小板的凝聚力,對抗血栓形成。飲用紫葡萄汁也具有對抗血栓形成的作用。
另外,辣椒、橄欖油、西瓜、甜瓜、菠蘿、蘑菇等也具有抗血栓形成的功能。
建設您每天從上述食物中選食2至3種,會幫您遠離可怕的血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