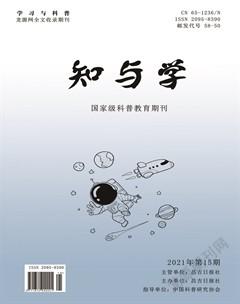語文教學中小學生表達能力培養分析
李園
摘要:在以往的小學教育中,教師的關注重點往往放在知識教學上。體現在語文學科中,則表現為教師非常重視學生對字詞等基礎知識的學習,要求學生背誦一些經典的內容。結果導致在培養小學生表達能力的時候,仍然采用了類似的理念和策略,對學生的表達做出種種限制,學生的表達存在非常眼中的“套路化”傾向。學生表達出的內容,很多時候是在某個模板下“湊字數”,并不是他們真實能力和想法的反映。這種情況必須改變。以下從培養小學生表達能力的意義及其途徑兩個方面展開論述,供大家參考。
關鍵詞:小學生;小學生表達能力;語文教學
口頭交流使用語言作為媒介。口語溝通能力可以準確判斷一個人是否具備與外界溝通和互動的能力。他們主要通過語言和情感的融合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良好的口語交流能力要求說話者具備一定的文學技巧和語法知識。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提高小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和口語交際能力,不僅可以提高他們的語言素養,還可以幫助學生鍛煉社交能力,實現他們全面發展的美好愿望。
一、培養小學生表達能力的意義
表達能力是會跟隨小學生一生的能力。在他們未來的學習、生活與工作中,有無數會用到語言表達能力的場合,而且口頭和書面表達能力同樣重要。有時,良好的表達能力還能為小學生的人生發展開辟新的道路,讓他們有能力去選擇真正適合自己,而且自己也感興趣的領域。即使把目光放在小學階段,學生想要在其他學科順利完成學習,與教師和同學朋友互動,同樣需要良好的表達能力。所以,表達能力的培養不僅對小學生在語文學科上的進步有重要意義,還關系到學生的人生未來,必須引起教師的足夠重視。
二、語文教學培養小學生表達能力的途徑
1、做好語言素材積累
學生想要完成語言表達,首先需要足夠的語言素材。學生沒有想要表達的內容,缺少組織語言文字的基本能力,是不可能很好地進行語言表達的。語言素材的積累有多種途徑,課堂上的閱讀教學,平時與其他人的口頭交流,都可以成為學生語言素材積累的重要來源。教師要提起學生的注意,讓學生能夠有意識地去進行語言素材積累,提升學生的學習效率;還要幫助學生做好語言素材的整理,提升積累語言素材在學生眼中的趣味性,使得學生逐漸能夠主動地去進行和完成語言素材積累,促進學生的自主成長。
例如,在學習《我變成了一棵樹》的時候,閱讀課文就是在進行語言素材的積累,學生可以學到新的字詞和語言組織方式。除此之外,教師還要指導學生去進行回憶和聯想,說一說自己曾經有過什么樣的有趣想象,這些口頭上的表達,也會成為學生語言素材的一部分。如果課堂時間足夠,教師還可以組織學生將課文內容加以改編并表演出來,提醒學生在表演時要用上課文中新出現的語言文字知識,表演時的角色、情景和同學們的反饋,都會激發學生的表達愿望,成為學生的語言素材。
2、開展豐富表達活動
總的來看,小學語文學科的語言表達形式主要包括口語和寫作兩種。這兩種表達應該是聯系在一起的,但不少教學在教學中則是將二者分開的,口語交際和習作教學沒有什么關系。其實我們只要思考一下,寫作的時候有“腹稿”這個詞,就可以明白以分開的眼光和方式來看待兩種表達方式是錯誤的。而且,口語表達和文字表達可以被包含在不同的活動之中,比如上文提到的表演,其中就包括口語表達,與一般的小組交流討論相比要更加有趣,后續還可以將感受寫下啦,成為文字表達。教師要實現靈活應用,豐富活動形式。
例如,習作“這樣想象真有趣”,在寫作之前,肯定要經過一個口頭交流討論,完成口語表達的過程。因為學生根據想象寫出來的內容必須合理,符合邏輯,通過口語交際可以就此進行判斷;也有的學生思路沒有打開,沒有什么想象的成果,也可以通過口頭交流幫助他們打開思路。在經過口頭交流對思路的梳理之后,學生的作文質量會更好。又如,對習作“身邊那些有特點的人”,教師可以鼓勵學生將自己想到的人和這個人的特點先畫出來,然后以畫作為基礎為大家介紹,相互交流補充,再完成寫作。
3、完善教學評價體系
學生的表達能力需要通過比較特殊的方式來進行評價,要有相應的評價體系,不能像考試一樣以單純的分數來對學生的表達能力下定義。通過上文的論述可以看出,表達能力是比較復雜的綜合能力,與學生對字詞等基礎知識的掌握,興趣愛好特點,性格上的特征等都有著很大的關系。有的小學生平時口頭表達上很流利,很積極,但就是不能較好地完成一篇作文,這種情況屢見不鮮。只有針對表達能力的特點建立起針對性的評價體系,才能滿足教學上的需要,對師生的教學活動進行有效的指導。
在這方面,教師首先要關注教學過程,展開對學生的過程性評價,或者提升過程性評價在總體評價中的比例。比如過程性評價在總體評價中占據70%的比例,剩下的30%由學生在考試中的作文成績來決定。另外,過程性評價的分數又要由多個部分組成,包括學生參與各種有關表達能力的教學活動時有什么樣的態度,進步情況如何,最好給予學生自評和互評的機會,還要利用好平時所做的教學記錄,以免因為記憶上的錯誤而造成評價的偏差。最后,除了分數之外,一定還要有描述性的評價,對學生加以鼓勵和指導。
總之,小學語文教師要堅持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看到表達能力在小學生發展成長中的重要作用,積極開展相關教學研究和實踐工作,調整優化教學策略,提升對學生表達能力的培養效果,為學生的未來人生開辟更多的可能,讓表達成為學生前進的有力工具和巨大動力。
參考文獻:
[1]莫承城. 小學語文表達能力的內涵闡釋與教學建議探討[J]. 新課程(小學版), 2019, 000(007):197.
[2]陳福英. 談小學語文教學中學生語言表達能力的培養[J]. 作文成功之路, 202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