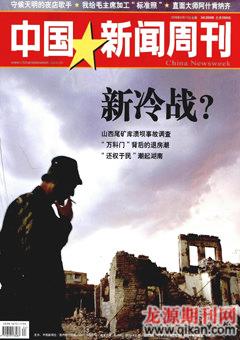空白的人格
楊 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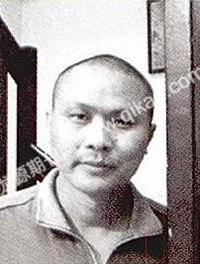
想想我這親戚的孩子,想想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在各個興衰混亂時期的榜樣,可以說是無窮無盡,難道在他們的書本里就沒有一位人格的典范,在他們心理的危難之時,從他們的心靈深處挺身而出?
我有一個親戚的小孩,15歲,一個多月前開始在夜里兩三點鐘時出走,親戚只好在后面緊跟。幾天前,他將這孩子送到腦科醫院檢查,經初步診斷有神經分裂的可能。兩口子大吃一驚的同時,也心驚膽寒。
說來話長,這孩子小時候并不生活在父母身邊,兩口子白天上班時將他交給父母,晚上回到父母家吃完飯后又將他丟給父母。孩子原先成績很好,自從喜歡上流行歌星、電腦之類,快速下降。成績不好,自然受歧視。我這親戚覺得奇怪,兒子竟然連一個朋友也沒有,他如此孤獨,不知城市化的推進無形中對此有無影響。
很快,這孩子對父親的管教會狠狠地扔來一只板凳,他把自己房間的門關上,你根本不知道他躺在床上在做些什么。這種情況持續了近兩年之后即出現了上述夜里出走之事。我這親戚對捆綁在腦科醫院病床上的兒子痛心不已,不知如何是好。
1936年,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張元濟在校閱《史記》時,常為其中的英雄人格所感動,因而想到要為青少年編一本書,以喚醒中華民族的人格。他從《史記》《左傳》《戰國策》中選出八篇故事,譯成白話文,并附評點,成書后定名《中華民族的人格》,于盧溝橋事變前兩月出版。
他在《編書的本意》中說:“我現在舉出的十幾位,都能表現出一種至高無上的人格,有的為盡職,有的為知恥,有的為復仇,歸根結底,都是孔圣人說的志士仁人。這些人都生在兩千多年前,可見我中華民族本來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謹守著我們先人的榜樣,保全著我們固有的精神,我中華民族不怕沒有復興的一日。”
這薄薄的只有幾十頁的小書的出版,立即引來日本人的屢次禁絕,這從1945年抗戰結束后,張元濟在好幾本《中華民族的人格》書前的題辭上可以看出:“一?二八”后,敵軍欲亡我國,嚴禁此書,妄冀消滅我國人之人格,豈知消滅不了,反益發揚,欣喜之余,書此記痛。
同年11月18日,他又在書前題詞:孔子曰殺身成仁,所謂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擲而人格不可失。圣訓昭垂,愿吾國人守之毋忘。
此書出版后,張元濟還曾要求胡適為其作序,以便擴大影響,而胡適給張的回信,儼然如古板與應時之爭,胡適說,“我讀了張先生的小冊子,也有點小小的意見,我頗望張先生在這些古代故事之外,另選一些漢以后的中國模范人物的故事,時代比較近些,使讀者感覺更真實、更親切,事跡不限于殺身、報仇,要注意一些有風骨,有肩膀,挑得起天下國家重擔子的人物。”胡適建議再增加馬援、諸葛亮、陶侃、王導、魏征、陸贄、范仲淹、韓琦、王安石、張居正等人。張元濟以年事哀孱為由,不復有下編。
然而胡適所說對我們今天所選之模范人物仍有啟迪意義,這同當年張元濟編寫《中華民族的人格》的緣由一樣。張元濟說他編這本書是因為這樣的理由:近幾十年來,設學堂,講究新學,但在社會上彌漫著一種驕奢、淫逸、貪污、詐偽、卑賤、頹惰、寡廉鮮恥的風氣,使我國家遭到這樣的田地,不能不說也是它的后果,回想四十年前,我們在那里提倡新教育的主張,到今朝,良心上也受著很嚴重的譴責。我們將人格的扶植,德性的涵養,都放在腦后,結果是如此了。他還引用張伯苓先生的一句話:我國教育太不適宜中國實際環境。
閑暇時我偶然翻翻現在初中的語文課本,深深感到雷鋒年代或董存瑞的戰爭年代已然過去,新時代人格榜樣的確立已是迫在眉睫。當然,這種人格榜樣一定是在我們幾千年的歷史中去尋找,去尋找的人也一定是有責任,有愛心,對中國之崛起有決定性信心的真正的教育家,這是真正的重任。
想想我這親戚的孩子,想想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在各個興衰混亂時期的榜樣,可以說是無窮無盡,難道在他們的書本里就沒有一位人格的典范,在他們心理的危難之時,從他們的心靈深處挺身而出?事實上是我這親戚對于舉著板凳朝自己砸來的兒子束手無策;對于他十五歲的孤獨更是大惑不解;對如今發生的這一幕,當然更不知如何是好了。而我也同樣常有無能、無力之感,大抵源于我小時候在人格培養方面的空白,而這空白隨年齡之日增愈顯緊迫和危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