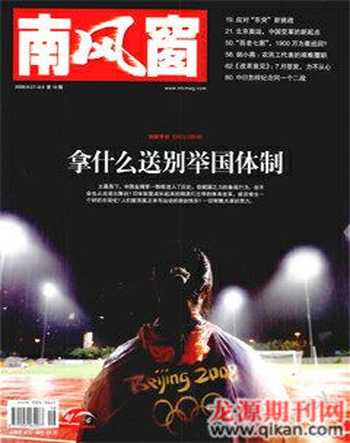奧運下一站:亞運廣州
甄靜慧
在劉江南眼中,“體育不僅能為國爭光,還應該為國增利”。在他推動下,廣州在全國城市最早公布了《體育競賽表演市場管理辦法》,降低社會力量辦體育的門檻,使社會力量舉辦的競賽表演越來越多,廣州離社會辦體育的理想狀態已經越來越近。
整個奧運期間都在北京觀摩的劉江南愛說“解放觀念”。
他的很多做法都與體育系統內的傳統思想相悖。業內人士習慣把2002年成功舉辦的湯尤杯羽毛球賽,鎖定為廣州以競賽表演業推動體育產業發展的一個成功范例——那一年,正是劉江南走馬上任廣州市體育局局長的第一年。
劉江南的另一個身份,是廣州亞組委副秘書長。北京奧運會結束后,中國舉辦的下一個重大國際體育賽會非2010年第16屆亞運會莫屬。奧運之后,亞運之前,南中國的廣州或許會是一處告別舉國體制、贏來體育產業市場化勢力真正崛起的合適地區。
沖動與熱情
作為學術專家和體育主管部門官員,劉江南從不否認自己對推動廣州體育產業發展有壓抑不住的沖動與熱情。
劉江南喜歡辦賽事在廣州體育界是出了名的。他上任,廣州每年舉辦的大小賽事馬上翻了數番,至少有四五十場。但劉局長辦賽事很奇怪,體育局光管申辦協調,不出錢、不操心,羽協、足協、籃協……眾多基層單位在市場上馬不停蹄地奔跑。
“我是故意逼他們的。”劉江南說。只給很少啟動資金,要協會承辦耗資甚大的大型賽事,他們除了用市場化運作方式外別無他選。
早在90年代初,還在廣州體育學院任職教授、副院長的劉江南就開始審視國內的體育事業:“體育除了健身功能、政治功能外,還包括一定的經濟功能。但這種經濟功能長期以來受經濟社會發展狀態約束,并沒有凸顯出來。”
1999年到2000年,廣東省委組織部派劉江南到美國進修,課程完畢,劉江南選擇了美國體育產業做研究課題,當時正值悉尼奧運會,中國第一次進入了前三強。“我明顯受到了美國人的尊重和華僑的贊揚。”可興奮勁過后,劉江南冷靜一想,心里仍然不是滋味。
作為體壇的霸主,美國并非不可超越,北京奧運,舉國體制便再放異彩。但越過競技體育來看體育產業的發展,美國與中國,相當于巨人與小孩的差距。根據當時的資料,美國2000年的體育產業總量已經達到2130億美元,成為全國第六位的支柱性產業。
“這個數字讓我感到非常震驚!”劉江南感嘆。那次調研回國后,他馬上提出一個口號,“體育不僅能為國爭光,還應該為國增利”。
競賽市場化
“體育產業包括很多內容,有競賽表演、體育用品、體育培訓等,我認為競賽表演業應該是龍頭。舉辦一場大型國際體育賽事,為城市帶來的人流、物流、資金流等附加值是難以估算的。”鎖定發展目標后,劉江南發現,他必須改革。

在體育系統傳統的觀念里,體育只是系統內的事業,是花錢不賺錢的事業。而大多數體育資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內部不會加以利用,又不釋放給市場,結果只是固步自封。
“很多體育局長曾向我抱怨說,每次辦賽事都是要體育局出錢,又沒人贊助,最后總是會虧很多錢,還不如不辦。”他們看到的是體育系統內的一場賽事,而劉江南看的,是這場賽事給整個城市帶來的附加值——當然,經濟效益也很重要。
劉江南盯上了體育局下面的基層單位——協會。2003年,中巴足球賽在廣州舉行,劉江南讓廣州市足協承辦比賽。據評估,這場比賽需要成本金1400萬。但作為主管部門,體育局只撥給足協150萬啟動資金。市足協只好使盡渾身解數向社會籌集資金。幸運的是,有兩家企業愿意投資這場賽事,成為了大股東,其他資金也很快到位。足協成立了一個組委會,以臨時股份制形式運作這筆資金,進行廣告招商、冠名等商業運作。
經過兩個月的商業運作,最后球賽不但完滿結束,而且獲得2200萬進賬,實現800萬盈利,扣除稅金后還凈賺200萬,社會投資者全部獲得了應有的回報。
“這叫‘放水養魚,使協會實體化。讓他們做到五有:有人、有錢、有權、有事、有基地。”劉江南笑著說,“現在協會的市場運作能力都很強了,廣州每年辦20場國際賽事,我一點都不用操心,而且沒有一場賽事要體育局全額撥款。”
改革者眼里的成功經驗,卻成了很多系統內人士的心頭之憂。他們覺得大型賽事運作漸漸離開體育局的操控,未免讓人不放心。“我說就是要給他們辦,要放這個權。”劉江南有一個更遠的夢想,“我希望通過現在對市場的培育與規范,把體育產業真正推向社會化。即使將來體育局因為體育改革而消失,也不用擔心沒人搞體育。”
2006年1月,在劉江南的推動下,廣州市搶在全國其他城市前面,最早公布了《廣州市體育競賽表演市場管理辦法》,不但降低了社會力量辦體育的門檻,同時規范市場,使社會力量舉辦的競賽表演越來越多。而近年,民營體育場館的經營也同樣發展得如火如荼。廣州離社會辦體育的理想狀態已經越來越近。
多辦比賽
劉江南的“放水養魚”,養的不僅是協會,還有體育場館。
近年,廣州舉辦的經典賽事包括湯尤杯、中巴賽、CBA全明星賽,WTA網球賽、羽毛球公開賽等。但重中之重,無疑是2010年亞運會。正如現在人們非常擔心鳥巢、水立方和其他場館在奧運會結束之后,很可能面臨運營的考驗,2010年廣州亞運會將新建的10余家場館在賽后的利用與經營,也是個難題。
廣州有過慘痛的教訓。天河體育中心是為第六屆全運會而建的,中心主任林彬表示,1987年中心投入使用之初就陷入了極大的經營困境。80年代末,天河還屬于廣州市郊,地理位置差,大家也根本沒有什么經營創收觀念,每年要靠政府撥款300萬才能維持基本運營。
1990年到2001年,是天河體育中心經營狀況的一個轉折期,首次采用了各場館以獨立法人單位身份,分開自主經營方式。一開始,這種方式的確調動了經營積極性,各場館各施其法,開創了很多新的場地經營利用方式,比如舉辦展覽、開演唱會、出租等。1993到1994年前后,天河體育中心年收入為600~800萬,實現了盈虧平衡;2000年到2002年,年收入達到2500萬。
“盈收提高不僅因為經營模式的改變,也要歸功于城市發展的東移,使體育中心交通、周邊設施等都更為便利。”但弊端也慢慢凸現,由于各場館完全獨立經營,造成資源、設施等的大量重復,人員臃腫,更形成了各種惡性競爭。
2002年劉江南上任后,開始對體育局下屬的天河體育中心進行新的改革,成立體育中心管理部門,對其下6個科技單位實行層級管理,當年就把原來的400多人減少到280多人。同時他要求“多辦比賽,
少做‘二房東”。
天河體育中心從1987年建成到2002年上半年,一共只舉辦過10次國際比賽,但2002年下半年始,與各大協會一起承辦了無數次大小賽事。通過市場化運作,這些賽事至少能夠收支持平,而部分有影響力的賽事能夠實現不錯的盈利。林彬說:“盡管是持平,但每舉辦一場賽事,對體育中心的影響力都大有提升。”
2002年,林彬聽從劉江南“少做二房東”的建議,把天河體育中心一塊出租的小廣場收了回來。當時廣場上有六片籃球場,體育中心做了改造,增加球場數量,將其辟為一個群眾籃球公園。“這個公園開始是抱著半公益性的想法去做的,門票3元/人,就可以在里面打一天。”但火爆程度出人意料,僅門票收入每年都能為體育中心創收500萬。而此前將這塊廣場出租,每年只能收到6萬元的租金。
2007年,天河體育中心達到空前的創收高峰,全年總收入8000多萬。
“總結了現有的經驗,廣州在新建亞運場館的規劃上其實已經充分考慮了賽后利用的因素。”廣州體育學院教授譚建湘表示。一方面,廣州對新建亞運場館的數量將會進行嚴格控制,充分利用原有場館,即使要新增大型場館,也盡量建在交通便利,有群眾需求的地方,“如南沙、番禺、大學城因為原來沒有場館,所以都將會新建一個大場館。”
另一方面則計劃建一些臨時場館。“強調場館多功能化也很重要,盡量不為某個特殊項目蓋一個場館,即使建造也只采用臨建。”譚建湘強調。
足球困境
然而市場化道路并非一帆風順,受體制約束,走得磕磕碰碰的最典型例子,是廣州的足球俱樂部。
廣東足球曾經代表了中國足球的一個時代,在廣州,足球運動群眾基礎一點都不亞于羽毛球。2002年甫一上任,劉江南就為廣州足球隊提出了沖超目標。去年底,廣州隊終于沖超成功。然而對廣藥足球俱樂部總經理寧智雄來說,體會到的是更多的困惑與無奈。
寧智雄2007年就任廣藥足球俱樂部總經理。到任那天,他發現這里根本沒有一個真正像樣的俱樂部。廣藥足球俱樂部的招牌樹立在白云山制藥股份有限公司旁邊,那里只是一個辦公地點,旁邊有一塊足球場,也是租借的。而球隊的主場越秀山球場,也不屬球隊所有,每次比賽前都要繳付租金,“什么叫主場?天天在那里訓練,場上各個位置的土壤軟硬度都知道,經常有球迷到場捧場,那才叫主場。”
“沒有自己的會員活動中心,沒有周邊產品展覽館,中超公司要求每支球隊要有四塊球場,現在我們只有一塊。”寧智雄攤了攤手。運營一個足球俱樂部,包括球員和主教練薪金、競賽獎金以及日常基本費用等,每年得投入兩三千萬。然而因為盈利模式的不成熟,要盈收平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更遑論有多余的資金作固定資產投入了。從最初的太陽神,到松日、吉利、香雪、日之泉,廣州足球俱樂部數度易主,原因無非一點:長期入不敷出令投資企業不堪重負。
現在廣藥隊最大的三塊盈收是招商廣告、門票和周邊產業銷售收入。而西方國家成熟足球俱樂部所依賴的電視轉播權、彩票、買賣球員、上市募資等盈利模式,在國內都面臨發育不良和體制限制。
足協成立的“中超公司”,是所有中超球隊在經營上都繞不過的一道坎。即使是在俱樂部所在地域舉行球賽,俱樂部也不能自主經營電視轉播權,而要由中超公司委任另一家公司統一經營。雖然到了年底,中超公司會把全年的轉播權及其他廣告經營所得分成給每一個足球俱樂部(2007年各足球俱樂部分得300萬),但寧智雄認為,在球市比較好的廣州,如果能在轉播權上得到自主經營權,營收應該遠遠不止這個數字。
球賽的廣告贊助商也具有排他性,如果中超公司拉來一位贊助商,俱樂部就不能再拉同一行業的企業贊助,在招商廣告、翻牌廣告經營上也受到了很大限制。
廣藥足球俱樂部每年的盈收數字都頗有玄機。廣藥集團旗下企業眾多,其中包括兩家上市公司。足球俱樂部采用所謂股份制形式,所有股東都是集團旗下的企業。每一年,這些企業都會花幾百萬在各場賽事中冠名、投廣告。雖然這些球場廣告確實對企業起到宣傳作用,但還是頗有內部攤派意味。
正如寧智雄所看到的,這是體制的問題,如果整個機制不能進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可以從中起的作用很少,最多也就是在政策上給予企業一些其他方面的補償。
萌芽之中
不過,從體育局長劉江南的角度看來,經營困境只是其中一方面,如果跳出體育來看足球,廣州隊沖超成功,不但為廣州增加了一項品牌賽事,而且對投資冠名企業的知名度、美譽度都有正面宣傳作用。
“我之前不知道他們的困難,但廣藥集團接手足球俱樂部,對拉動廣州體育產業發展肯定是功不可沒的,體育局能幫上忙的一定會幫。”但問題在于,足球產業的改制雖然不完善,無法走上純市場化的道路,但它又確實已經脫離了與主管部門的直接隸屬關系。俱樂部托管給企業后,已經不歸體育局管了,體育局不可能直接在資金上給予支持。
現在劉江南可以承諾的,是在練習和比賽場地的提供上給予足球俱樂部更大支持,以及親自鼓動企業贊助中超賽事的冠名和廣告。“如果廣州隊能在中超甚至世界賽事上打出好成績,像籃球運動一樣多發掘出優秀球員,改善經營還是有希望的。”
令人欣慰的一點是,沖超成功和大力發展會員制,對今年廣藥隊主場球賽的上座率已經產生了正面影響,門票銷售量從以往的1萬以下'上升到2萬以上。
說到底,這又跟該體育項目的發展成熟程度,以及整個城市體育產業發展程度相輔相承。只有當球隊的群眾認知度越來越高,城市競賽表演業發展相對成熟,社會和企業對贊助體育賽事的熱情普遍高漲,中超賽事離真正實現盈利才會越來越近。屆時,廣州離體育產業化的目標也會越來越近。
雖然艱難,但政府主導的市場探索道路一直在前行。譚建湘告訴記者,國家即將出臺體育產業統計指標體系,對產值、從業人員等都會有一個規范的統計標準。在發達國家,體育產業的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里起碼能占到幾個百分點,而在中國大多數城市,比例只有百分之零點幾。“經過這些年的努力,廣州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經好了很多,已經超過1%了。”
劉江南卻并不過分樂觀。由于體制的束縛,盡管有地方政府部門的力推,體育產業發展進程中很多事情還是擺脫不了計劃經濟的影響。即使是廣州最引以為豪的賽事運作,離國外完全市場化操作的模式還有一段距離。“所以說,我們的體育產業發展還處于萌芽狀態,雖然有了一定成績,但不要過高評估其發展。我從來不談體育‘產業化這個詞,因為確實還沒到這個程度。”劉江南強調。
——評《休閑體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