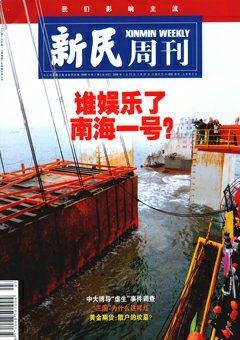“屁股下的腐敗”何以治愈?
陳 憲
講公車改革,著實有年頭了。朱镕基任國務院總理那會兒,就準備大干一場,好好整治一下這個百姓詬病已久的“屁股下的腐敗”。中國官員擁有300多萬輛公車,每年公車消費無論2000萬元或3000萬元之說更準確,均可謂世界之最。然而,政府至今未能拿下這個“老大難”。可見此病癥之頑,根深蒂固、盤根錯節,哪是限時限刻就能輕易解決的。
約10年了,公車改革的呼聲不絕。據我所知,在我國的發達地區,如江浙滬一帶,基層政府的公車改革盡管短期成本不低,但還是頗有進展,且取得實效的。然而,最近的幾則報道又讓我們疑惑不少,灰心也不少,不禁試問:公車病癥靶點找準沒有?公車改革何時了?
據近日《新華每日電訊》報道,陜西省人事廳包括編制辦近年來公務車輛配備混亂,公車使用嚴重超標,在廳機關出現了一個“超級車隊”:只有126名公務員的廳機關正在使用的公車達42輛,這還不包括一些購買后仍未掛牌使用的車輛,也不包括下屬事業單位的十多輛汽車。該報道還稱,10年前這個廳才配備5輛汽車,而現在增加到了40多輛。怎么公車越改越多了?根據觀察和了解,這種公車越改越多的現象,有一定的普遍性。
公車消費是政府公務消費的一個大頭,社會上對公車超標配置(車輛排量超標、數量超標)、公車私用等問題一直存在諸多議論。近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從各級政府到有關部門,關于加強公車管理下發了許多文件、通知,收效卻并不明顯。這次陜西省人事廳“超級車隊”暴露的問題,具有典型意義。公車泛濫,不僅增加財政支出和資源消耗(各種口徑的統計都表明,我國每年公車消費都達數千億元),而且滋生特權。這與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相去甚遠。最近,海南省委、省政府辦公廳轉發了省紀委等有關部門的文件,要求對原發放專用號牌的車輛,從2007年12月16日開始,由所在單位派員到屬地車管所按普通車輛牌號自動選取程序選號,更換為普通號段車輛。對此,贊同者認為,取消公務車輛專用車牌,相當于抹掉了“特權”(這是形式的特權,實質的特權是公車使用權)的痕跡,將黨政機關車輛和普通車輛擺在了同樣的地位,是一件利民的好事。但也有人表示擔心:這一做法雖然摒棄了“特權標志”,卻為公車私用、亂用創造了條件。從這些不同意見中不難發現,此舉之所以左右不是,就是因為治標不治本。治本的辦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取消公車。而且,我們還要糾正近些年來政府部門形成的一個“習慣”:所有公務人員的公務活動,都必須要用本單位配置的公車來提供交通服務。實際上,在大多數情況下,公共汽車、地鐵、出租車等其他交通方式,同樣可以滿足公務活動的需要。
另據其他媒體報道,近日《舟山日報》以一個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舟山市市級機關(單位)車輛油耗及維修費用情況公示》,將全市480輛公車的單位名稱、車輛號碼、耗油量、里程、修理費用等,按季度匯總的方式向全社會張榜公布。有評論者對此評價甚高,認為,其他治理公車的措施都收效甚微,問題在于,相當多的制度根本不執行,而監督者也根本不能監督到位。假如全國各地都像舟山這樣,公車花費的大“窟窿”還能堵不住嗎?我以為,他太樂觀了。盡管此舉透明度甚高,便于監督,但是,一方面亦會有失偏頗,因為每輛車的公務肯定不等,另一方面,對違規用車者沒有相應的查處跟上,又何用之有﹖
其實,想真正治愈公車腐敗,早就有了良方,嚴格按照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的明確規定,只有正省部級干部才能按一人一輛配備專車,副省部級干部都只是工作相對固定用車,副省部級離退休干部不配備專車。由此能夠作出什么推論,就不言自明了。公車改革的正確方向,就是按規定加快取消不按規定配備的公車。作為一種過渡,可以根據年齡、職級、任職時間等,采取可操作的措施,一級監督一級,強制執行。如果不執行,或執行不力,是否可視為一種集體性腐敗、制度性腐敗,由有關部門嚴加查處?因為,這也是一種變相占有、侵吞公共資源。
公車占有公共資源還有另一種表現形式,即占有本來就很擁擠的道路。在中國的大城市,幾乎都存在日益嚴重的堵車問題。這里,公車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是一種典型的與民爭利。現在,大小官員都說,老百姓的事最大。對老百姓來說,每天上下班的事,又是一天中幾件大事之一。因此,公車的事無論如何也不會比這事大。而且,官員坐公交或地鐵上班,還能更多地了解百姓疾苦。就算用私車或打車上下班,花了自己的錢,也能更多地體會一些百姓過日子的不容易。
無疑,公車改革將使公車使用者的既得利益受到影響,但對于這些明顯不能繼續存在的既得利益,早改比晚改好,況且現在已經不早了。(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