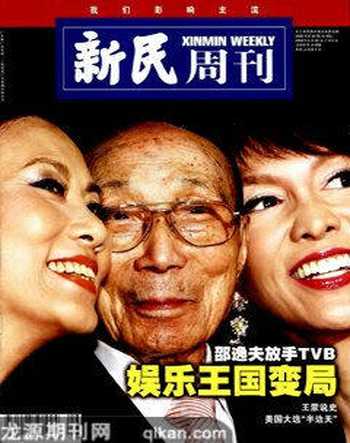讓中國移植走上“臺面”
黃 祺
緊要的任務是建立一個器官移植供受系統,讓自愿捐獻的器官最高效地用于患者的救治。這個系統計劃在《人體器官移植條例》頒布后5年內,也就是2012年以前完成。
中國完成第一例器官移植手術至今,已經30年,如今,每年約有1萬病人因為接受器官移植手術而重獲新生,并回到正常的生活中。但是,中國移植事業,也曾經因為管理的缺失而受詬病。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日前接受《新民周刊》采訪,詳解怎樣讓中國的移植事業走上“臺面”。
從“亂”到“治”
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可能是最愿意談及器官移植這個“敏感話題”的中國官員。在四川抗震救災的繁忙時刻,黃潔夫還是抽出時間,帶著幾位司長參加上海“第三屆移植運動會”開幕式,為這個沒有多少中國人聽說過的運動會造勢。黃潔夫反復強調的是,捐獻器官挽救一位病人的價值和意義與救援人員在地震廢墟中救出生命,是一樣的重大。

雖然自己是肝臟移植專家出身,但黃潔夫從不“護短”。在2006年接受媒體采訪時,黃潔夫就毫不客氣地指出中國器官移植事業的“混亂”,當時,中國每年器官移植的數量達到“峰值”,批評的聲音同樣也在“峰值”。現在,黃潔夫仍然堅守在推動中國移植事業規范化的陣營,但他還是不回避批評的聲音:“以前認為,中國的器官移植系統有陰暗的一面,認為見不得陽光。”
中國肝移植注冊中心助理主任王海波公布了中國肝移植注冊系統(CLTR)的統計數據,這個由香港大學瑪麗醫院和安斯泰來公司共同建立的系統,是唯一獲得中國衛生部授權的肝移植注冊系統。在CLTR的一個柱狀圖上,2005年到2006年度上的藍色柱遙遙領先于它的左鄰右舍。數據顯示,2005年中國肝移植手術一共實施了2500例,2006年突破3000例。跟肝移植的情況相似,中國各種器官移植手術的數量,在2005年左右都達到了“頂峰”,在此之前,每年移植手術的數量都在快速攀升,而從2006年以后,立柱立即滑落,變得很矮。
柱狀圖形象地描繪了中國器官移植事業在近10年來的發展狀況。1980年代開始,一批肝臟、腎臟外科專家陸續從國外留學歸來,帶回國外先進的器官移植技術,并開始在中國開展移植手術,黃潔夫副部長也是這其中的一員。到現在,中國器官移植的手術水平,在一些大型醫院里已經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復旦大學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樊嘉教授稱,該中心的肝移植5年存活率在60%左右,這個數字已接近65%-70%的國際水平。
技術的進步給更多患者帶來希望,一些原本被“判死刑”的患者由于器官移植手術重獲新生,再加上中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患者需要實施器官移植手術。
在2007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實施之前,中國一共有600多家醫院開展器官移植手術,形成了讓人擔心的器官移植“繁榮”場面。黃潔夫對那個階段的總結是:“國內移植技術進步,但法規、倫理規范的建設滯后。”
與需求突增形成鮮明差別的是,器官自愿捐獻的熱情卻未能發動,器官一直是稀缺資源。2005年左右,中國器官移植數量“突飛猛進”,但這個時候,中國并沒有建立起器官資源捐獻系統,多數器官來自包括死刑犯在內的個人自愿捐獻,而非法的器官買賣現象也一直存在。
供需之間的巨大差距自然會滋生非法買賣市場的產生。黃潔夫坦承,這種供需差異在世界上其他國家也同樣存在,“如不加以規范,就會促成非法的市場”。作為主管部門,中國衛生部并非對此視而不見,政策研究的工作從沒有間斷。隨著法規的出臺,器官移植規范化的“拐點”終于出現。
2006年7月1日起,衛生部開始實施《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管理規定》,2007年3月21日國務院通過《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并于2007年5月1日起施行。后一個條例是中國首個針對器官移植的正式條例,也是中國器官移植事業走向規范化的里程碑。
黃潔夫把這個條例叫做“世界上最嚴格的條例”,其中的“嚴格”除了針對開展手術的人員、技術和設施,更是針對器官捐獻的條件,這些規定,目標都朝向之前被詬病最多的“器官買賣”現象。“我國是管得最嚴的國家之一。”黃潔夫介紹說。條例頒布以后,600多家開展器官移植的醫院,多數被取消資格,只剩下164家獲準繼續開展器官移植手術。
建立合法捐獻系統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的實施大大扭轉了器官移植手術“泛濫”的現象,但對于整個器官移植事業來說,移植手術只是“中游”,如果“上游”的器官自愿捐獻不能解決,器官資源緊缺,還是無法避免非法的器官買賣現象的出現。
近年,由于管理嚴格,傳統的器官來源越來越少,親屬間活體器官移植被認為是解決燃眉之急的辦法,很多患者在醫生的建議下考慮活體器官移植。《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定,活體器官移植的捐獻者和受著之間,只能是三種關系:配偶、直系血親或者三代以內旁系血親,以及“有證據證明與活體器官捐贈人存在因幫扶等形成親情關系的人員”。條例對活體器官移植的限制,同樣是為了避免器官買賣的發生。
但從醫學倫理的角度,親屬間活體器官移植并不是最佳的方案。“我們鼓勵親屬間的活體器官移植,但不宜大力提倡,因為對于捐獻者來說,畢竟存在一定的風險,而且術后會影響部分勞動力。”黃潔夫說。
一方面要盡力消滅非法的器官買賣現象,另一方面患者的移植需求又得不到滿足,黃潔夫認為,要緩解這個矛盾,現在緊要的任務是建立一個器官移植供受系統,讓自愿捐獻的器官最高效地用于患者的救治。這個系統計劃在《人體器官移植條例》頒布后5年內,也就是2012年以前完成。
“我們把這個重任交給紅十字會,抗震救災告一段落以后就會啟動系統的籌建。”在移植運動會期間的一個會議上,黃潔夫扭過頭,鄭重地對身旁中國紅十字會的一位官員說。黃潔夫說,這個系統應該是一個民間性質的系統,由衛生部指導建立,政府授予權力。
美國等國家都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器官獲取組織,這些組織不僅要負責宣傳、招募器官捐獻的志愿者,而且要派出專業人員去維護志愿者捐獻的器官,然后在等待移植的患者中篩選出最“合適”的對象。
在中國,目前只有一家民間性質的“中國器官捐獻管理委員會”承擔類似的功能。“沒有捐獻者,一切等于零。”“中國器官捐獻管理委員會”負責人陳忠華教授道出了矛盾的根源。2006年,中國內地的器官自愿捐獻率是百萬分之零點零一三,2007年是百萬分之零點零三,這個數字與西班牙相差1000倍,與香港相差100倍。陳忠華介紹說,中國的自愿器官捐贈數量少得可憐,“符合國際標準程序的器官捐贈”,從2003年至今,只有90人。

中國內地呼吁自愿器官捐獻,已經很多年,但收效卻微弱。黃潔夫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澳大利亞留學時,澳大利亞80%的人持有器官自愿捐獻卡,在很多發達國家,申領駕駛護照時就可以領到一張自愿捐獻卡,如果持卡人不幸遭遇車禍,捐獻卡就可以證明遇難者愿意捐獻器官的愿望。“中國每年遭遇車禍身亡的人數是個龐大的數字,如果這些人中有10%愿意捐獻器官,那么就可以讓很多病人得到移植的機會。”黃潔夫說。
在黃潔夫看來,人們對器官移植認識和理解的有限決定了中國自愿器官捐贈數量稀少的現狀。在第三屆中國移植運動會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一位記者向一對腎移植的親屬提問:“你捐獻的是雙腎還是單側腎?”這樣的問題,讓這位將腎臟捐獻給自己弟弟的捐獻者覺得很好笑。
將來中國器官移植供受系統,同樣會涵蓋器官自愿捐獻的宣傳、數據管理、資源分配等等功能,這個系統被寄予厚望。從移植數量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肝移植大國,依靠未來的器官移植供受系統,黃潔夫說:“希望中國能成為最符合WHO倫理標準的器官移植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