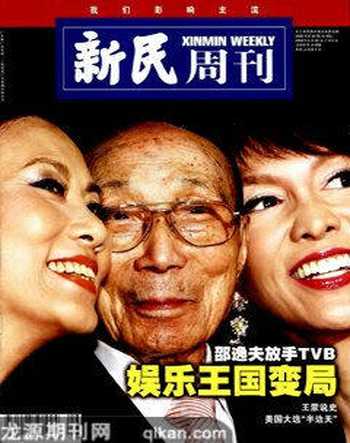“共同富裕的道路”走得通嗎?
江曉原
事實上,今天的環境保護問題,首先不是一個科學技術問題,甚至幾乎就不是科學技術問題,而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問題。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我們非常熟悉的話頭,它既是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后對其余人的承諾,也是對那部分已經先富起來的人的提醒。但是,這條“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不是肯定能走通?我們以前從不思考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就假定了答案:肯定能夠走通,只是時間早晚而已。
這種關于“共同富裕”的信念,對于一個鄉,一個縣,乃至一個國家,確實都有可能成立。但是,如果將范圍擴大到全世界,它能不能夠成立呢?
這種全球“共同富裕”的類似“大同世界”的信念,實際上是以“無限地球”作為前提的,即假定了地球的資源是無限的——或者至少也是供全人類使用綽綽有余的。
然而,我們現在已經進入“有限地球時代”——其實人類從一開始就是處在有限地球時代,只是我們直到很晚的時候自己才意識到這一點。
所謂有限地球時代,意思是說,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還有一個平行的說法是:地球凈化、容忍污染的能力是有限的。
這兩個“有限”,在今天早已成為普遍的常識,可是在唯科學主義的信念——相信科學早晚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之下,這個常識竟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取而代之的,是所謂“人定勝天”的盲目信念——相信我們對大自然瘋狂的征服和榨取可以永遠持續下去。在這樣的信念之下,地球上的資源,地球凈化、容忍污染的能力,都已經被假想為無限的。即便在理性的層面沒有否認其有限性,但這兩個極限也被推到了無窮遠處——在眼下就可以先當作無限來盡情榨取。
在西方,從1962年蕾切爾·卡森出版她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書,強烈警告地球容忍污染的極限開始,環境保護和“有限地球”的觀念就日益深入人心,最終匯成全球性的運動。
在中國,最初我們曾經認為,“環境污染”是資本主義國家才有的問題,和我們毫無關系。后來我們被現實所教育,知道這是誰也避免不了的問題,而且西方國家在環保方面已經走在前面了。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還想當然地將環境保護問題理解成一個科學技術問題。以為只要進一步發展治理污染的技術,就可以逐步解決問題。
但是賈雷德·戴蒙德在他2005年的新著《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Collapse:How SocietiesChoose to Fall or Succeed)中指出,事實上,今天的環境保護問題,首先不是一個科學技術問題,甚至幾乎就不是科學技術問題,而是徹頭徹尾的政治問題。
10年前戴蒙德寫了《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Guns,Germs,andSteel:The FatesofHumanSocieties,1997)一書,試圖探討“人類史作為一門科學”的可能性。如果說他當時的這種意圖還有一些唯科學主義色彩的話——盡管他是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使用“科學”這個詞的,那么在《崩潰》的結尾部分,他竟然已經明確地宣告:“我們不需要科學技術來解決問題!”——他的理由是:“雖然新科技可能會有所作為,但大部分問題,只是需要政治力量來實施已有的解決方案。”確實,環境問題不是靠進一步發展科學技術就能解決的;而且,環境污染問題,歸根結底也不是科學技術帶來的。
為什么環保問題不是科學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呢?戴蒙德說,歸根結底,這是因為西方有一部分人搶先過上了“窮奢極欲的”——也即所謂“現代化的”——的生活而帶來的。而這種現代化生活是高能耗、高污染的。但是現在,這種西方生活方式已經成為全世界人民追求的榜樣。然而,“如果中國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國家,以及當前第一世界國家,都過著窮奢極欲的生活,地球必定無法承受”。
同時戴蒙德又知道:“如果告訴中國,不要向往第一世界國家的生活水平,中國當然不能容忍這種態度。”但是你要第一世界國家人民放棄他們如今的生活水平,他們當然也不能容忍。而大家都過上“窮奢極欲”的生活呢?地球又不能容忍。這樣一來,環境問題,資源問題,發展問題,自然就成為未來最大的政治問題了。
戴蒙德希望第一世界的人們能夠認識到,即使你們現在還可以向第三世界轉移污染,但終究會有無法繼續轉移的那一天;即使第三世界不反抗(這實際上肯定是不可能的),地球承受污染的極限也很快就要到了。這就是我們面對的現實。
在全球尺度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走得通嗎?
《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
(美)賈雷德·戴蒙德著,江瀅等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