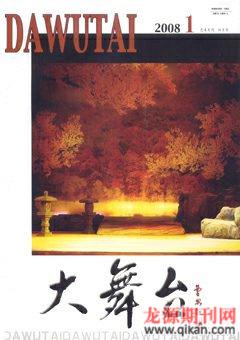淺析隱喻在文學作品中的抒情作用
高 文
【摘要】情感性作為文學藝術的基本特征通常是在隱喻、象征的基礎上得以實現的,從隱喻所具有的抒情功能和藝術情感的表現離不開隱喻這兩個方面研究隱喻在文學作品中的抒情作用。反襯表現法是是對人們特殊情感的對反性表現形式的隱喻或象征。
【關鍵詞】情感性;隱喻;反襯表現法
情感性是文學藝術的基本特征之一,任何文學作品都包含著作家的主觀情感。文學的情感性越濃烈,越能感染讀者,就越富有藝術魅力。文學作品采用語言作為媒介,在表現人物的內心情感時,形成一種具有審美特征的抒情話語形式。抒情性話語突出可感性,具有很強的表現力,而且通常是在隱喻、象征的基礎上得以實現的,以至于我們不得不說,形象的必然是隱喻的,而情感的必然也是隱喻的。
文學藝術的情感性與隱喻的內在關系可以通過以下兩個角度的分析進行說明。
一、隱喻所具有的抒情功能
西方隱喻學界對隱喻的本質考察中,除了替換論、比較論、互動論外,還有情感論一派觀點。情感論認為,隱喻不是感受、認知外部客觀世界的有效途徑和方法。人們之所以熱衷于使用隱喻是看中了隱喻的情感沖擊力,換言之,隱喻的功能不是感受、體驗、把握和理解外部世界,不是以一種語言單位替換另一種語言單位,而是激蕩情感,或者說隱喻是煽情的工具。情感論進而認為,在隱喻中,情感與意義此消彼長,情感的存在以意義的喪失為前提,意義的獲取也必須以犧牲情感為代價。認知意義與情感意義是不可得兼的“魚”與“熊掌”,獲取認知意義就必須放棄情感意義,獲取情感意義就必須放棄認知意義。比爾茲利曾對情感論隱喻觀作了很好的概括說明:“根據情感論,只有當一個詞具有明確的所指物時,這個詞才有意義。例如,刀的鋒利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加以驗證,因此‘鋒利的刀這樣的短語是有意義的。我們還可以假定‘鋒利具有負面的情感內含,它來自我們對鋒利事物的體驗。現在,當我們談論‘鋒利的刺刀或‘鋒利的錐子時,其情感內含是并不強烈的,因為這些短語是有意義的。但是當我們談論‘鋒利的北風、‘鋒利的商人或‘鋒利的舌頭時,對鋒利的驗證就是不可能的了,因此盡管短語中的單個詞語是有意義的,但合在一起就沒有意義。此時,‘鋒利這個形容詞所具有的情感含義釋放了出來,并得以強化。”[1](p25-26)
情感論將隱喻的認知功能與抒情功能對立起來的觀點顯然是不能成立的。其一,隱喻是人類心智的胚胎,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它逐漸滲透到人類心智的方方面面,從而使隱喻具有了多重的功能,它既具有認知功能,又具有抒情功能,既具有修辭功能,又具有社會功能等。只看到隱喻的抒情功能而忽視隱喻的其它功能,對隱喻在人類文化建構過程中作用的認識未免過于狹隘、片面了。其二,語言以及一切符號的意義具有多面性,既可以是某種理性的認知意義,也可以是某種情感態度,既可以是感性的實體對象,也可以是抽象的非實體對象。總之,符號指涉的一切對象,都是符號的意義。將符號的情感意蘊排斥在意義大門之外,暴露了對符號意義的極其偏狹的理解。其三,在隱喻中,情感意義與認知意義的表達可以有不同的側重,但并非水火不相容的,而是統一共存的。
隱喻學中的情感論的總體觀點雖然有待重新認識,但它對隱喻的抒情功能的高度肯定則是有見地的。隱喻的功能不僅僅是抒情,但抒情的確是藝術隱喻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因此,藝術的情感性常常借助隱喻性的表現方式表現就不足為怪了。
二、藝術情感的表現離不開隱喻
隱喻具有抒情功能只說明了藝術抒情與隱喻聯姻的可能性,不僅如此,藝術的抒情性與隱喻之間還存在一種必然的關系。
藝術情感是內在抽象的,情感的表現必須付諸一定的直觀形式,即憑借一定的符號媒介。不同藝術形式正是依據不同的符號媒介而存在的:音樂的符號媒介是聲音的長短、高低及其節奏、旋律,舞蹈的符號媒介是表情和形體動作,繪畫的符號媒介是色彩、線條,文學的符號媒介是語言、文字。不同藝術形式雖然具有不同的符號媒介,但其作用卻是共同的,即給抽象的情感賦予一種可以訴諸感覺器官從而可以看、可以聽、可以觸摸、可以感受的直觀形式。
藝術情感并不是隨便付諸什么直觀形式就能得到表現。對特定藝術情感的表現,需要借助特定的符號媒介,即特定符號媒介的選擇、構成要符合藝術表現的形式法則。而藝術的形式法則之一就是要求藝術的符號表現形式與其表現的情感內容之間具有內在的關系,這個內在關系就是相似或相關性的聯系,即象征、隱喻的關系。例如在舞蹈中,強烈的情感需要通過夸張的表情、力度很大的形體動作加以表現,平靜、柔和的情感需要緩慢、輕盈的形體動作加以表現;在音樂中,歡快熱烈的情感需要快速的節奏、明朗的旋律加以表現,悲痛欲絕的情感需要婉轉、高音域或音程跳躍性很大的旋律加以表現;在繪畫中,色彩、光線的明暗、濃淡,線條的繁密、疏朗,畫面的凝重、清新等總是分別與情感的熱烈與低沉、莊重與恬適、強烈與平和等相對應;在文學作品中,直接的符號表現形式是語言,而實際上的符號表意單位則是由語言構成的意象,因此,由語言符號構成的意象與被表現的情感之間同樣需要具有隱喻或象征的關系,例如,楊柳依依狀惜別之情,雨雪霏霏狀心緒的紛亂、凄涼,暮靄沉沉狀心地迷惘,一江春水狀憂愁深長……所以,在藝術作品中,情感的表現必然是直觀的,而直觀形式與情感的關系必然是隱喻的。
在藝術表現中還有反襯表現法,即符號表現形式的直觀特征與情感之間似乎非相似性的隱喻關系,而是對反的關系,如以樂寫悲或以悲寫樂、以動寫靜或以靜寫動等。老子就倡導“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老子》第四十一章)的藝術標準,后來蘇軾發揮道:“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蘇軾《送參寥師》)講的就是這個道理,這個道理就叫藝術表現的辯證法。表面看,在以悲寫樂、以樂寫悲、以動寫靜、以靜寫動中,藝術表現形式與情感內容之間是對反關系而非相似性的隱喻關系,然而從深層意義看,之所以能以樂寫悲或以悲寫樂、以動寫靜或以靜寫動,根本原因仍在于二者之間存在一種更深層次上的相似性。也就是說,藝術形式相對情感內容的對反特征不過是對人們在生活中情感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摹仿的結果。因為生活中人在悲痛欲絕時往往會狂笑不止,在異常高興時往往會痛哭流淚,在平靜的面部表情背后往往隱藏著劇烈的心理活動。在藝術表現中,當表達這些異常強烈的情感時,藝術家往往借助以上生活體驗,用特定的方式模擬人們在生活中強烈情感的這種特殊表現方式。白居易《琵琶行》描寫琵琶女的高超演奏技藝和巨大的藝術感染力時,用的正是這種手法:“冰泉冷澀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別有幽情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東船西舫悄無聲,唯見江心秋月白。”所以,藝術表現形式相對于被表現情感內容的對反性特征,是對生活中人們特殊情感的對反性表現形式的模仿,或者說,這種具有對反性特征的藝術表現形式歸根結底是對生活中人們特殊情感的對反性表現形式的隱喻或象征。
中國古典悲劇理論在悲劇情感結構和悲劇情節布局上十分重視“苦樂相錯,悲喜相乘”的反襯藝術表現方法。元代陳剛中就主張“抑圣為狂,寓哭于笑”。祁彪佳的《遠山堂劇品》評“簪花髻”時說:“人謂于寂寥中能豪爽,不知于歌笑中見哭泣耳。曲白指東扯西,點點是英雄之淚。曲至此,妙入神矣!” “于歌笑中見哭泣”,這正是那種“透過眼淚的微笑”,在貌似喜樂歡笑之下透出掩飾不住的悲哀。正如《桃花扇》中老禮贊所說:“演得快意,演得傷心。無端笑哈哈,不覺淚紛紛”。笑總是無端的,勉強的,而淚卻是不覺的,情不自禁,發自內心的。需要以強笑來掩飾的悲,才是潛藏于人心中的最大的悲哀。正如梁啟超所說:“然其外愈達觀者,實其內愈哀痛、愈辛酸之表征。”所以說,中國的悲劇是以喜為肌膚悲作魂的。喜和悲這兩種人類最重要的情感是相互依存、互相交融并相互映襯的。呂天成把悲喜交錯看作是一種高層次藝術境界,認為《琵琶記》“布景寫情,真有運斤成風之妙,穿插甚合局段,苦樂相錯,具見體裁。可師,可法,而不可及也。”雖不可及,卻可效法,是對劇作家的一個重要的藝術技巧要求。清代王夫之指出:“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可見,哀景和樂景都可以成為對方的鋪墊或陪襯,為對方服務。[2]
在傳統修辭學和藝術表現理論中,人們將隱喻和反襯視為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種表現手法,實乃皮相之見。這一是沒有看到反襯手法蘊含著深層的隱喻心智,二是將隱喻僅僅視為存在于詞語層面的語言修辭現象,沒有看到隱喻根本上是一種思維方式,可以表現在文化的不同層面和領域。藝術作品的反襯表現手法,尤其文學作品中的反襯手法在通常情況下恰恰不表現在語詞層面,而表現為由語言符號構成的句段或更大的表意單位層面。反襯的藝術表現形式(喻體)往往是語言描寫構成的意象、情景或情節,只有一個意象、一個情景或情節的語言描寫才有可能完整地隱喻或象征人們在生活中那種超常規的情感表現情態。
總之,文學藝術是作家對情感生活的隱喻,藝術家運用隱喻的過程來從事藝術品的創作。隱喻這種抒情話語方式使抒情性作品語言更加凝練而情感內涵更加豐富含蓄,從而給讀者帶來更加廣闊的審美想象空間,在審美體驗中收到綿長而深遠的藝術效果。人類的認識是有限的,人們用隱喻思維,用更為簡單的方式來表達復雜的事物或情感,隱喻已成為人們認識世界,表現思想感情的復雜性和微妙性的必不可少的認知工具。
參考文獻:
[1]季廣袤.隱喻視野中的詩性傳統[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張丹飛.中國古典悲劇論[J].貴陽:貴州社會科學.1997(1)
(作者單位:延安職業技術學院財經信息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