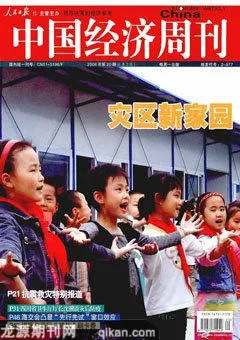曾經被誤解的直升機
5月12日晚將近11時,曾經是軍人的我不斷被朋友們“質問”:“為什么下午的地震,到現在都九個小時了,救援的隊伍只到了成都?”“軍用機場都啟用了,可是為什么直升飛機不飛?”他們甚至計算出震中汶川離成都只有55公里,奇怪怎么這么久了還沒有人趕過去。“先不說北京的,就是成都的救援隊伍,騎自行車也到了啊。”
我曾是一名軍人,一名軍醫,我經歷過1998年抗洪,但這一次,我和我身邊的朋友們一樣,與四川遠遠相隔,朋友們只能把一切焦慮、不解都發泄在我身上了。
開始的一兩天來,那個高原不能飛、山地不能飛、風雨不能飛的世界上最脆弱的機種——直升飛機,正在和軍人們一起,在救災的焦急渴盼中受到質疑,而這樣的質疑到現在都沒有完全消除。可是我常坐直升飛機執行任務我知道,如果在當時那種惡劣的天氣下強行派直升飛機執行任務,無異于置救援人員于絕地——僅山谷里的風對直升飛機就是致命的,會讓直升飛機粉身碎骨,那將不是救援,而是毀滅性的自殺。那同樣也不是士兵的光榮,而是指揮員的恥辱。
“蜀道難,難于上青天。”這句1300多年前的詩句,為這次救援提供了現實版的殘酷注解。大型機械上不去,我們的戰士就手腳并用。實在沒有路了,每隔幾米遠一個戰士就站成樹樁,用系在腰間的繩索給戰友們開辟一條通途。那些年輕的戰士,有的是家里的獨生子,十八九歲稚嫩的手,面對的是堅硬的鋼筋、水泥、磚塊和巨石。用最原始的救援,去面對危險和自己無力施救的死亡,他們內疚的傷痛可能要持續一生。而傘兵們則寫好了遺書,在4000多米的高空進行高難空降。那些曾經不解的人,知道了這些,當深受感動。
我們不缺少救援人員,也不缺少救援設備,我們的野戰機動方艙醫院只需2個多小時就可以迅速組成一所擁有200張床位、4個手術臺的野戰醫院。這里還可以包括120名醫務人員和近百名后勤保障人員,晝夜可留治傷員200名。艙內的無菌程度完全可以達到三級甲等醫院的標準。但救災的前幾天,我們仍然不能在最前線使用我們的方艙,因為選擇建立野戰方艙醫院的條件,首先要求地形平整,而當地連直升飛機降落的地點都難找到。
部隊的軍醫們是最有野戰急救經驗的人,因為這是每次演習中最重要的一環。可是隨著救災的深入,我的擔心更多了:一些頑強地堅持了幾十、上百個小時的生命,在被救出的片刻時間里迅速凋零。唏噓的同時,高死亡率的擠壓綜合癥正在被人們更多地提起。那些四肢或軀干肌肉豐富部位遭受重物長時間擠壓的人們,也許看不見外傷,但是,在擠壓解除后出現的以肢體腫脹、肌紅蛋白尿、高血鉀為特點的急性腎功能衰竭,卻成為了脆弱生命的致命打擊。沒有專業的透析儀器,救治仍然是個難題。
救災到現在,急救都已經開始退居其次,被救出來的人們更需要的是專業的腦外、骨科、胸外、腎內、神經內、心理等專業醫務人員,因為暫時脫離生命危險的傷員們,救治的路更漫長,稍有不慎,也會前功盡棄。還有更重要的大災之后防大疫,是任何人不能掉以輕心的持久戰。所有的這些,都離不開我們的軍人。
別去埋怨我們的戰士為什么睡下了,他們不是機器,災難中他們已經透支到極點;也別埋怨戰士們再不能一個人背起一個傷者,他們的能量也消耗殆盡,在那些人力難以達到的地方,物資給養很難送上去。而這一點,在我經歷的1998年抗洪的時候多次發生,能送上物資的地方食物在腐爛,而堅守在最艱難地方的部隊,沒有吃喝。
災難還沒有過去,災難中,有軍人和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