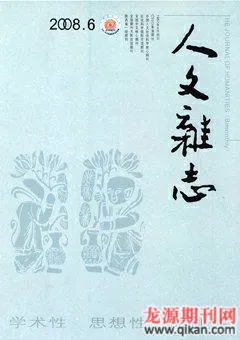從生活世界到公共領域:現象學的政治哲學轉向
內容提要
同樣是面對現代性的危機,胡塞爾堅守著理論的純粹性,對現代社會理論危機的根源做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海德格爾則以實踐的態度面對危機,對人(此在)的在世界結構做出了深刻地分析,但是由于他們都秉承著理論或者沉思優于實踐的傳統,故而都未能對政治的世界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只有阿倫特,直面這樣一個現實而重要的領域,并為之提出了具有洞見性的主張——恢復公共領域,以積極的態度參與政治,擔負起每個公民應負的責任,從而使我們在迷茫與彷徨中看到了希望。
關鍵詞 政治維度 生活世界 公共領域 交往
〔中圖分類號〕B0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08)06-0064-05
一、胡塞爾的生活世界
在《世界現象學》一書中,黑爾德不無洞見地指出,現象學的主要發現是人類生存特有的世界關聯,根據現象學的理解,世界的開放性界定著人類,但是,特別令人注目的是,在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對人類的世界的開放性的分析中,政治的生存向度這樣一個特殊類型的世界并沒有作為世界而得到認識。與胡塞爾不同,海德格爾意識到了公共性現象在現象學中的意義,但是,很可惜,由于將之歸結為“常人”而非本真的生存模式,海德格爾對政治世界的理解與評價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偏差。①
的確,如果從政治哲學的維度看,我們必須承認這一確鑿無疑的事實,即“根本原理和普遍形式的胡塞爾思想包含很少政治哲學的內容。”在胡塞爾汗牛充棟的著述中,我們很難找到“善與惡、政體與法律、智慮與政治家通過長期的專門經驗所獲得的政治知識。”
②其原因或許如倪梁康先生所言,在胡塞爾那里,“純粹理論現象學占有首要的位置”。借用保羅?利科爾的話來說,就是“人們完全可以將他(注:即胡塞爾)稱作是一個非政治性的人,他受的教育、他的愛好、他的職業以及他對科學嚴格性的偏好都決定了他的非政治性。”③胡塞爾這位純粹的現象學家似乎可以做到某種程度上的不食人間煙火。正因為這樣,所以當胡塞爾面對學生們的期待,即現象學從先驗層面轉向經驗的層面,用現象學的方法澄清一些長期以來困擾著人們的問題,從而對人類生活的此在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時,他似乎可以無動于衷,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二十年代,胡塞爾身上并沒有發現人們所希望的歷史使命感。
① 克勞斯?黑爾德:《世界現象學》,倪梁康等譯,三聯書店,2003年,第218頁。
②列奧?施特勞斯、約瑟夫?克羅波:《西方政治哲學史》,李天然等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00頁。
③ 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三聯書店,1994年,第115頁。
令人吃驚的是,在胡塞爾和海德格爾關系破裂后的1936年,胡塞爾在《歐洲科學的危機和先驗現象學》中大談“歷史”和“危機”,尤其是“生活世界”這一形下味十足的概念,似乎成了胡塞爾思想轉向的重要標志。對此,利科爾評論道,這位現象學家并不滿足于歷史和在歷史中思考,而且,他還發現了一個令人驚異的任務:像蘇格拉底和笛卡爾那樣,建立一個新時代。梅洛?龐蒂則由此認為,現象學同樣是一門哲學,它將所有本質都會指到生存中去,并且要求在事實中理解人和世界。②(注:倪梁康:《現象學及其效應》,三聯書店,1994年,第119、121頁。)在他們看來,胡塞爾似乎不再是那位固守于象牙塔中的老夫子了,搖身一變成為了一位充滿現實關照和歷史使命的實踐哲人了,但是,對胡塞爾后期思想的這種理解很難說是確切的。從“生活世界”的提出及其語境來看,正如許多研究者所言,是一個科學批判的概念而并不是社會哲學的概念。胡塞爾的危機意識的產生與其說是由于外在危機狀況的壓迫,不如說是處于一種理論家在面對理論危機時所產生的在現實問題上的超前意識。②生活世界在胡塞爾那里是本真認識和嚴格科學的根基,并沒有絲毫政治的意味。
然而,作為一個哲學家,怎么可能對自己身邊的人事視而不見呢?對古希臘情有獨鐘的胡塞爾又怎么可能忽視蘇格拉底“認識你自己”的呼聲呢?在這一點上,我認為列奧?斯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史》中的判斷是有道理的:政治哲學的缺乏并不是由于胡塞爾或及追隨者對政治的人有關的事物漠不關心,相反,胡塞爾帶有強烈倫理色彩的關于哲學家目的的想法含有為政治思想和行為提供哲學指導的志向。(注:列奧?施特勞斯、約瑟夫?克羅波:《西方政治哲學史》,李天然等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00頁。
)由于實踐領域不能滿足這樣的預期,胡塞爾才和古希臘以來的許多哲學家一樣,認為只有沉思的生活或者說理論的生活是最高的生活方式,因為“觀念比經驗更有力”,在觀念的洞見中可以去除偏見,而現象學就是這樣一種哲學,它能成功的“克服對千年王國的偏見”,從而使人放棄古老的思想習慣而成為對自身充分負責的和完全自主的。這其實不是胡塞爾一人如此,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阿奎那的上帝之城,現實的政治領域都被視為非本真的領域,對理論的偏愛可謂源遠流長。但是,理論的領域畢竟與實踐的領域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因此以沉思的方式對待政治必然對這一世界的判斷出現誤差,胡塞爾對于“政治世界特有的本質和權利的盲目”也就不可避免了。(注:克勞斯?黑爾德:《世界現象學》,倪梁康等譯,三聯書店,2003年,第220頁。)
人們對胡塞爾固守理論的純粹性的態度很難認同,生活世界這個概念的提出卻引起諸多研究者的關注,但是由于與胡塞爾立足于純粹理論的立場不同,人們往往是出于各種實踐目的來解讀這一概念,而其所固有的理論意向已經逐步淡化了,到哈貝馬斯那里的時候,生活世界作為通向“先驗現象學”的通道這一功能已經無蹤無影了,生活世界已經成為其社會哲學的奠基性概念,因為公共性的政治生活已經成為哈貝馬斯哲學的關注點了。
二、海德格爾的“共在”
如果說胡塞爾是一位純粹的理論哲學家的話,海德格爾無疑是有著強烈現實關注的實踐哲學家了。海德格爾生于其中的世界是一個馬克斯?韋伯所謂的“祛魅”后的世界,歐洲普遍信仰理性和科學的進步,虛無主義剛剛開始。按照韋伯的診斷,是“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自由喪失與意義喪失并存,而一次大戰把人們對科學的信仰也打破了,于是“上帝死了”,諸神隱退,這就賦予哲學以前所未有的嚴肅性和迫切性。在海德格爾看來,虛無主義是根本誤解存在的最終結果,是他所謂遺忘“存在”的最終結果。海德格爾把這種遺忘的根源追溯到古希臘人的思想,尤其是柏拉圖思想,因為柏拉圖把存在重新定義為恒在或其所在永遠不變的東西的結果。這個概念是如此的普及,以至于似乎提供了存在問題的確切答案,結果問題本身被遺忘了。
海德格爾曾經指出,馬克思完成了對形而上學的顛倒,也稱尼采是最后一位偉大的形而上學家,但是他們都是“顛倒了的柏拉圖主義”。他們或者以物質,或者以意志取代了柏拉圖理念的至上性,卻為人樹立了新的規定性,這與形而上學并無本質區別。但是,尼采的終點,恰恰成為他的起點。上帝死了,一切都是可能的。海德格爾認為人這種“存在者”(或存在物)與其他的東西不同之處在于,人不能像定義物體一樣來定義,對于物體可以說它“是什么”,但對于人不能說他“是什么”。因為人有主動性,能夠感悟萬物的存在,能夠改造自身和世界,因此人不是“什么”,而只能說人“去-是” 或“去-存在”。也就是說,此在是什么永遠有待于他去是、有待于他將來是什么。普通的物體是“現成存在”、“本質存在”,是定型化的東西,而此在則充滿了各種可能性,因為此在有選擇性。
作為生成的、展開的、自為的“此在”,并非自我封閉、孤立自存的“單子”。海德格爾認為,此在與世界的本真關系不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此在與世界并不是先分裂,事實上,此在的基本機制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 。在世界之中,意味著此在必然與物、與人遭遇,此在必然與他人共在,“共在”此在的在世方式。我們似乎可以感覺到海德格爾已經觸摸到了政治世界的邊緣,但是很可惜,“共在”不過是被批判、應當被超越的“非本真”的存在方式,所以,他完全是貶義地使用‘公共’這個概念,共在的方式應當聽命于更高的“思”的生活。
海德格爾認為“此在”總是在制作、使用工具中與用具發生關系,通過用具與世界打交道,而不是先認識后實踐,并且是在過程中與他人照面,他談到了制作的生活,而他本人進行的又是沉思的生活,而缺乏的恰恰是政治的或道德的生活。依照亞里士多德:沉思的生活是最高的,但政治的生活是最重要的。人天然就是政治動物,如果忽視這樣一個重要的向度,那顯然有悖于“面向事情本身”的現象學精神。而尤為嚴重的是,由于這種缺陷,可能引起內在尺度在面臨陌生領域時的混亂,從而導致像海德格爾一樣的政治悲劇。我甚至認為,對古希臘情有獨鐘的海德格爾在一個虛無主義的時代,有柏拉圖 “集權力與智慧于一身”的哲學王的情感,來拯救戰敗后的德國。德里達曾經說,《形而上學導論》將自己置于一個新的政治或地緣政治的語境中:地球上為世界統治而進行斗爭的語境中。在海德格爾看來,歐洲,特別是德國,處在一個巨大的鉗子中,受到俄國和美國兩邊的威脅。問題是歐洲是否能恢復其本源的力量,這要求“從中心發展出一種歷史的力量”。德里達說,地緣政治在這里采取了一個“精神的世界政治”的形式,這種政治要對抗世界的沒落:諸神的逃遁、地球的毀滅、人類大眾化和平庸之輩占上風。因此,要以某種精神來予以拯救,海德格爾將精神表述為力量或力,作為一個原初統一和強制的權力。(注:張汝倫:《海德格爾:在哲學和政治之間》,中國現象學網(www.xianxiang.com))在這一語境下,《形而上學導論》把精神定義為:“精神是對在者整體本身的權能的授與。精神在哪里主宰著,在者本身在哪里,隨時總是在得更深刻。”(注: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導論》,熊偉、王慶節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49-50頁。)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海德格爾和胡塞爾不同,他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注,但他從未把自己看作是政治家,而他一直也沒對此在的政治或倫理的行為進行說明的意愿,他認為“我們還遠未足夠明確的思考行為的本質”。(注:Martin Heidegger.Brief ueber den Humanismus.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