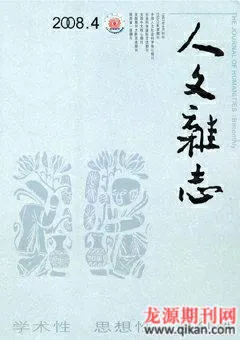空間理論的三次論爭與“空間轉向”
內容提要 空間不僅僅是一個物質性的存在,它還是一種文化、政治、心理的多義現象。空間的構造、體驗以及形成空間概念的方式,極大地塑造了個人生活和社會關系。思想史上空間本質認識的三次論爭以及近些年社會理論的空間轉向,充分展現了空間作為“未知之地”的理論魅力。絕對空間與相對空間的區分出自對空間屬性的認識與把握,先驗空間與經驗空間的爭辯則出于自然實在與主體知識的有效關聯,對空間的意義的關注則產生了社會空間與自然空間的區分。社會理論的“空間轉向”更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注入了全新的視角和思維方法,從而證實空間從來都不是單一的現實。
關鍵詞 絕對空間 先驗空間 社會空間 空間轉向
〔中圖分類號〕B016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08)04-0023-07
什么是空間?沒有哪個定義能做到一言以蔽之,因為空間無所不在,而又復雜多元。“從以往的資料可以看到,有多少種不同的尺度、方法與文化,就會有多少種空間以及在空間中展開的人類活動。”
(注:彭茨等:《空間》,馬光亭、章紹增譯,華夏出版社,2006年,第2頁。)劍橋大學最富盛名的達爾文年度主題講座在新世紀伊始就選擇“空間”作為共同主題進行多學科系列講演。無論絕對空間、相對空間,還是先驗的或經驗的空間存在,空間之于人類主體都有一種天然的情感與認知紐帶,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空間決不僅僅是一個物質性的存在,它還是一種文化、政治、心理的多義現象。空間的構造、體驗以及形成空間概念的方式,極大地塑造了個人生活和社會關系。本文擬就思想史上對空間認識的幾個不同階段,選擇性地突出對空間本質認識的三次論爭以及近些年社會理論的空間轉向,以期展現空間作為“未知之地”的理論魅力,并進一步證實空間從來都不是單一的現實。
(一)絕對空間與相對空間之爭
從唯物主義的視野出發,空間和時間都是物質的客觀存在形式,時間、空間和物質緊密關聯,無論從理論還是經驗層面,所有的空間分析都會把空間視為一種物體化的客觀性的物質構成。這種一般化和抽象化的物質形式的空間,由于其作為人類生活環境的容器(container)的特性以及可以作為幾何學分析的客體化特征,引發了關于絕對空間、相對空間的討論。
所謂絕對空間,是指空間依其固有本質屬性而存在,它不依賴于任何其他事物,它是一種絕對的載體,處處均勻,永不移動。柏拉圖在《蒂邁歐》中指出,作為一種存在,空間“不朽而永恒,并作為一切生成物運動變化的場所”。絕對空間與事物表面的映象要嚴格區分開來,這就需要一種理性審視,他說,對于空間,“感覺無法認識它,而只能靠一種不純粹的理性推理來認識它;它很難是信念的對象”。“說真的,看這個東西就像在夢中看東西似的。我們說,任何事物都得占個地方,地上或空中。對于既不在地上、也不在空中的東西是無法談論其存在的,所以說像夢一樣”(注:柏拉圖:《蒂邁歐篇》,謝文郁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頁。)。而對于現實中各種空間形式,柏拉圖認為,由于塑造這種映象的真實性并不屬于它本身,它只是別的東西的轉瞬即逝的影子。這些映象只能存在于空間中,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存在著,否則它就不存在。但他同時也承認,正是由于存在于空間中,映象也獲得真實的和確實的理由。這種對絕對空間與絕對運動的強調,在盧克萊修的《物性論》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回應,他也主張一定存在絕對空間,因為如果沒有絕對空間,“東西就絕不能運動,既然物體那種能阻塞的本性就會永遠到處對一切發生作用”,“物體就無處安置,根本也不能移動”。盧克萊修深情地贊嘆絕對空間的“毫無止境,深不可測”,“即使是閃亮的雷電在它們的疾馳中也不能完全穿透,盡管它們奔跑了無窮無數的時間,也不能由于它們不斷的奔跑,而使得它們的路程縮短半點:這么多的空間為事物向周圍伸展——每方面都有空間,毫無止境”(注:盧克萊修:《物性論》,方書春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18、23、51、54頁。)。
與柏拉圖同時代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則努力證明絕對空間是不存在的。他證明的邏輯很簡單,空間中的物體是運動的,而絕對空間無法成為物體位移的條件,因此“一個物體被置于分離存在而且不受內容物變動影響的空間里,這樣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因為它的部分若不是分離著,就不是在空間里,而是在整體里了”。進一步講,如果分離的空間不存在,絕對空間也就不會存在了。他在《物理學》中還說,“現在假設空間是指包容各個物體的直接空間,它就應該是一個限。因此應該認為空間是確定每個事物的量和量的質料的形式或形狀,因為后者是每個物體的限”。事實上,“恰如容器是能移動的空間那樣,空間是不能移動的容器。因此,當某一物體在運動著的事物內運動,或者說,在它里面移動著,如船在河里移動著,寧可作為包圍的容器里,而不作為在包圍的空間里。空間意味著不動的,因此寧可說整條河是空間,因為從整體著眼,河是不動的。因此,包圍者的靜止的最直接的界面——這就是空間”(注:亞里士多德:《物理學》,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12、95、103-104頁。)。這樣,他就在船與河的關系的比喻中,提出了相對空間的意義和價值。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對后世物理學、幾何學的發展和運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雖然對于絕對空間的敬畏感同時也常在幾何學家、物理學家的頭腦中掠過(注:例如,帕斯卡就在他的《思想錄》III,第205-206頁中寫道,“當我想到我一生的短暫時間,湮沒于永恒的古往今來,我所在的和能看到的小空間湮沒于無限廣闊的空間之中。對此空間我一無所知,它也不知道我。我處在這里,而不是那里,我感到惶恐,也感到驚訝,因為沒有理由能說為什么我在這里而不在那里,為什么是此時而不是彼時。誰把我放在這里?是誰命令和指使把這塊地方和這段時間分配給我?……這永恒沉寂的無限空間使我害怕。”),但對絕對空間的思考還是漸漸地在理論中擱置。正如貝克萊在《人類知識原理》中說,“運動的哲學含義并不含有絕對空間的存在,即是說并沒有離開感官知覺而和各種物體絕緣的所謂絕對空間”,“我們甚至不能構成一個離開一切物體的純粹空間的觀念”,“學者們關于純粹空間的本質,雖然一向有許多爭辯和困難,可我們這里所立的原則,似乎可以使它們都消除了”(注:貝克萊:《人類知識原理》,關文運譯,商務印書館,1973年,第73-74頁。)。
偉大的物理學家牛頓總結了這一絕對空間與相對空間的理論界限,他在《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的附釋中稱,“絕對空間,其自身特性與一切外在事物無關,處處均勻,永不移動。相對空間是一些可以在絕對空間中運動的結構,或是對絕對空間的度量,我們通過它與物體的相對位置感知它;它一般被當做不可移動空間”,“絕對空間和相對空間在形狀與大小上相同,但在數值上并不總是相同”。牛頓進而指出,“事物的基本處所可以移動的說法是不合理的。所以,這些是絕對處所,而離開這些處所的移動,是唯一的絕對運動”。“但是,由于空間的這一部分無法看見,也不能通過感官把它與別的部分加以區別,所以我們代之以可感知的度量。由事物的位置及其到我們視為不動的物體的距離來定義出所有的處所,再根據物體由某些處所移向另一些處所,測出相對于這些處所的所有運動。這樣,我們就以相對處所和運動取代絕對處所和運動。”(注:牛頓:《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王克迪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5頁。)牛頓經典物理學正是在相對空間的基礎上發現并創立了三大定律,并成為后世各類科學的理論原點。
絕對空間與相對空間的區分在認識論上有著重大的意義,標志著人類認識空間、把握空間的理性能力的提升。利用相對空間進而掌握事物運動規律的思維本身,奠定了現代空間科學技術的基礎,既來自于生產實踐,更被作為科學思維范式直接運用于包括教育活動在內的廣泛社會實踐之中。這種被稱為唯物主義的勝利的相對空間意識,構建了包括學校在內的所有社會空間。
(二)先驗空間與經驗空間之辨
雖然絕對空間與相對空間的區分,不可能完全脫離主體的意志和觀察位置的影響,但他們總是力求以一種遠離主體的視點,以一種純粹對象化的思維來認識空間,以期獲得關于空間本身的客觀性知識。而先驗空間與經驗空間,則將空間對于主體的意義作為考察的重點,通過把主體放置于空間之中或者把空間放置于主體之中來考察空間形成的過程和結構,從而尋求“關于人的空間的知識或者關于空間的人的知識”。其實先驗空間無疑是一種絕對的存在,一個在主體經驗之先的不涉及對象自身而與我們據以認識此對象的方式相關的先天存在;經驗空間與相對空間同樣有很大的關聯,相對空間強調了位移的條件,而經驗空間更強調了物體與位置之間的關系。
經驗空間即通過感官所知覺到的空間存在,可以從他人那里所學,也可以從外部源泉或內心反省而得,所有空間知識建立在經驗之中,最終來自于經驗。例如,萊布尼茲在《與塞繆爾?克拉克的通信》中就坦誠地宣稱:“我將在此說明人們是怎樣形成空間概念的。他們首先想到許多事物同時存在,并且注意到事物中一定的共存秩序,由此則一個事物與另一個事物的關系相當簡單。這個秩序是它們的位置或距離。當共存事物中的一個改變了同其他大多數事物的關系,而這大多數事物沒有改變相互之間的關系;另外一個新出來的事物像前面那個一樣形成了同其它事物相同的關系,這樣我們說它進入了前一事物的位置……如果或假設在那些共存的事物中,有足夠數量的事物沒有變化;我們可以說,對固定的存在物有如此關系的那些事物,像那些以前處于同樣關系的其他事物一樣,此時占有曾經是以前那些存在過的事物的相同的位置。包括所有這些位置的東西,稱為空間。”(注:莫特瑪?阿德勒,查爾斯?范多倫:《西方思想寶庫》,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第1124頁。)這種空間,我們也可以稱為關系空間。
與之相反,相同時代的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先驗感性論”中指出,“空間不是從外部經驗得出來的經驗性的概念。因為如果要把某些感覺和一個在我之外的東西(即其所占的空間部位不同于我所在的空間部分的某種東西)發生關系,而且同樣要使我能夠把這些感覺表現為在外邊而又是相互并列的(不只是彼此不相同而又是在不同的地方),那就必須預先假定有空間的表象。因此,空間的表象就不能是在經驗上從外部的出現之種種關系得來的。正相反,只有通過空間這種表象,這外部經驗本身才成為可能”。“空間是一個作為一切外部直觀基礎的必然的、驗前的表象。我們永遠不能想象到空間的不存在,雖然我們盡可能想到空間為空無一物”。康德把這種直接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時間與空間都叫做“先驗的闡明(presentation)”,最后結論性地指出,“空間所表現的不是‘物之在其本身’的任何屬性,也不在‘物之在其本身’的相互關系上表現‘物之在其本身’。就是說,空間并不表現任何依附于對象本身、而且甚至當直觀的一切主觀條件都被抽掉后仍然存在的確定。因為沒有任何確定(無論是絕對的或相對的)在它們所屬的事物存在之前能被直觀到,因而就沒有任何的確定能在驗前被直觀到”(注: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韋卓民譯,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65-66、67、69頁。)。康德對空間的看法,直接促成了新康德主義對空間問題的認識,并深遠影響著社會科學對空間的認識,當然我們不能承認經驗感受的空間會與空間表象完全相同,樸素實在論的認識必然是經不起推敲的。
一般說來,先驗空間直接承繼著絕對空間的思想,經驗空間則與相對空間的思想緊密相關;但是它們之間區分的標準卻有明顯差別,如果說絕對空間與相對空間的區分基本上已經保留了可以比較確定地認識空間基本屬性的預設,那么先驗空間與經驗空間的思考則將問題從空間轉到了認識空間的主體對對象的知識方式上來。經驗空間的知識強調了感官的能力,而先驗空間的知識則把“空間是先天直觀”作為其他相關知識得以可能的必要條件。因此,經驗空間更強調在相對的有界限的空間之內事物之間的關系構架,正是這些關系證明了空間的作用,而空間本身又強化了這些關系。而先驗空間則強調了同一的先天空間表象的存在,正是它促成人類認識和行為協同的可能。先驗空間與經驗空間的區分自然衍生出對空間的意義的關注,正是意義本身產生了各類社會空間,學校空間就是其中之一。
(三)自然空間與社會空間的區分
二十世紀以后,隨著城市急速發展對正確和合理的城市規劃的緊迫需要,同時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早期城市化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諸如居住擁擠、環境惡化、社會治安惡化等社會問題,使得社會科學領域對空間的社會性進行了許多重要的理論思考。這種空間理論可以追溯到芝加哥生態學派、結構功能主義等理論學派。
在社會學經典大師中,西美爾是唯一一位力圖創建空間社會學的先行者。他在研究社會互動的意義時,發現了從空洞的空間(自然空間)到有意義的空間(社會空間)創建的整個過程。人類城市化的整體和局部都可以被視為從自然空間到社會空間的躍遷過程。因此,他分析了互動中的各種空間形式,歸納了空間的五種屬性:排他性或獨特性;分割成塊的統一體;場所的固定形態;特定的意義;表現于行為習俗中(注:西美爾:《社會學》,林榮遠譯,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460-529頁。)。空間的排他性或獨特性、分割成塊的統一體兩種屬性其實仍然是經驗與先驗空間所具有的自然特征,而后三種特征已經滲透了社會交往分配所需要的價值意義,成為社會建構的獨特的空間性。這種獨特的空間性不僅是人類社會所刻意創造出來的特性,而且又會潛藏于習俗文化的行為規定中,直接表現于空間中人的慣習中。他在論城市現代性的《大城市與精神生活》一文中就專門論述了都市空間對都市人格的塑造的重要的影響作用(注:西美爾:《大城市與精神生活》,《橋與門:西美爾隨筆選》,三聯書店,1991年,第258-279頁。)。然而,西美爾還是“傾向于認為,隨著社會組織開始脫離空間,空間越來越失去其重要性”(注:特納:《Blackwell社會理論指南》,李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11頁。),關系空間以某種結構的形式成為一種顯學,由于其結構性要素在形成社會意義上的作用使具體的社會空間本身不再顯得重要。
這種對產生社會意義的關系結構的強調,正是結構功能主義理論滋生的沃土。在空間的不斷抽象化中結構掙脫了具體的空間實體形式的束縛,而被賦予組織、制度等非物質的直接方式以更有效地進行功能的控制和發揮。
另一方面,西美爾在自然空間的基礎上研究社會空間的意義,并追問空間的社會性對于社會以及人本身的價值,也成為研究具體社會空間知識和技術的思維原點。他的空間社會學的許多思想都在后來發展的城市社會學和鄉村社會學中得到回應。芝加哥學派的城市生態學采用的基本方法即是在生態過程和文化分析的基礎上,增加了空間向度的分析,如空間隔離形成的不同社區面貌和生活形態,以及不同的道德面貌等。然而,由于重視抽象性結構關系的技術理性的強大優勢,芝加哥學派關注具體空間形式的零星聲音顯得非常寂寥微弱。
總之,在人類社會的空前發展中,自然空間已經基本消失,抽象的幾何學和純粹的自然地形學上的空間只能是一種理想化情境中的智性操作。社會空間在告別自然空間的過程中由于對特定社會意義的強調,不斷地形成各種場所的固定形態,有著特定的空間結構和行為制度。因此對于空間來說,不僅其自然特性隨著自然空間的消失而遭受漠視,而且其社會特性也在過度地強調社會功用的結構特征而逐漸失去其具體性。空間性探索成為現代性進程中被嚴重忽略的開發后棄地。然而,隨著社會進一步發展,人們逐漸發現,空間的意義本身也需要進一步全面的考量和批判性反思,一方面所謂的空間中的“行為習俗”非常容易構成葛蘭西的“文化霸權”,另一方面社會行為效應的多面性將會以空間性特征反作用于人類自身。整體性的社會意義如果進一步簡單化為社會控制與生產的效率時,必然帶來單一功能主義空間形式的盛行,對空間性的重新關注正越來越成為社會和教育發展的迫切需求。
(四)“空間轉向”與地理學想象
雖然不同領域的空間探索不曾真正中止過,但是在“什么知識最有價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學”的今天,空間知識與技術,尤其是社會領域中空間知識,都已成為既定的抽象、確定、客觀的原理性知識。社會化分工促成的專業群體控制使之更加趨于僵化,很少有人愿意仔細思考空間構成的諸多可能性。多數人在參與教育或其他工作中,都直接遵從工具理性的空間配置,并自覺地成為現代化機器空間的一個構成部分。空間不再是主體獲取自由的先驗的或經驗的力量來源,而成為控制主體的體制構架。這樣,空間性的內涵隨之大量地流失,不信可以看看簡明大英百科全書,這里就僅把空間簡單地概括為兩句話,“空間,指無限的三度范圍。在空間內,物體存在,事件發生,且均有相對的位置和方向”(注:《簡明大英百科全書》第17卷,臺灣中華書局,1989年,第60頁。)。
所謂“空間的轉向”,被認為是20世紀后半葉知識和政治發展中最具舉足輕重的事件之一(注:陸揚、王毅:《文化研究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12頁。)。學者們開始刮目相看人文生活中的“空間性”,把以前給予時間和歷史,給予社會關系和社會的青睞,紛紛轉移到空間上來。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一位和20世紀一同降生的現代法國思想大師,在其六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為后人留下了六十多部著作、三百余篇論文這樣一筆豐厚的精神遺產,是西方學界公認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論之父”、“現代法國辯證法之父”,他的巨著《空間的生產》詳細論述了發生在社會生活的“精神”和“物質”空間的社會生產,成為一大批空間理論學者的思想源泉。Shields,R.認為,列斐伏爾對馬克思主義最大的貢獻也許是不斷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研究現代日常生活問題,但他目前對西方思想界影響最大的方面卻是對“社會空間”的發現。“列斐伏爾不斷地將自己的最初的日常生活概念譯解為一個空間與城市領域內的范疇。”(注:Shields, Rob. (1999)Lefebvre,Love and Struggle,Spatial Dialectic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P13.)列斐伏爾最重要的貢獻是將辯證唯物主義基礎從時間移向空間。美國著名的左派地理學家戴維?哈維在《空間的生產》一書英譯本后記中指出:通過1968年的歷史事件,列斐伏爾認識到了日常生活狀況的重要意義——它是革命激情與政治的核心,這種看法與傳統馬克思主義只關心工作場所的政治問題的狹隘視野是對立的。對于列斐伏爾來說,空間不是通常的幾何學與傳統地理學的概念,而是一個社會關系的重組與社會秩序實踐性的建構過程;不是一個同質性的抽象邏輯結構,也不是既定的先驗的資本的統治秩序,而是一個動態的矛盾的異質性實踐過程。空間性不僅是被生產出來的結果而且是再生產者。馬克思僅僅看到一定空間與時間制約下的物質生產,而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更是一個不斷地超越地理空間限制而實現空間的“自我生產”過程。列斐伏爾非常重要的一個貢獻是提出“空間生產的歷史方式”。借鑒馬克思的生產方式理論與社會形態理論,他將迄今為止的空間化歷史過程理解為如下幾個階段:一、絕對的空間——自然狀態;二、神圣的空間——埃及式的神廟與暴君統治的國家;三、歷史性空間:政治國家、希臘式的城邦,羅馬帝國;四、抽象空間:資本主義,財產的政治經濟空間;五、矛盾性空間:當代全球化資本主義與地方化意義的對立;六、差異性空間:重估差異性的與生活經驗的未來空間。他說,“我所概括的理論……并非試圖提出一種(或某種)空間話語,而是要把各種不同的空間及其生成樣式全都統一到一種理論之中,從而揭示出實際的空間生產過程。”因此,上文對思想史上的空間理論的回溯可以更有利于理解當代文化的“空間的轉向”。
列斐伏爾特別強調,人類的研究活動如果缺少了空間,思維的其他維度就會被夸大;空間的維度的重新引入,要求我們擯棄社會理論的整個構架。在《空間的生產》的最后一章,列斐伏爾指出,“空間將與目的明確的行動及斗爭利害攸關”。也就是說它不僅僅是“各種力量的武器庫”,“施展策略的場所”,也遠不止是“行動的劇場、冷漠的舞臺或背景”。空間在把發生其中的種種物質或力量,聚集一起,并以逐個包圍的手段,用它本身來取代每一個因素。列斐伏爾說,“它也不能被看作是一個結果或一種產物。是可以在經驗上證明的,過去、歷史或社會的產物。空間果真是一個媒質、一個環境、一個中介嗎?毫無疑問,它都是;但它的中性特點越來越少,能動性越來越強,它既是工具又是目標,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注: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Nicholson-Smith, N., Oxford: Blackwell, 429-431,353-373,16,410-411.)。
在列斐伏爾的著作《空間的生產》發表后不久,福柯作了《地理學問題》的訪談,他同樣注意到了空間的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中的命運,空間長期以來一直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辯證的、靜止的。顯然,空間和時間觀念在西方人文、社會科學中的發展是極不平衡的,空間成為了與時間及其所代表的豐裕性、辯證性、富饒性、生命活力等相對立的觀念。雖然福柯從來不把自己認同為某一學科的研究者,但他依然在他許多作品中表現出對空間的濃厚興趣,他認為,在現代都市生活的人們,處于一個同時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時代,人們所經歷和感覺的世界,是一個點與點之間互相聯結、團與團之間互相纏繞的人工建構的網絡空間,而不是傳統社會中那種經過長期演化而自然形成的物質存在。在福柯看來,空間、知識和權力問題乃是建構歷史的核心問題。他反對對歷史做線性的目的論的解釋,而是非常強調歷史的非連續性和中斷性。他以知識考古學的方法集中地對規范的理性觀念進行了顛覆,并表明規范的理性觀念在歷史上都是偶然的。因此,福柯把知識當作是權力的形式,并把自己關心的問題轉到社會中權力的地點性、特殊性和情境性運行上,因為他堅信權力的分析就是空間的分析。空間是權力實施的手段,權力借助空間的物理性質來發揮作用。這樣,空間成為政治統治必不可少的一環。在他的《規訓與懲罰》一書中,福柯對現代社會所作的空間化處理,就是將現代社會監獄化,著名的全景敞視監獄就是空間自動地、持久地、匿名地發揮監控作用的范例。他指出:“空間是任何公共形式的基礎,空間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研究空間是為了“保證人們在空間中的特定的定位、移動的渠道化(canalization),以及符號化它們的共生關系”(注:包亞明:《后現代性與地理學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28,13-14頁。)。這種政治性的空間,既是可能是統治的工具,也可能有助于人們的政治反抗。福柯在這里已將空間概念堅固地植入了文化的探討中。
列斐伏爾總是謹慎地將空間和社會的關系納入到辯證法的框架,“空間和空間的政治組織表現了各種社會關系,但反過來又作用于這些關系”(注:蘇賈:《后現代地理學》,王文斌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23頁。),社會和空間存在著一種基本的辯證關系。而福柯則強調空間對于個人的單向的生產作用,物理性的空間以一種隱秘的權力機制持久地匿名地規訓著將個體鍛造成一個新的主體形式。列斐伏爾將空間既看作是媒介,也是產物,既是工具和手段,也是目的和結果。空間本身即是一種生產力和生產資料,是一種巨大的社會資源,也是社會形態變化的淵藪。而福柯則明顯有別于這種空間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在他那里,空間只是權力的媒介,是權力藏身之處和運作場合,現代社會的規訓與控制建立于空間的微觀政治學。無疑,他們二人都是“空間的轉向”中最重要的代表,給社會科學的研究注入全新的視角和思維方法,在培植社會研究中的地理學想象力方面影響深遠。
所謂“地理學想象力”(geographical imagination)是指對場所、空間和景觀在構成和引導社會生活方面的重要性的一種敏感。它的直接對應是米爾斯(Mills)著名的“社會學的想象”概念。米爾斯說社會學的想象“可以讓我們理解歷史與個人的生活歷程,以及在社會中二者間的聯系”(注:米爾斯:《社會學的想象力》,陳強、張永強譯,三聯書店,2001年,第4頁。)。而哈維(Harvey)說地理學想象力“能夠使……個人去認識空間和地區在他們自己經歷過程中的作用,去協調與他們看得見的周圍空間,去認識個人之間和組織之間的事物關聯是如何受到分離他們的空間的影響……去評價發生在其他地區的事件的關聯性……去創造性地改變與使用空間,以及去正確評價由他人創造的空間形式的意義”(注:約翰斯頓:《人文地理學詞典》,柴彥威等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253-254頁。)。無論是米爾斯還是哈維,他們都強調他們的概念并非限定于本學科之中,他們是在討論“思維習慣”。哈維本人就把自己的著作《社會公正與城市》視為“一種去跨越社會學想象力與地理學想象力之間的鴻溝的追求”。他曾指出,“馬克思、馬歇爾、韋伯和迪爾凱姆均具有以下的相同點:他們在考慮時間、歷史和空間、地理的問題時,總是優先考慮前者,而認為后者是無關緊要的,往往視空間和地理為不變的語境或歷史行為發生的地點。……諸種空間關系和地理布局首先產生的方式,在大多情況下,往往不引人注目,被人漠視。……地理的變化被視為具有‘不必要的復雜性’而被排除在外。我的結論是,他未能在自己的思想里建立起一種具有系統性和明顯地具有地理和空間的觀點,這因此破壞了他的政治視野和理論。”(注:蘇賈:《后現代地理學》,王文斌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00頁。)
正是出于要將空間性的維度延伸到馬克思主義內部,或者說要賦予《資本論》一種具體的地理學論述,他在一度猶豫徘徊的情況下完成了《資本的諸種局限》,并認為自己最獨特的貢獻就是將空間的生產與空間的布局整合為馬克思主義理論闡述的核心中的一個積極因素。
自此以后,對空間的敏感在許多學者的不同研究領域中都得到了回應。卡塞(E?Casey)在《重回地點》一書中詳細考察了“我們所占據的地點”,由于地點(如具體定位、居住點、建筑環境、荒地和實驗場地等)的表現不一,我們如何做以及如何定位自己也都會表現不一,卡塞的哲學思辨告訴我們,只有充分認識我們的地點,我們才能夠了解自己的生活是如何迷失的。瑪克英特爾(A.MacIntyre )認為自我、德行和理性發展的方向定位與主體處身其中的環境廣泛相聯,我們不能獨立于心靈的意向性來規定行為,也不能獨立于構成心靈意向的環境規定意向自身。任何理性斷言只能就特定的時間、地點來說才是有用的,實踐理性總是地點化的理性,所以地點實踐有著獨特的倫理和政治意義,在特定的具體環境中折射出普遍性的威力。沃特斯托夫(N.Wolterstorff)則主張如同存在理性歷史學一樣,存在一種理性地理學。他認為理性的邊界會因時間和地點的不同而不同,理性的變化依賴于人們所處歷史的、社會的、個人的背景,即社會空間的不同,理性只有針對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情境才能加以把握,理性總是情境化的理性。哈拉維(D.Haraway )通過“定位的理性”對知識的真理性進行了重新評價,他拋棄了客觀性與無地點性同一的觀點,指出知識與我們所棲居的位置有著必然的聯系,提出了所謂的“社會空間的定位”觀念。他認為知識是物化的、背景化的和位置化的,占據某一位置或被置于某一位置都必然地是一個倫理問題,因此所謂客觀性總是與地點的具體化和被占據的社會空間存有內在的聯系,它們共同加入到情境性知識之中。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責任編輯:張 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