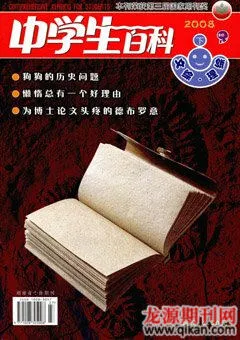只是一場明媚的憂傷
有一個歌手,你也許不會去刻意地關注她,但她會在某個有月亮的晚上用干凈的嗓音和簡單的吉他旋律將你的心徹底地融化,或在某個午后讓你在那些純粹的音符中靜靜地沉淪在那青春明媚的憂傷里,即使你已經步入而立之年。
陳綺貞,這個笑容甜美、眼神溫暖的女生,這個出道十余年只發行了四張專輯和若干單曲的歌手,這個無論是在滾石唱片還是后來成為獨立音樂人都始終堅持自我風格的音樂人,呈現給我們的,始終讓我們無法猜透。
抱著木吉他,穿著藍色連衣裙,一個人低著頭在舞臺上淺吟低唱,這是陳綺貞的姿態,甜美而任性。陳綺貞是甜美的,她的聲音清澈,眼神恬靜,唱出的曲調如同清澈小溪般緩緩流動,歌詞簡單而可愛。她唱的,是少女的心事,是孩提時的歡樂和感傷,她述說著她那套約翰·列儂的紀念版郵票,叨嘮著坐火車去湘南的海岸,幻想著她的偶像木村拓哉。這一切無疑都讓人感受到她的純真甜美。
但是任性才是陳綺貞的真正姿態。這個哲學系畢業的女生,幾乎不對這個社會發表意見,不涉及生和死,不思考任何困擾俗人的問題,只是靜靜地唱著自己的生活,陽光、空氣、花園、咖啡店。她述說她那些童年的疑問,少女的憂傷,渴望的愛情,但這些都只是她愿意展現出來的,那些她所隱藏的,我們始終無法知曉。她固執地展現她的姿態,渴望保持一種距離,她自己說,她要有自己的秘密,這樣她才感覺到安全。她的音樂,時而緩緩吟唱,時而呢喃自語,時而自問自答,她不需要通過音樂去尋找什么意義,音樂只是她展現姿態的一種生活方式。
陳綺貞所展現的,我們只能隔著一層玻璃靜靜欣賞,玻璃雖然透明,但始終無法僭越。她是在唱自己的主題曲,透過自我的眼光和標準來看待青春和愛情,偶爾涉及生活的悲觀美。通常我們喜歡借位第三人的角度來剖析周遭的人與事,但是在這種自以為是的思想渠道下,我們最終失去的是對自我以及整個世界的把握,從而走向虛偽。音樂最重要的技巧就是真實,為當下而生活,為當下而思考。在約翰·列儂的歌曲中,我們能感受到他強烈的自我,而他也通過這種方式去完成對那個時代的反思。所以在《Merry Chrismas》、《Working Class Hero》等這些歌曲中,盡管旋律簡單,配樂僅是一把木吉他,歌詞直接,但是產生的沖擊力卻完成了搖滾對一個時代的最佳詮釋。許巍歌唱青春,是從一個過來人的角度來回憶那些往事,曲調滄桑。約翰·丹佛唱著“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他對那些old golden time始終進行著精神導師般的追尋,所以他能成為一個時期的文化偶像。但是無論是許巍還是約翰·丹佛,他們都是站在那些歌曲之外的,陳綺貞卻是完全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吟唱,作為聽眾也只能看著她獨自任性和放肆著。這也是陳綺貞獨特的魅力之所在,特立獨行的女生,用任性的甜美和偏執的憂傷穿透人心。
喜歡陳綺貞,但是卻正如她在《太多》中所唱的那樣,不能太多。我們可以在午后的陽光下通過她的歌聲感受青春的純真,也可以在午夜的月光下涌起旅行的沖動,但是這始終都是她的狀態,而如果我們試圖將自己的生活去與她對照的時候只會剩下惆悵。陳綺貞是不適合唱高音的,因為青春本身就是一場淡淡地遺留的美好,而這美好的明媚之中,包含的是讓人融化的憂傷。《華麗的冒險》這首歌曲,她加入了大量的電子樂,用高音呼喚愛情,然而卻覺得這首歌是比較失去了陳氏風格的失敗之作,淪為了一首簡單的主打。而《吉他手》也如是,她的聲音在過多的配樂中失去了穿透力。
翻開日歷,卻發現,1975年出生的陳綺貞,已經到了為人母的年齡。
編輯/劉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