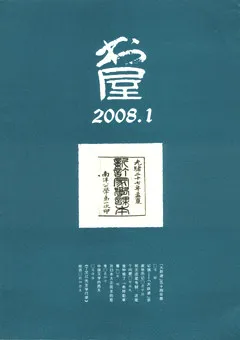何謂“民粹主義思潮”?
讀過傳播甚廣的《值得重視的幾種錯(cuò)誤思潮》〔1〕一文,發(fā)現(xiàn)這篇出自中國社科基金通訊評(píng)審專家李樹橋之手的文章,其寫作手法和觀點(diǎn)倒是比文章列出的思潮更值得注意。
文章主旨是點(diǎn)評(píng)“當(dāng)今中國的社會(huì)思潮”。一開頭就采取排除法,稱“新權(quán)威主義、新自由主義”這些“外國的社會(huì)思潮”已經(jīng)被國人關(guān)注過了;“專制主義、民本主義”等“中國古代的社會(huì)思潮”也已經(jīng)關(guān)注過了。言下之意,這些都不屬“當(dāng)今中國的社會(huì)思潮”。
排除了所謂“外國的”、“中國古代的”,作者列出了“正在社會(huì)上流行、傳播、發(fā)酵”的四大“思潮”:民粹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教條主義、無政府主義。四種主義,民粹主義居首,屬于主要的鞭撻、討伐對(duì)象,因此本文專就就其所批判的“民粹主義”作一點(diǎn)辨析。
一段時(shí)間以來,“民粹主義”一詞有些不尋常的出現(xiàn)于平面媒體和網(wǎng)絡(luò)媒體。作為一種可能的危險(xiǎn)思潮,基于防患于未然而提出,自然有道理。但如果把民粹主義當(dāng)成中國當(dāng)下主要問題,甚至張冠李戴,借以回避和轉(zhuǎn)移現(xiàn)實(shí)問題,就值得注意了。但《思潮》所作的遠(yuǎn)不止于此。
在《思潮》作者筆下,民粹主義是討伐——不是討論——的重點(diǎn)。當(dāng)然,作者可以選擇只討伐而不討論,但起碼該清楚自己究竟在說些什么。首先得弄弄明白,什么是民粹主義?當(dāng)下中國,民粹主義是不是形成一種社會(huì)思潮了?前一問題涉及理論,后一問題涉及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判斷。誰也不能說自己理論上一定正確,事實(shí)判斷一定準(zhǔn)確。但既然利用媒體公共平臺(tái)談民粹主義,讀者自然有權(quán)要求作者所談名實(shí)相符,也有權(quán)要求現(xiàn)實(shí)判斷不要離事實(shí)太遠(yuǎn)。
那么,還是從基礎(chǔ)開始。
一、什么是民粹主義?
民粹主義(Populism)并非一個(gè)版本,至少有美國以人民黨主義為代表的版本和俄國以激進(jìn)知識(shí)分子為代表的民粹主義版本;不是一種走向,發(fā)展趨勢(shì)和結(jié)果可能是極權(quán)主義,也可能被吸納進(jìn)民主政治之中。
在美國和俄國,民粹主義是幾乎同時(shí)出現(xiàn)于十九世紀(jì)中后期的運(yùn)動(dòng)或思潮。美國的人民黨主義與俄國民粹主義有區(qū)別,但在關(guān)注農(nóng)民這一點(diǎn)上是共同的。人民黨運(yùn)動(dòng)是起于十九世紀(jì)后期美國中西部和南部農(nóng)業(yè)改革者的政治聯(lián)盟,主張以廣泛的經(jīng)濟(jì)政治立法來促進(jìn)農(nóng)民的利益。當(dāng)時(shí)的美國,一些人以陰謀方式占有金融和政治權(quán)力并借此謀私和排斥人民。這一現(xiàn)實(shí)使人民黨主義者大多不相信代議制民主,而傾向于公民投票等直接民主手段。運(yùn)動(dòng)持續(xù)了二三十年,雖然最終在十九世紀(jì)末瀕于崩潰,但它的政綱和實(shí)踐影響了美國后來的政治,許多州關(guān)于全民投票公決、公眾創(chuàng)議權(quán)——即選民可以不通過代表而提出立法議案,在公民表決中進(jìn)行投票、鎮(zhèn)民大會(huì)以及罷免等保障和強(qiáng)化公民參與權(quán)的憲法條文中,就有人民黨主義的影響。
俄國民粹主義是十九世紀(jì)俄國革命運(yùn)動(dòng)的一個(gè)階段。在這場(chǎng)運(yùn)動(dòng)中,激進(jìn)的知識(shí)分子將農(nóng)民、農(nóng)民的宗教性傳統(tǒng)和價(jià)值觀理想化,希望在俄國農(nóng)村中殘存的集體耕種傳統(tǒng)基礎(chǔ)上建立一個(gè)新型的社會(huì)主義社會(huì)。
正如無政府主義并非絕對(duì)消極——在它作為“其他思想體系和運(yùn)動(dòng)的批判精神的一種來源”的意義上,就不乏積極性,民粹主義同樣不可輕率定論。無論美國版本還是俄國版本,本身都包含著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發(fā)展因子。而且它并非獨(dú)立的思想體系,而是一種政治心態(tài),往往要與其他意識(shí)形態(tài)或政黨相結(jié)合。例如人民黨主義,當(dāng)它“與其他意識(shí)形態(tài)或政黨的結(jié)合,或者向其他意識(shí)形態(tài)或政黨的轉(zhuǎn)化,有兩種不同的形式。這取決于其他意識(shí)形態(tài)或政黨為國家所規(guī)定的角色”。當(dāng)人民黨主義運(yùn)動(dòng)或集團(tuán)被吸收進(jìn)那些具國家主義性質(zhì)的政黨,“由于國家主義(崇尚國家)的政治體制所固有的、趨向壟斷權(quán)力的必然發(fā)展,權(quán)力將會(huì)集中到極少數(shù)‘精英人物’乃至某個(gè)幾乎無所不能而又被自愿地推上絕對(duì)權(quán)力寶座的領(lǐng)袖人物手中。但對(duì)此卻沒有提出任何反對(duì)意見,連懷疑也被保藏起來”。
但另一種情況是被吸收進(jìn)民主政黨或政權(quán)中去,“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及其官僚集體和強(qiáng)制力量均被置于國家治理的各個(gè)層次上的人民控制和人民決策機(jī)構(gòu)的制約之下”。瑞士聯(lián)邦制那樣的體制,就“接近于人民黨主義那種基本上是非集中化的、反國家主義的、參與制的理想”。在美國,如前所述,這種草根政治的理想,也通過被許多州納入憲法條文的全民公決、公眾創(chuàng)議權(quán)、罷免權(quán)等有所體現(xiàn)〔2〕。
這種體現(xiàn)于制度安排上對(duì)精英分子的疑懼和對(duì)人民的信任,使民粹主義在政治上表現(xiàn)為平民主義的民主制,或者也不妨把這類制度安排視為民主的一種極端形式。
一般而言,“極端”常常意味著把事情推向反面。但我認(rèn)為,在憲政體制下,國家制度中包含某些民主的極端形式(如全民公決、公眾創(chuàng)議權(quán)、罷免權(quán)等),并不等于就極端民主化了。實(shí)際上,成熟的憲政民主國家的制度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這類因素,它們對(duì)精英政治構(gòu)成某種制約;反過來,這種體制下的精英民主制成分也制約著平民主義。所以,在制度層面,極端不極端,要看有沒有足以與之形成對(duì)抗性力量的要素。
民粹主義的問題在于,它有著在原本并非截然對(duì)立的價(jià)值之間作絕對(duì)化取舍的傾向:信任人民而懷疑甚至反對(duì)精英分子,強(qiáng)調(diào)大眾參與而反對(duì)代表制,要求平等而反對(duì)一切等級(jí)關(guān)系,以及對(duì)外來者的排斥態(tài)度等。所以,問題并不在于信任人民、強(qiáng)調(diào)大眾參與、要求平等(其實(shí)對(duì)民主來說,這些本是題中應(yīng)有之義),而在于對(duì)精英的排斥、對(duì)代表制的反對(duì)等方面。
近一二十年間,某些社會(huì)政策向富人、向權(quán)貴傾斜,通過擠壓平民的生存、就業(yè)空間給富人、權(quán)貴讓路,乃基本的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政治表達(dá)上的極度不對(duì)稱也是基本事實(shí)。與這種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政治現(xiàn)實(shí)相應(yīng)的,是透著強(qiáng)烈勢(shì)利氣息的社會(huì)風(fēng)氣:吹捧權(quán)貴、蔑視平民特別是蔑視農(nóng)民和城市下層——不久前媒體披露,某市有市民拒絕與民工同乘一輛公交車。僅這一社會(huì)生活細(xì)節(jié),就透露了太多沉重信息。
如果說民眾與精英關(guān)系上的“極端平民化”是民粹主義主要表現(xiàn),恐怕當(dāng)下中國的問題并不是這樣。
二、《思潮》把什么當(dāng)民粹主義?
“有人說民粹主義是農(nóng)民社會(huì)主義。有人說民粹主義是民主極端主義”。開頭部分這兩句話表明作者知道民粹主義有兩大來路。可是卻邁過兩大民粹版本的特征、發(fā)展方向,一下子就鎖定在“草根”、“激進(jìn)”上。接下來引用俞可平相關(guān)文章,斷章取義地選取了有利于把民粹主義鎖定在“草根”、“激進(jìn)”上的表述:“作為一種社會(huì)思潮,民粹主義的基本含義是它的極端平民化傾向,即極端強(qiáng)調(diào)平民群眾的價(jià)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眾化作為所有政治運(yùn)動(dòng)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以此來評(píng)判社會(huì)歷史的發(fā)展。”由于“草根”與“平民化”的相通性,討伐對(duì)象便兌換成了“平民化”。然而,無論“草根”或“平民化”,本身并無貶義,毋寧說現(xiàn)代民主政治就是以“草根性”、“平民性”為底色的。只是,極端了,失了平衡,就會(huì)出問題,甚至走向反面。《思潮》作者引述時(shí)倒是保留了作為“平民化”定語的“極端”二字,實(shí)際上卻沒有理會(huì)這至關(guān)重要的兩個(gè)字;更沒有理會(huì)民粹主義的復(fù)雜影響和不同的發(fā)展走向,比如,被納入國家主義之中,或者與自由派結(jié)盟、被民主政治所吸納。于是,經(jīng)過按需所取和非邏輯的跳躍,民粹主義就莫名其妙地與“平民化”成一回事了,而且民粹主義的多面性也不見了,只剩下純粹的消極性,隨后開始了嚴(yán)重的政治指控:
有些人打著為民請(qǐng)命的旗幟,把自己打扮成平民百姓的代表,否定其他群體的正當(dāng)利益及其在社會(huì)發(fā)展中的積極作用,制造平民群眾和精英群體的對(duì)立,在客觀上起了激化矛盾與撕裂社會(huì)的作用。
他們……苦心孤詣地聚合并渲染社會(huì)上的不滿情緒……把改革開放以后新成長起來的企業(yè)家妖魔化。
民粹主義喜歡“惡搞”,一陣子把國有企業(yè)的高管說得一塌糊涂,一陣子把私營企業(yè)家說得一無是處。
這一攬子指控充滿誅心之論,對(duì)此倒不必在意。可這些指控究竟是怎樣跟民粹主義聯(lián)系起來的呢?文章沒有顯示。唯一可以勉強(qiáng)把二者拉扯在一起的,就是那個(gè)“平民化”。因?yàn)椤按蛑鵀槊裾?qǐng)命的旗幟”、“打扮成平民百姓的代表”、“制造平民群眾和精英群體的對(duì)立”的指控中,都少不了“平民”。然而,“打著旗幟”也好、“制造對(duì)立”也罷,都意味著搞陰謀。指控別人搞陰謀,得用證據(jù)說話。證據(jù)呢?是這些人“指責(zé)我們的改革發(fā)生了方向路線問題”,“把……企業(yè)家妖魔化”。所謂“妖魔化”,就是“把國有企業(yè)的高管說得一塌糊涂”、“把私營企業(yè)家說得一無是處”。可是,這仍然都是作者的斷言而不是證據(jù)。如此論證方法夠奇特:每當(dāng)需要證據(jù),便提出新的斷言,結(jié)果形成了一種不斷用新斷言來證明前面斷言的無證據(jù)長鏈條。證據(jù)是沒有,不過,在蔚為大觀的斷言鏈條中,隱在民粹主義背后的真實(shí)的討伐對(duì)象已見端倪,緊接著的設(shè)問更挑明了目標(biāo)所在:“國有企業(yè)改制過程中有沒有人盜竊國家財(cái)產(chǎn),造成國有資產(chǎn)的嚴(yán)重流失?非公經(jīng)濟(jì)的‘第一桶金’是否合法?”——原來,一連串指控是沖著揭露批評(píng)國有資產(chǎn)流失現(xiàn)象和利用非法手段暴富現(xiàn)象而來的!
兩個(gè)設(shè)問所涉問題關(guān)系到全社會(huì)所有人的正當(dāng)利益有沒有受損,經(jīng)濟(jì)運(yùn)行是否健康、有序,什么樣的制度缺失需要面對(duì),等等。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既是現(xiàn)實(shí)問題也是理論探究對(duì)象,而且人人有權(quán)過問。可是《思潮》作者霸氣十足,一句話就要大眾和媒體統(tǒng)統(tǒng)閉嘴:“這一類問題是司法問題,而非理論問題……這些是在法庭上進(jìn)行聽證和判決的問題,而非在媒體上進(jìn)行討論和炒作的問題。”作者想封住大眾和媒體之口,這著急上火得很沒來由,而媒體“炒作”之說則離事實(shí)太遠(yuǎn)。媒體的實(shí)情是什么?是炒“皇”、炒“星”、炒花邊新聞的空間大得出奇,偏偏在最該發(fā)揮作用的輿論監(jiān)督上動(dòng)作偏慢而且乏力。經(jīng)由媒體披露的重大經(jīng)濟(jì)案件(無論國企還是私企),比事件本身慢了許多步,早就不該是新聞了。嚴(yán)格說來,這是媒體失職,盡管媒體有著不得已的苦衷。《思潮》作者甚至霸道地以“司法問題”為由否定在媒體“討論”的權(quán)利。然而,“司法問題”就神秘得到了連媒體討論都要禁止的地步?不讓公開討論,莫非只能“腹誹”?只能“道路以目”?
這且不說了。可是,揭露批評(píng)國企高管和私營企業(yè)主中的問題跟民粹主義有何相干?
但作者用一種令人大開眼界的方式硬把二者扭在了一起。叫人閉嘴后,便描繪出一幅勞資關(guān)系和諧,國企、私企精誠合作,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圖景。緊接著詞匯一變,指控就轉(zhuǎn)回民粹主義了:“民粹主義極力在工人群眾與企業(yè)家之間制造對(duì)立,表面上為工人群眾爭(zhēng)利益,實(shí)際上是從就業(yè)、稅收和工資等方面摧毀工人群眾生存和發(fā)展的機(jī)會(huì),動(dòng)搖國計(jì)民生的根基,侵害工人群眾的根本利益。”不知道作者意識(shí)到?jīng)]有,這段話其實(shí)把“工人群眾”看成了企業(yè)家施與恩惠的一方。
“制造對(duì)立”、“摧毀生存發(fā)展機(jī)會(huì)”、“動(dòng)搖根基”、“侵害根本利益”……罪名大得嚇人。證據(jù)呢?一如既往,沒有!但正如在前面一連串?dāng)嘌枣湕l中露出的端倪一樣,這段指控字里行間也透露出,真實(shí)目標(biāo)是對(duì)國資流失、暴富現(xiàn)象以及弱勢(shì)群體遭遇的不公正提出批評(píng)的人。作者在多得令人咋舌的無證據(jù)斷言中繞來繞去,說穿了,其實(shí)就用了一個(gè)公式:揭露批評(píng)國資流失和種種不合法致富現(xiàn)象,就是反對(duì)精英;道出弱勢(shì)群體的困窘,呼吁公正、呼吁善待社會(huì)下層,就是“打扮成平民百姓的代表”,就是“否定其他群體的正當(dāng)利益及其在社會(huì)發(fā)展中的積極作用”;而批評(píng)也好,呼吁也罷,都是在“制造對(duì)立”,都是民粹主義的表現(xiàn)。
至于國資有沒有流失、暴富群體中有沒有不合法行徑,弱勢(shì)群體有沒有受到不公正對(duì)待,等等,全然不在作者視野之內(nèi)。遺憾的是,回避了這些關(guān)鍵性問題,一連串判斷全成了信口開河。
三、睜眼瞎還是屁股決定大腦?
比信口開河更糟糕的是睜著眼睛說瞎話。作者就勞資關(guān)系發(fā)表的宏論,怕是會(huì)讓人以為撞見外星人了呢:“工人群眾和企業(yè)家本是利益與共、相輔相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同一體。”好像勞資之間原本親密無間,無須博弈、談判,中國更是不存在勞資沖突的理想國!似乎壓低工人薪金、欠薪、逃薪之類損工人以肥資方是媒體憑空編造的,總理為農(nóng)婦討薪、國務(wù)院規(guī)定限期清理拖欠工資是多此一舉!
“民粹主義……從就業(yè)、稅收和工資等方面摧毀工人群眾生存和發(fā)展的機(jī)會(huì),動(dòng)搖國計(jì)民生的根基……”好像是企業(yè)家提供的就業(yè)崗位、付的工資給了工人生存發(fā)展機(jī)會(huì),似乎就這一個(gè)群體身系著國計(jì)民生的根基,其他群體都白吃飯來著。然而,那些被認(rèn)為從資方得到生存發(fā)展機(jī)會(huì)的工人,特別是其中低收入、高付出、無保障的農(nóng)民工,他們?yōu)閲医?jīng)濟(jì)所作的貢獻(xiàn)一點(diǎn)不比企業(yè)家少,可以說,沒有他們,城市建設(shè)將立即陷于癱瘓。如果作者尊重這一基本事實(shí),肯定不會(huì)把話說得這么離譜,話里話外大有資方養(yǎng)活工人、工人仰賴資方的意味。盡管也說“利益與共”之類漂亮話,卻掩不住頌揚(yáng)資方、為資方辯護(hù)的立場(chǎng)。作者的頌揚(yáng)、辯護(hù)立場(chǎng),也從語言表達(dá)和所選詞匯上耐人尋味的不平衡中透出。比如,凡提及工人和“企業(yè)家”,搭配詞分別是“群眾”和“群體”,無一處例外,決不混用,尊卑貴賤涇渭分明。不過,最表明作者立場(chǎng)的,還是那種一觸即跳,動(dòng)輒給揭露和批評(píng)我國勞資關(guān)系問題的人扣帽子、羅織罪名的做法。
羅織的罪名,諸如“制造矛盾”、“撕裂社會(huì)”、“動(dòng)搖根基”,條條非同尋常。然而,勞資矛盾是批評(píng)者制造的嗎?前不久,浙江省勞動(dòng)與社會(huì)保障局勞動(dòng)工資處處長陳秀慶說:“勞資沖突已是現(xiàn)階段社會(huì)的主要矛盾,欠薪則是其核心。”對(duì)不起,這是媒體披露的。來源是《南方周末》2007年5月10日第十八版。按作者的邏輯,《南方周末》在炒作,這位陳處長在制造對(duì)立、在摧毀和動(dòng)搖什么什么根基。我剛在網(wǎng)上看的一個(gè)新帖,大概也屬此列。帖子上有幅圖片,拍的是5月21日河南鄭州劉莊蔬菜批發(fā)市場(chǎng)門口橫幅:“拾菜偷菜下賤可恥。”在蔬菜價(jià)格暴漲的情況下,一些貧困市民靠拾菜葉解決一些生計(jì),竟成了公開打擊對(duì)象,還用上了“下賤”、“可恥”這種在某些西方國家肯定引起訴訟甚至政治事件的極端侮辱性詞匯。
對(duì)這些,作者盡可以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抵死不予承認(rèn);也盡可以堅(jiān)持認(rèn)為勞資關(guān)系是和諧的,社會(huì)底層沒有受欺侮、沒有遭到不公正,對(duì)立、沖突是民粹主義制造的。只是,認(rèn)為“勞資沖突已是現(xiàn)階段社會(huì)主要矛盾”的,有事實(shí)有數(shù)據(jù),2004年,建筑行業(yè)累計(jì)拖欠工程款就高達(dá)三千六百六十億元;交通、鐵路等行業(yè)拖欠情況還逐年增加。
但民粹主義之為民粹主義,不是因?yàn)閺?qiáng)調(diào)平民化,而是把這一點(diǎn)推向極端。可作者自己這種一邊倒、不平衡又該叫什么主義呢?
四、一點(diǎn)厘清
《思潮》談民粹主義,整個(gè)一風(fēng)馬牛。但的確代表了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即把民粹主義當(dāng)成棍子,誰批評(píng)強(qiáng)勢(shì)群體,站在受損的平民一邊,民粹主義帽子就可能扣向誰。前一陣重慶楊武夫婦為維護(hù)自己私宅而進(jìn)行抗?fàn)帲伺e受到社會(huì)各界廣泛支持,但被有的法學(xué)家說成是民粹主義;知識(shí)分子失去道德感召力,面對(duì)這一事實(shí),有的人不反省自身在這些年出現(xiàn)了什么樣的分化、其中一些人陷入了怎樣的道德沉淪和腐敗墮落泥沼,卻說他們被民粹化思潮妖魔化了……
民粹主義如此方便地成了可以隨時(shí)掄起來砸人的大棒。
然而,站在受損的底層或平民一邊說話,并不就是民粹主義;批評(píng)“精英”也并不就是民粹主義。
談底層處境困頓、謀生艱難,是在表述一個(gè)事實(shí);農(nóng)村人也好城市底層也罷,都不是受歧視和虐待(尤其受來自公權(quán)力的歧視、惡待)的理由。我談的是國民同等待遇問題和導(dǎo)致國民待遇不公現(xiàn)象的體制問題,而不是在對(duì)這部分民眾進(jìn)行道德評(píng)價(jià),不是把他們的價(jià)值或習(xí)慣理想化,更不是要否定其他階層的貢獻(xiàn),排斥其他階層的利益。
迄今為止,人們談及底層,主要還是基于民生多艱的現(xiàn)實(shí),呼吁社會(huì)公正,呼吁善待底層,給留一條自救、謀生的路,并不涉及對(duì)平民價(jià)值觀的判斷,與民粹主義無涉。拿輿論對(duì)楊武夫婦的支持來說,我看就不是因?yàn)槠淦矫裆矸荩且驗(yàn)樗麄兊脑庥鲆鹆藦V泛共鳴。就在去年四月間鳳凰衛(wèi)視晚間一次訪談節(jié)目,一位為被拆遷戶打了多年官司的律師列舉了大量觸目驚心的案例。其中一例發(fā)生在武漢:幾十戶人家,上班時(shí)間家中物件被所謂拆遷公司搬運(yùn)一空,沒了蹤跡。三年多過去,至今未獲解決。
如果說把平民理想化是具民粹主義性質(zhì)的價(jià)值判斷,那么,這不是我國的現(xiàn)實(shí)。現(xiàn)實(shí)情況是漠視底層的勢(shì)利心態(tài)讓人感受強(qiáng)烈。誠然,包括進(jìn)城謀生農(nóng)民在內(nèi)的底層中,犯罪現(xiàn)象的確不少,但動(dòng)輒把底層犯罪率作為反對(duì)取消城鄉(xiāng)二元戶口制或以此給外來人口進(jìn)城設(shè)置門檻的人,卻閉口不談以下事實(shí):第一,論犯罪率,我國掌握或靠近公權(quán)力的公務(wù)員群體特別其中的官員犯罪率也很高,已經(jīng)披露出來的官員犯罪涉及面之廣之深,令人觸目驚心;對(duì)社會(huì)的現(xiàn)實(shí)危害和長遠(yuǎn)危害最大的也是官員犯罪。第二,底層犯罪,很多情況下是被迫的,比如,為了所謂城市清潔而驅(qū)趕各種非正規(guī)就業(yè)的人而阻斷人家勞動(dòng)謀生的路,就必然生出許多事端。拿一些民營企業(yè)和個(gè)體戶偷稅漏稅現(xiàn)象來說,不堪重負(fù)的高稅收和稅外收費(fèi)無底洞應(yīng)是原因之一。相反,官員犯罪不是生活所逼而是欲壑難填,是憑借本應(yīng)服務(wù)于人民的公共權(quán)力去侵犯和侵占人民的權(quán)利。
至于“精英”群體名聲不佳,越來越成為批評(píng)對(duì)象,對(duì)這個(gè)現(xiàn)象,依我看,如果是精英的話,不必過度反應(yīng)。第一,精英群體在社會(huì)上占有或支配著更多資源,受到更多關(guān)注或批評(píng),應(yīng)是社會(huì)的常態(tài)。第二,當(dāng)招致了廣泛批評(píng),首先需要反省的是這個(gè)群體在社會(huì)中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起了什么樣的作用,即使遭到誤解,也沒必要?jiǎng)虞m拿民粹主義帽子砸人,至少應(yīng)該分辨針對(duì)著精英群體的社會(huì)情緒是根本要排斥精英,還是對(duì)精英群體的作為表示不滿或失望。第三,談及精英,還有一個(gè)不可忽視的事實(shí),即我國目前語境下,“精英”中包括了太多偽精英。此處無意展開,只引述美國文化評(píng)論家威廉.亨利遺作《為精英主義辯護(hù)》中一段話,他說:“美國社會(huì)中同樣遍是頭腦糊涂的精英分子,其中有的人起的作用極壞。有些人憑借出身或宗教信仰就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對(duì)于這種人我根本不會(huì)去為他們辯解。有人不是憑借學(xué)識(shí)和成就,而是靠著其他途徑躋身于一個(gè)得享榮寵的小團(tuán)體里,而且為此自鳴得意。這種人令人生厭……”還說:“一旦才干不再是擔(dān)任政府官員的唯一條件,信奉精英統(tǒng)治和褊狹就沒啥兩樣。”〔3〕我國的情況,遠(yuǎn)比威廉·亨利說的糟糕,招致廣泛的批評(píng)甚至反感,再自然不過。動(dòng)不動(dòng)就揮舞起民粹主義大棒,其實(shí)是缺乏底蘊(yùn)的表現(xiàn)。
回到《思潮》,我想說的是,談思潮不能不關(guān)注當(dāng)前現(xiàn)實(shí)而迫切的問題。當(dāng)權(quán)力和資本成了社會(huì)上不斷升值的硬通貨,當(dāng)官本位思潮長盛不衰時(shí),這個(gè)社會(huì)就蘊(yùn)含了太多的風(fēng)險(xiǎn)。作者文末表示要“排除各種各樣的干擾”。“排除干擾”一說過于霸道,但我相信本意是想維護(hù)社會(huì)和諧。可是,如果不對(duì)權(quán)力的胡作非為這一最大亂源保持警惕,反而在“排除干擾的名義下”堵塞言路,恐怕結(jié)果會(huì)南轅北轍。
注釋:
〔1〕載《改革內(nèi)參》2007年第9期。同一文章以《當(dāng)前我國社會(huì)思潮點(diǎn)評(píng)》為題出現(xiàn)在2007年4月9日《經(jīng)濟(jì)觀察報(bào)》網(wǎng)絡(luò)版,并有光明網(wǎng)、南方網(wǎng)、網(wǎng)易、新浪、搜狐等各大中文網(wǎng)站轉(zhuǎn)載。
〔2〕這部分主要采用了《布萊克維爾政治學(xué)百科全書》中的“民粹主義”詞條的解釋,并參考了《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相關(guān)詞條。引文均出自前者。
〔3〕(美)威廉·亨利著:《為精英主義辯護(hù)》,胡利平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