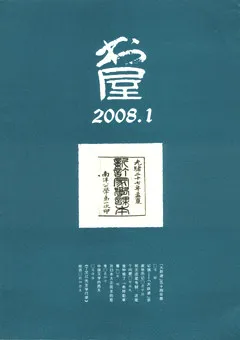信任的社會經濟學
最近,被炒得沸沸揚揚的“周老虎事件”顛覆了多數中國人的基本信任底線,以至于動用一萬七千多名科技工作者、耗資上億的嫦娥一號拍回的首張月球照片,也遭到某些人的質疑。
中央二臺的一個節目叫做《為您服務》,自從在每期加入了各種生活中的防騙常識以及對各種騙術的現場模擬之后,收視率陡增。這證實了在我們當下生活的這個國度中,信任缺失達到了何種程度!
關于信任,有人說它產生于理性。父母為什么信任子女,按照貝克爾的家庭經濟學模式,子女是父母自身效用函數的一個內生變量,父母對子女進行投資的目的是在于從中獲得自身滿足程度的提高。因而父母是債權人,子女是債務人,他們之間這種緊密的債權債務關系把他們捆綁在一起,密不可分,互不背叛。這是極端理性主義的解釋。
實際上,信任遠非理性主義所能涵括。信任有一種簡化功能。它是知識和無知、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半搭子組合。現代社會是一個充滿復雜性的系統,在既有認知水平下,世界變得越來越復雜,遠超出人的有限理性的把握程度。人的知識系統始終處于理論上臻于完善而實際上永無止境的積累和演化過程之中,無論科學技術怎樣進步,人們想在對世界的完全確定性狀態下采取行動,都永遠是一種奢望。因而,人們要做出迅捷的反應和決策,必須反求諸己——通過簡化認知模式的徹底性來消解現實世界的復雜性,說白了,就是“難得糊涂”、“不要較真”。比如說,我們走進一部電梯,在理論上它的確存在著墜落的可能性;我們坐上飛機,聽著乘務員講解逃生技巧,在理論上它也存在著失事的可能性;我們坐上火車,越過南京長江大橋(最近一條新聞說大橋要接受全面的“體檢”),在理論上它更存在著大橋坍塌、火車墜入江底的可能性;甚至于我們晚上閉上雙眼進入夢鄉,也存在睡過去就再也醒不過來的可能性。為什么我們仍然能夠心安理得地搭電梯、乘飛機、坐火車、睡大覺呢?這說明,有一種信任機制的存在,它源于對過去發生的歷史事實的歸納和總結,以過去推出未來,以熟悉推論不熟悉,以大概率推演全過程。盡管這樣做并沒有足夠的依據,甚至是一種夸大和冒險,但是它有助于化解人們主觀上的疑慮、顧忌和恐慌,使人們擺脫杞人憂天的庸人自擾狀態,有勇氣地、積極樂觀地行動起來。從這個角度看,我覺得信任更多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尤其在中國當下的環境中,很多現象是理性信任觀所不能解釋的。
把信任擴展到經濟領域,就是信用。消費者去餐館可以先吃飯后付錢,可以賒賬;上下游企業之間在供貨機制上有一系列靈活的交割方式;銀行、證券、保險,各種金融創新都離不開信用的支撐和發展。有什么樣的社會信任程度、社會信用水平,就對應著什么樣的交易成本和效率損失,就孕育了什么樣的社會經濟制度和社會交往關系。我在上海某高校外墻見過一條當地派出所貼出的標語:“受騙源于輕信,被盜源于輕心”,這充分展示了我們當下所生活的時代信任成本的高昂。一個充滿互信、互惠、民眾積極參與公益事務的社會顯然有助于促進個體間的經濟合作與社會和諧發展。信任危機和社會資本缺乏則顯然會增加交易成本、損耗社會效率。比如,由于信任的缺失,社會犯罪、官員貪腐、個人自殺、家庭破裂頻發,政府不得不把有限的資源用在防范人們不誠實的行為上,比如建立監獄、增加行政監督和反腐敗支出、增設勞教所、發展律師事務所等,大量的保守性、防御性的資源配置成為社會發展的中心,這個社會就是在“不進則退”。
國務院每年都要召開整頓市場經濟秩序的專門會議,言外之意就是中國化的市場經濟中存在著失序、失控、不合乎人的目的性的現象,其集中表現就是誠信缺失帶來的各種亂象。有趣的是,信任越是無以復加地危機,信用越是明目張膽地擴張。當下中國社會的各個行業,無論規模大小、資質如何,都大搞“金融創新”、“信用擴張”。就是你到一個很不起眼的理發店理一次發,也要經受理發師唐僧一般難纏的推銷“辦卡”。就算不考慮那么多辦卡斂財之后一夜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的行業和部門,但是你理發店又不是銀行、不是股市、不是房地產,你憑什么吸引流動性往你那里流入,憑什么讓我預支成本,難道是預支頭發?解釋不通啊。為了增加現金流而無所不用其極,真是新鮮。
信任缺失不僅會導致經濟秩序的混亂,也會帶來政治博弈的瘋狂。歷史上的叛亂與鎮壓,歸根結底是執政者與民眾之間極度的不信任,雙方都無法獲取足夠的信息、形成足夠大的交集和共同知識,來清晰地預期到對方下一步的行動,只能是零和博弈、魚死網破。哈耶克之所以一直倡導自由主義立法原則以及形式主義、普遍主義原則,就在于在一個穩定的憲政框架下,任何行為主體的行動都符合規范,具有長期性、可預見性。這就十分有利于一個高水平的社會信任結構的形成,從而降低社會成本,積累社會資本。
制度性的長期變化和一種新制度的出現,都是與一些非制度、一般看成外生的變量,比如習俗、傳統的變化有著神秘的勾連。費孝通曾對中國傳統社會有一個極精妙的描述,即以我為中心,一層層向外擴展的“差序格局”,意指是由一根根私人聯系所構成的網絡;與此相對應的,西方社會則是“團體格局”,在公共活動和政治經濟事務中比較規范和成系統。我幾年前初看老先生此一判斷時頗感不解,心中還暗自懷疑,莫非研究社會學的和研究經濟學的思路果真不同?為什么在社會學家的視野里,更強調西方國家的社會性;在經濟學家的視野里,就更強調西方國家的個人本位、個人主義方法,甚至于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中還專門批判了“社會”這個名詞,認為這是極權主義在修辭學上對語言文字的一個毒害呢?今天突然頓悟,這其實是兩碼事,兩個意思。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也倍加推崇西方國家的團體意識,他和費孝通先生一樣,所指的均是一種公民意識,而這與個體首創性、個性的自由發揮是并行不悖的。公民意識的形成與長久的契約式的社會交往關系是有著深刻關系的。西方社會不存在“不要同陌生人講話”,也不熱衷于搞各式各樣的“老鄉會”,更沒有太深刻的家族觀念。西方人跟你說:我帶我全家來看你,你很清楚那無非是他夫人與孩子,而在傳統中國,這個家的概念和范圍的彈性就非常之大了。家可以擴展到許多親屬層次,變為一個家族,進了一家門就是一家人,家國天下。所以我們通觀中國從古迄今的全部歷史,就知道我們中國人在家和國之間界限模糊,我們中國人在私與公之間貓膩甚多。中華文明仍然是十分注重家庭價值的文明,我們講仁義禮智信。但我們的信用、信任是首先建立在個人、家族的基礎之上、并由之推廣到熟人之間的。這是信任的最原始狀態,在這種原始信任狀態之下的無條件利他行為進一步增強了親族和血緣體系內的凝聚力,促進具有共同基因的同胞的繁衍和發展。在這種社會中,經濟組織的形式就只能以家族企業、家庭經營為主,而對非家庭的其他社會成員采取普遍不信任和排斥的態度。這便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狹隘的或說是畸形的信任文化或信任結構,它以特殊關系(親緣、地緣、學緣)而非普遍關系作為信任的載體,以約定俗成的前現代道德傳統作為信任的保障。
在當下,這些傳統則正在被社會轉型的疾風暴雨所打破,每一個社會階層都被裹挾進市場的洪流之中,接受新的制度環境的洗禮。一方面,一種適應市場經濟的、建基于契約意識與法治精神之上的制度信任尚未形成——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爾虞我詐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建立在傳統的熟人社會的特殊信任、人格信任也逐漸解體——熟人之間亦不能赤誠相見,“殺熟”竟也見怪不怪。這就是中國快速轉型過程中信任狀況的可憐而真實的寫照。生存在這樣一個時代,那就最好做最壞的打算,以最低的人性來揣度他人。我不是教你詐,只是,在有如盲人摸象的環境中呵護那揣在胸中的一顆善心,太不容易。與其在無數次被騙中讓那善良的心漸漸失望而至哀莫大于心死,何妨一開始就把這個世界看得稍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