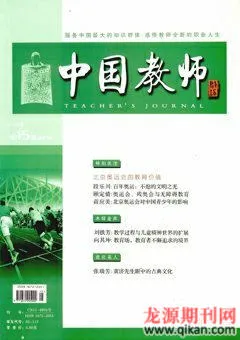淺談民間音樂遺產保護中的文化自覺
作為有五千年輝煌文明的泱泱大國,中國擁有的民間音樂種類之繁多、內容之豐富,令世人稱羨。2006年國務院確定的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中,列出了72種國家級重點保護的民間音樂,這無疑會對保護民間音樂這一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然而,審視我國民間音樂保護的現狀,情形卻不容樂觀:一些堪稱各民族思想感情結晶的音樂在悄無聲息地消逝,一些高品質的民間音樂在商業炒作中蛻變為不倫不類的文化鬧劇……在我看來,出現這種狀況既與立法保護措施的不到位有關,更與人們深層次的對民間音樂保護的文化意識有關。所以,保護民間音樂必須要首先意識到它是一種重要的文化資源,從而以理性的態度和文化的眼光來關注它的處境和命運,即有一種基本的文化自覺。如何建立對民間音樂保護的文化自覺呢?下面從三個方面對此做簡要分析。
小與大
如果把中華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總成果稱之為“大文化”的話,那么民間音樂應當屬于“小文化”的范圍。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與經濟發展趨向于全球化相反,世界文化發展的前景是走向本土化、多元化或多樣化。對此,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覺觀。文化自覺首要的問題是,如何“各美其美”,即如何用理性的態度和文化的眼光來關注、認識自己的民族文化。
民間音樂是一個民族文化的精神母體之一。民間音樂并不是一種孤立的音符運動,它是作為一種民族文化現象而存在的。從我國各種類型的民間音樂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各民族悠久的歷史發展脈絡和廣闊的社會生活,包括政治、經濟、風土人情以及審美習慣等。它像一面鏡子,映照出各民族文化的各個側面的真實風貌。雖然與中華民族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總和的“大文化”比起來,民間音樂只是一種“小文化”,但在民間音樂這種“小文化”中體現出的卻是一個民族的獨特性或個性,反映的是中華民族的“大文化”風貌。它孕育著中華民族的生命力、想象力和創造力,是傳承民族文化的重要精神載體。所以,對民間音樂遺產進行保護就要對我們的民間音樂傳統進行省思,明白“小文化”亦有大價值,“小文化”是“大文化”存在的根基。同時也要了解這種“小文化”表現形式“活態流動”的特點。民間音樂無法完全用物質的形式將其固定下來,很大程度上是靠口傳心授代代相承。民間音樂的保護不同于有形遺產,一旦失傳,它就會消亡。只有保護好傳承人及其繁衍的生態,才能有效地保護民間音樂,才能保住“大文化”賴以存在的根基。
源與流
5b7f7161154ad4913a6bb5973d17b835 近來,音樂界對“原生態音樂”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原生態”無論解讀為原初的生存狀態,還是原初的表現形式,都是以初始性為出發點。民間音樂與人們的生命和生活貼得最近,它不但處在某一種生活狀態和環境中,而且是民間集體創作、口傳心授,最大程度上保持著“原汁原味”,它的音樂風格特征是民族文化歷史沉淀的產物。因而,在我看來,“原生態音樂”是個相對的概念,它實際上就是民間音樂的別名;在原始音樂無法復原的情況下,原生態音樂也就成了民間音樂的同義語。
民間音樂作為人類的文化意識的基礎層次,它直接來自民間,由大眾口頭創作,并在流傳中不斷地得到豐富和發展,表達越加精煉,曲調漸臻完美。在文化演進的序列中,民間音樂是音樂發展的“源”,文人音樂、宮廷音樂、宗教音樂等其他音樂是音樂發展的“流”。民間音樂在傳承過程中,一些基本的主題和旋律是作為母體而流傳于世的,處于相對穩定的地位。而民間音樂真正的生命力在于,隨著傳承人對“母體”的進一步消化、吸收和應用,產生了很多基于自己感情、處境以及對音樂藝術的理解而對“母體”的音樂形式進行的即興發揮和改編的“子體”。這種即興的發揮既包括即興的填詞也包括即興的編曲,例如民歌,平時沒有固定的歌詞(如號子和山歌),但在進行“對歌”的時候,歌唱者可以根據這種固定的旋律,見景生情,在填詞的同時進行編曲,此時的民間音樂作品便會更有生機和活力。
民間音樂可以激發作曲家的創作靈感,并為作曲家提供不可多得的作曲素材。很多偉大的作曲家把民間音樂素材運用到其作品中,誕生了不少優秀的音樂經典,其中何占豪和陳剛的《梁祝》、華彥鈞的《二泉映月》就是杰出的代表。又如,西部歌王王洛賓扎根西部,寫下了《在那遙遠的地方》《掀起你的蓋頭來》等歌曲,其作品帶有濃郁的西部鄉土氣息和民歌風味;作曲家施光南也是沿著這個路子創作出《打起手鼓唱起歌》《吐魯番的葡萄熟了》《月光下的鳳尾竹》等一首首膾炙人口的名曲。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民間音樂是音樂大河的源頭活水,沒有民間音樂的滋潤,音樂的原創力就會自然衰竭。保護民間音樂,以保“源”來促“流”,中華音樂事業才會充溢著源源不斷、生生不已的創新活力。
俗與雅
當前,我國民間音樂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一方面民間音樂受到以精英話語霸權為主導的文人音樂的打壓,另一方面又被以市場為導向的流行音樂所擠占,處于雙重夾擊的邊緣。這也許與民間音樂“又俗又雅”的性質有關:音樂的俗與雅是相對而言的,民間音樂相對于文人音樂來說是俗,相對于流行音樂而言則是雅。
民間音樂代表的是一種口傳心授的民俗文化,而文人音樂體現的是以藝術經典為載體的精英文化。二者的創作和傳承方式是不同的。由知識階層創作的文人音樂,采用文字譜、減字譜、律呂譜、五線譜記寫并流傳。它包括由古代文人雅士創作的古琴及古曲詩詞音樂,也包括近代以來得知識階層新寵的西洋歌劇、交響樂等西洋音樂。民間音樂從體裁上可分為民歌、民間舞蹈音樂、戲曲音樂、曲藝音樂、民間器樂等,一般是由個人草創、集體口頭創作并依靠口傳心授的方式代代相承。民間音樂作品最初都是由某個人唱(奏)出,經過無數人你加一點,我改一點,流傳在農人、船夫、趕腳人、牧羊漢中間,逐漸定型下來。由于這種差異,在精英語言主導的價值天平上,民間音樂一直處于低位的狀態。不少人鄙視民間音樂,認為其“嘔啞嘲哳難為聽”,斥之以粗俗,棄之如敝屣。人們也往往依據文人音樂的標準判斷民間音樂的美感,很難領會到民間音樂的審美意蘊。
其實,民間音樂有自己獨特的審美語言和審美習慣。這種審美語言自由、活潑,一任天然,完全出于審美的自發,一種鮮活的生命和生活的自然表達,其中有生命的律動,也有生活的理想;有虛幻的想象,也有現實的渴望。民間音樂直接來自生命本身,更能體現生命的本質,生命之美是民間音樂的第一要素。正因此,文人音樂也總是不斷地從民間音樂這個“源”中吸取生命的源動力與氣質。遺憾的是,民間音樂只是被文人音樂作為一種審美資源來使用的,它本身卻沒有被放在與文人音樂同等的位置上。音樂雖有雅俗之別,但并沒有高下之分,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雅和俗從來都是共存的,它們共同承擔起傳承中華文化的使命。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化應當有平等的位置,應當自覺地給民間音樂留下自由生長的空間。
當然,對民間音樂的最大沖擊,還是流行音樂的泛濫。民間音樂是生命自身的流淌和宣泄,其最燦爛的文化主題是對永恒的想象和追求。流行音樂是商業社會快餐文化的載體之一,其主要任務是不斷地推出悅人耳目的新刺激新享受。流行音樂所代表的快餐文化擠占了民間音樂應有的發展地盤。這種文化只要求活在當下,不追求永恒,只需要通過市場從文化里謀利,不需要建設。它對于民間音樂的態度是挑選賣點,把能成為賣點的拿出來叫賣,而對文化本身不負有任何傳承責任。真正的新文化必須給民間文化留下足夠的地盤,重視發掘其中文化精神內涵,才有可能實現創造性轉化。流行音樂要得到長久的“流行”,大概也不例外。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哲學系)
(責任編輯:王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