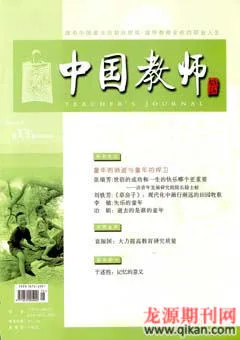失樂的童年
童年是人生的黃金時代,它閃爍著美麗神奇的光芒。童年讓人們感懷最多的就是無拘無束的生活,孩子們在游戲中快樂地成長。然而,現代教育卻讓童年的生命綠洲面臨著沙化的危險,呈現出“失樂”的童年景觀。
一、兒童生活的“大生產性”
現代教育的產生和發展對兒童的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奠定了兒童生活的“大生產性”基調,學校生活鮮明地表現出現代化大生產所具有的“數量化”和“抽象化”特征。學生的未來發展是可以預測的,只要他們進入相同的學制體系、使用相同的教材、遵從相同的學校管理制度、配合相同的課堂教學流程,那么,在預定的時間點上,他們就會被集中貼上相應的標簽,然后再被配置到不同的社會部門中去。
現代教育直接推動了學校教育的普及化發展,在中國以及更廣泛的地區,學齡兒童的生活就是一種“受教育”的生活。當“受教育”生活成為兒童生活的一種基本樣態時,則需要我們關注,兒童的“受教育生活”是一種怎樣的童年生活,它能否給孩子帶來成長的幸福和歡樂?
學校教育強調的是高效率,它對于復雜的人性需求沒有過多的考慮。學生的生活起居、愛欲物求、喜怒哀樂……這些與學習無關的事情都被推脫給家庭或學生自己。然而家庭也成了學校教育的合理延伸地,一副副誓死捍衛學校立場的家長面孔沒能讓家庭為孩子提供可以喘息的出口,做不盡的課外作業、補不完的輔導課、上不完的興趣班……這些鮮活的家庭景觀讓許多孩子萌生從家庭中逃離的想法。
此外,令人備感無奈的是,學生自己也不能給自己出口。孩子們從出生那天起就被規訓著要勤奮刻苦、出人頭地,他們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一切要求得以滿足的前提是服從家長的意愿。現代教育的普及化發展和現代學校的科層制安排把學生緊緊束縛在既定的軌道中,遮蔽了學校生活之外的其他色彩,孩子更多的時候像墻頭草那樣做出被動的順從行為。經過學校教育的統一改造,學生們很快就像卓別林在《摩登時代》里所演繹的大工業時代的工人一樣擰螺絲擰到自己也成了“螺絲人”,遺忘了童真童趣,言行刻板、生活沉悶。這樣的孩子長大成人進入社會以后,也只能像“暫出樊籠的小禽”一樣,“決不會飛鳴,也不會跳躍”了。[1]
現代教育制造了兒童生活的生產性格局,就像物品一樣,學生在學校那里可以計件生產并具有物的使用價值。“如果一件東西對使用者有好處,這件東西就叫做好東西。對于人,也可以使用同樣的價值標準。”[2]那么,如果一個學生聽話、不惹麻煩,并為教師增光,教師就稱他為好學生。同樣,一個孩子溫順聽話,他就可以被稱為好孩子。學校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正是如此這般地追求大批量地生產“好學生”和“好孩子”,社會的生產性格也正是通過成人意志不斷吞噬兒童生活的豐富性和趣味性。
二、成人繼“發現”兒童之后又“主宰”了兒童
自人類誕生以來,兒童就一直存在著,但他們的內在精神和獨立人格卻并沒有隨人類社會的發展而得到肯定,整個社會尚未在意識水平上把兒童和成人這兩個概念從寬泛的“人”的概念中分離出來。
菲利普?埃里斯的著作《童年的世紀》(Centuries of Child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