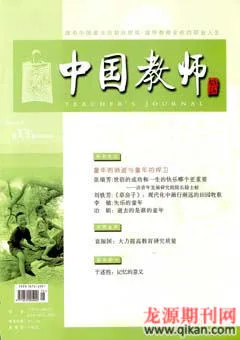記憶的意義
兩種風(fēng)格的歷史記憶
去年暑期,讀了兩本個性鮮明的日記。一本是豐子愷的《教師日記》,記錄著他抗戰(zhàn)初期的流浪教學(xué);一本是《吳宓日記》,記錄了作者學(xué)習(xí)于清華學(xué)校開始直至晚年的生活。
抗戰(zhàn)時期,是中國知識人最痛苦的歲月之一。當(dāng)時的大學(xué)中人,因不甘心在淪陷區(qū)仰侵略者之鼻息,卷起行囊,背井離鄉(xiāng),跟隨不斷退卻和遷移的大學(xué),奔波流浪。豐子愷就是這流動大軍中的一員。空襲、廢墟、窮困、生離死別……也是其日記所展現(xiàn)的歷史場景。寫日記的豐子愷,卻恰似一尊巨幅雕像,屹立在廢墟之上:那來勢洶洶、狂轟濫炸的敵機(jī),在他眼里,不過是群蠅亂舞;簡陋而異常艱苦的生活,對他來說就是人生的歷練。他會駐足農(nóng)人院外,透過門縫,仔細(xì)傾聽,去欣賞那夫唱婦隨的恬淡生活;他把廣西農(nóng)村那些他從未見過、又相當(dāng)機(jī)巧的器具,如出自匠人之手的門栓、窗欞、食籃,畫下來,并仔細(xì)品評一番。當(dāng)然,他也繪制了很多戰(zhàn)爭題材的圖畫,奮發(fā)激揚(yáng)。他的繪畫作品,觀察細(xì)致入微,刻畫入木三分,筆法粗獷樸拙、簡潔明快,真有大智若愚、大辯若訥之象。難怪,他教學(xué)生繪畫會強(qiáng)調(diào)境界高于技巧,文化重于技能;難怪,他能成為大畫家——不,是藝術(shù)大師。
讀吳宓日記,憋悶、痛苦的情緒,會彌漫在你的周圍。吳宓很內(nèi)向。你看他那時與家人的一幅照片(大概在他30歲左右),妻兒被置于身后,他戴著一副近視眼鏡,從眼鏡后面發(fā)出的視線指向水平線以下——不是向內(nèi)的沉思,而是憂郁并帶著拒絕地向外尖視。他希望自己能像“寅恪兄”那樣,“閑他人之所忙,忙他人之所閑”,專心學(xué)問,著書立說,成一家之言,卻又總受“參與”意識的驅(qū)使,一會兒當(dāng)主任,一會兒辦報(bào)辦刊。一旦投入那些事務(wù),就得同各種愿意、不愿意與之打交道的人周旋,可他偏偏不長于此道。于是,在他的日記中,你常常會看到,他會因?yàn)橐患∈隆e人的一句話,抑郁終日甚且數(shù)日。對于那些“不可忍”之人、之事,他竭力忍讓,然后在日記中拼命發(fā)泄。他拳拳服膺“寅恪兄”,甚且認(rèn)為他是自己的老師。他也真該拜陳寅恪為師:不僅是學(xué)問,更是那種毅然決然的處世態(tài)度。可惜,他最終還是沒有學(xué)會。
我猜想,吳宓寫日記,記得那么仔細(xì),持續(xù)時間那么長,對他自己來說,主要是一種情感宣瀉,平衡心理的手段。可對于我們來說,這位多愁善感者的日記,還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豐富歷史素材。有些東西相當(dāng)生動有趣——畢竟,它反映了吳先生的真性情,盡管充滿了痛苦和傷感。
記憶的意義
人是歷史的動物:他在記憶中形成自我意識,獲得生命的意義。記憶有選擇性。人總會竭力強(qiáng)化那些想記住的東西,回避甚至淡忘那些不想記住的東西。但事情不會總遂人愿。一些東西之是否被記住,還與經(jīng)驗(yàn)的強(qiáng)度有關(guān)。那些強(qiáng)烈的經(jīng)驗(yàn),會在潛意識中一再呈現(xiàn),想忘也忘不了。
經(jīng)驗(yàn)有消極和積極之分。有些人會有意無意間記住那些積極的經(jīng)驗(yàn)。所以,我們會看到一些人,總是笑咪咪的,充滿快樂。他在接納自己過去的同時,也接納他身邊的每一個人。你從他身邊走過,他微笑的目光與你不期而遇。你自然會以為,他是在向你微笑。那笑,一下子就拉近了他與你的距離,讓你與他親近。這樣的人,并不是沒有痛苦的經(jīng)歷,但他的態(tài)度,使他能超然面對過去,不會把過去的痛苦不斷放大,更不會把它無有休止地傳輸給別人。他安慰痛苦中人,會說:“瞧!雨過天晴,有一片彩虹。快點(diǎn)看哪,別讓它溜走。”
有的人,會傾向于記住消極的經(jīng)驗(yàn)。一個人獨(dú)處的時候,他會不斷地揭開未愈的傷疤,帶著痛,去吮吸自己的傷口。日子久了,那痛,就堆積成皺紋,深深的,一道道,縱橫交錯,成就了一副苦不堪言的臉。他猛然看見你,會立即換一副笑臉。但那笑,也苦苦的,讓你退避三舍。他不是沒有快樂的經(jīng)歷,只是那快樂,更多的是成就了他人生的無常感。他想抓住,想讓它留住,卻留不住。于是,他對幸福的感覺倒超然起來,好像無所謂了。他只有時刻準(zhǔn)備著,受苦受難。好像只有痛苦,才是永恒的。這樣,我們就會明白,他為什么總在尋求“本體”,尋求一種超越此生此世的“本然”的東西。表面上,這種尋求有一種理想主義的情調(diào)。其實(shí),那不是理想主義,而是悲觀主義,厭世主義。他安慰痛苦中人,會略帶不屑:“嘿!那算什么?我經(jīng)歷的那些齷齪事兒,比你要嚴(yán)重得多。”
上個世紀(jì),有兩個“瘋子”,尼采和福柯,也曾讓這個世界上那些所謂“有思想”的人瘋狂。他們顛覆了人們的整個歷史記憶、文化想象。尼采從反權(quán)貴開始,走向反庸常,最后通向“超人”。福柯循著“考古學(xué)”的方法,把一切都還原為“權(quán)力關(guān)系”。但我面對那“考古學(xué)”,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在由遍地骷髏和草木灰組成的層層廢墟上,除了蠕動的“考古者”,還有生命的氣息嗎?一想到那考古者也會變成骷髏和灰燼的時候,我不禁毛骨悚然。
所以,記憶這個東西,可能充滿快樂,也可能充滿痛苦。盡管有時快樂會使人淺薄,而痛苦則可能使人深刻,要讓我選擇,我寧愿成為一個淺薄的快樂者。深刻的痛苦畢竟還是痛苦,我不太愿意像魯迅那樣去面對“淋漓的鮮血”和“慘淡的人生”。
當(dāng)然,有些記憶也可能是以“客觀”形式呈現(xiàn)出來的流水賬。碎片一樣,沒有感覺,記憶者本身先已成了“考古學(xué)家”的工作對象。我覺得,對于生命的記憶,還是要由生命來承擔(dān)。那里,有色彩,有線條,有波浪,有花紋,更有氣息。那氣息會讓生命充盈,撫平我們滿臉的溝壑。
不滅的記憶
在過去,四十歲上下的讀書人,就開始寫回憶錄了。學(xué)中國教育史,讀過陳鶴琴先生的書。他就在不惑之年,寫了《我的前半生》,借著回憶過去,暢想未來。那未來自然沒有明白寫出,但看得出來,它潛藏在作者對過去的回憶中。到了這個歲數(shù),未來似乎已經(jīng)很確定,卻又不那么確定;態(tài)度似乎很堅(jiān)決,卻又帶著一絲猶豫。
我如今四十有四,已過了不惑之年。不知為何,最近總想起一些過去的事,特別是中小學(xué)時代,點(diǎn)點(diǎn)滴滴,綿延不絕。有時候想得出神,自己會啞然失笑。仿佛看到了少年時代的我,光著身子,一個人置身無邊的海洋,隨波逐流,與天地為一。于是就借著悠閑的春光,從頭寫來,帶著微笑,帶著眷戀,也帶著憧憬。既然都是些無法忘卻的往事,索性就叫《不滅的記憶》吧。一邊想,一邊寫,再一邊自我欣賞。讓記憶溫馨自己,讓過去照亮未來。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xué)教育學(xué)院)
(責(zé)任編輯:王哲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