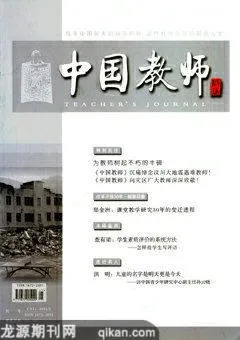經義詩賦 隨時更革
宋朝的科舉制度建設,不僅建立了怎么考的制度,健全了考試規程,對后來的科舉考試,具有示以準繩、框其趨向的作用;而且對考什么,究竟是重經義還是重詩賦,也做了積極的探索。
在唐朝,明經和進士是最重要的考試科目。雖然這兩科的內容屢有變化,但基本上是明經著重帖經和墨義,進士側重詩賦。所謂的帖經,就是給出一行或幾行經書中的文字,要求將其中故意隱缺的文字填上,類似于今天的填空題。所謂的墨義,也就是以書面的形式,簡單直接地回答經義。墨義答題的格式較為固定,以“對”開始,而以“謹對”結束。如考試題目是:“‘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這是《論語?憲問》第三十七段中孔子的一句話,考生要知道這里的七人,是指古代的七位隱逸之士,即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與。所以標準答案就是:“對:七人: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與也。謹對。”如果考生不知道答案,就答“對:未審。”
由于帖經和墨義考察的是記憶能力,只要熟讀經典就能考中,錄取的名額也多,往往是進士科的幾倍乃至幾十倍,得第頗為容易,所以當時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說。意思是說明經中第容易,即便是30歲中第,也屬于年老的了;相對而言,進士中第很困難,即便50歲中第,也尚屬年輕。雖然唐朝的“取士之科,以明經為首”,但應舉之人,往往搜章摘句,“只念經疏,不會經義”,“正如和尚轉經相似”,如同會說話的鸚鵡一般。因而全社會上上下下,都頗為輕賤明經科。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進士科考察的是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要求具有較高的文學才能,為時人所看重。“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集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為聞人。”(《唐國史補》卷下)時俗所尚,眾望所歸,也使得一些飽學之士、英發才俊只應此科,這就使得進士科在當時眾多的科目中,得以脫穎而出,一騎絕塵。所以當時有“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唐摭言》卷一)之說。隨著唐朝歷史的發展,進士科日漸顯貴,而明經科則日趨沉淪。
宋朝承襲唐朝的發展路向,最初也是趨重詩賦、崇尚進士科,鄙薄記誦、冷落明經科。宋朝常科的考試科目有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和明法等。進士科之外的其他科目,統稱諸科。由科目名稱的變化,就可見明經科已經不能與進士科相比倫。以擅詩賦中進士之后,往往升遷迅速,位至通顯。進士及第即一等的進士,大多數都可以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進士科為宰相科。而明經科的遭遇,則每況愈下。流風所及,以至于“有司待之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士入試之日,主文則設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徹幕以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飲硯水而黔其口者,當時傳以為笑。歐公亦有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諸生。’其取厭薄如此。”(《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八)進士和明經在科考之初的禮遇,就已經有天壤之別。
然而,經術畢竟是“王化之本”“致治之源”,熟讀經書、通曉經義是傳統士人的天職,是其安身立命之本。改變重文學、輕經術的社會風習,在科舉考試中,強化六藝,“責治道之大體”,淡化詩賦,“舍聲病之小癡”,一直為眾多恪守正統觀念的人士所吶喊和倡導。北宋時期的幾次變法,都包括了對這種社會風習的移易和矯治。
宋神宗時,范仲淹任參知政事。他提出了一系列除舊布新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精貢舉”。在他看來,六經才是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詞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舍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四十三)這樣就決然選擇不到經國濟民之才,即便選擇到了所謂的人才,也建樹不了經國濟民之業。為此,他在要求各地學校延請“通經有道之士,專于教授”的同時,又建議改革取士之法。“進士先策論而后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同前)慶歷四年推行的慶歷新政,對科舉考試的內容做了新的規定。省試分策、論、詩賦三場,改變了過去先詩賦后策論的順序,以突出策論的地位,加強策論的重要性;廢除帖經和墨義的考試形式,舉子有通曉儒家經典愿對大義的,則考試經典大義十道。
在這同時,新政還規定:士人必須在學校學習三百天以上,才有資格參加州縣的“發解試”;廢除密封謄錄試卷,由各級學校各地方官員保證舉子的學歷和操行。這些做法,勢必使權勢、賄賂、私情和個人喜好在科舉考試中發揮作用,回到“通榜”乃至察舉的老路上去,動搖宋朝初年一系列以公正、公平為目標的制度建設,因而引起了眾多的反對。不到一年,新政大臣紛紛調離朝廷,包括科考內容在內的全部新政被廢除,先詩賦后策論的做法復舊。
在經過激烈爭論和反復比較之后,在科舉科目方面,宋神宗最終采納了王安石的意見:科舉只設立進士科,原來的諸科都并入進士科,罷除詩賦、帖經、墨義,改用大義、論、策取士。每個考生要在《易》《詩》《書》《周禮》《禮記》中選治一經,此外還要兼治《論語》《孟子》。所選治的一經稱大經,兼治的《論語》和《孟子》稱為兼經。每試四場,第一場試大經大義十道,第二場試兼經大義十道,第三場試論一首,第四場試策三道,禮部試策增二道即五道。殿試也一改以前試詩、賦、論三題的做法,只試策一道。
雖然包括明經在內的諸科,這時都納入到了進士科,考試的科目,只有單一的進士科,但此進士已非彼進士。“此時的進士科不考詩賦而側重于經術,名為進士科,其性質實際上卻已經蛻變成了明經科。”(劉海峰:《科舉考試的教育視角》第66頁)考試大義或經義,就是從儒家經典原文中,摘出句子或段落作為題目,要求考生作文闡發其中的的義理。這種形式與“論”相似,但“論”出題的范圍不限于經典,而及于史書和諸子,經義出題的范圍,則嚴格限定在儒家經典的范圍之內。既要通曉經義,表述也要有文采,兩者兼備才算合格,與明經科考試墨義,只是粗解章句完全不同。經義的格式發展到南宋后期,已經比較固定,成為元明時期八比文和八股文的濫觴。
宋神宗之后,王安石罷相,司馬光執政,開始“元祐更化”。作為王安石最堅定政敵的司馬光,廢除了王安石幾乎所有的新法,但保留了科舉改革的基本成果。在他看來,取士應當先看一個人的德行如何,而后再看他的文學怎樣;即便單純就文學而言,也應該首先著眼經術,其次才是文采。他認為廢罷賦、詩以及經學諸科,是“革歷代之積弊”;而專以經義和論策試進士,則是“復先王之令典”,是“百世不易之法”。但以蘇軾為代表的文學派,極力主張恢復詩賦取士。在這種壓力下,最后采取了一種折衷的辦法。元祐四年,正式分立經義進士和詩賦進士。詩賦進士要在《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選習一經。第一場試所選習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第二場試賦及律詩各一首,第三場論一首,第四場試子、史、時務策二道。而經義進士,則必須選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左傳》為大經,《書》《易》《公羊》《谷梁》《儀禮》為中經,《左傳》得兼《公羊》《谷梁》《書》,《周禮》得兼《儀禮》或《易》,《禮記》《詩》并兼《書》,可以選習二大經,但不得選習兩中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第二場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第三、四場如詩賦進士一樣試論和策。經義進士以經義定取舍,詩賦進士以詩賦為去留,名次高下,則參照策、論綜合評定。
哲宗親政后,開始“紹圣紹述”,廢除了司馬光的做法,進士罷詩賦,專習經義。在此之后,“士子各徇其黨,習經義則詆元祐之非,尚詞賦則誚新經之失,互相排斥,群論紛紛。”(《宋史》卷一五七)爭論盡管激烈,但是否恢復詩賦取士,朝廷一直是議而不決,直至亡國也沒有結果。南宋初建,很快就設立了經義進士和詩賦進士兩科,但不久之后,一度又合并兩科為一科。這樣分合無常,令考生不知所從,無有定向,頗多不便。紹興末年,朝廷議定復立經義進士和詩賦進士,并“永為成憲”,直與趙宋王朝相終了。
可見,宋朝科舉考試的內容,一直處在摸索過程之中。“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初無定制。”(《宋史》卷一百五十六)經義與詩賦的分合,與時變化;重經義還是重詩賦,因勢消長。在中國科舉史上,總體而言,前期重文學,后期重經術。宋朝的探索之路,精彩地呈現了這一轉型的過程,其中的幾次科舉改革,則是實現這一轉型的樞紐。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
(責任編輯: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