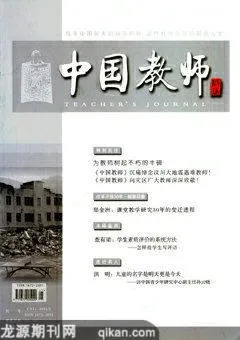游走在承接與拓創之間
縱觀中國畫的發展歷史,不難發現中華民族繪畫創造源出于“意象”。意象,即主觀意念想象。意象造型,就是不拘泥于形似,不模擬自然,而是把自然物象作為傳情達意的中介,強調對自然物象內在神韻上的把握。它不需要真實的視點、科學的透視、比例和客觀色彩理論,而是根據主觀意愿、理想及對物象大悲大徹“順天應人”的理解和關注,跨越表象、跨越時空、默契著客觀法則的自由表象和任意組合,并與“天人和一”的傳統哲學觀念一脈相承。儒、道、釋三家的“入世”、“出世”、“忘世”以及莊禪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眾生平等”的寫意觀,構成中國畫的“物我交融”、“主客合一”的,既觀物又觀我的宏觀思維方式。“入世”就是積極投身參與現實生活,在負起責任、擔起義務中求得自由。“出世”超逸了現實“獨與天地精神往來”,是對“入世”,欲念情感的超脫,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絕對自由。只有精神上的絕對自由才能到達“忘世”——“忘懷現實”的物我兩忘、渾然一體的,“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的境界。儒、道、釋三家都是“天性自然主義”,三者會通,構成了中華民族的自由超越的精神。精神的無限性,才能達到藝術的無限性。中國畫傳統就是在這種精神完全自由下,對時代及人與自然的所感所悟,自由自在、隨心所欲的表達和表現。正是這種超越精神的自由,使中國畫家在認識大千世界時,一開始就排除了時空序列性的制約。這種精神的超越需要歷史的展現,更需要跟隨時代的脈動、與時俱進。
眾所周知,中國畫傳統博大而精深,源遠流長,它與整個民族的文化素養、審美意識、思維方式、美學思想、哲學觀念等息息相關。它是開放的,不是封閉的;它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不斷的“生成”之中。學習中國傳統不是簡單的從前人那里繼承和積累美術技能知識、制作方法及審美意識,不是簡單的繼承、模仿、再現、復制;而是應該學習傳統的精神——“創新”即揚棄。
“創新”就是打破舊的秩序,建立新的和諧;突破舊的思維框架、審美定勢而努力創造出新的形式。生活中,我們常常發現一些藝術家因一兩幅畫得名,找到了所謂自己的風格、樣式就不再敢求新求變,而是畫地為牢。就好像一束枝繁葉茂、花苞累累的鮮花,當第一朵鮮花綻放時,就應順其自然,任它開花結果,自生自滅。然后再孕育新的力量綻放另外一朵,使之更加絢麗多彩,只有這樣它才會生生不息、碩果累累。而不要僅停留在第一朵鮮花面前大做文章,對其千般呵護、萬般保鮮,即便是噴“定型液”、涂鮮亮顏色,它也終將枯萎、失去原有的生命意義。“任何藝術形式或手法,都不可能紅顏永駐、長生不老,都不可避免地要經歷發生、發展和衰亡的過程。對已經完成歷史使命并日趨衰敗的藝術形式和手法,人為的耗時耗力給予搶救是不明智的。”傳統就好比鮮花,只是生命過程中的一個亮點、一粒果實,傳統的精神就好比它的“根”、它的全部的生命動力。鮮花否定枝干,果實否定鮮花,留下的是生命。我們應該繼承傳統的創新精神,否定或超越傳統的樣式。傳統的精神是一個活生生,不斷生成和發展著的生命本原,而不是一種法則或一套審美樣式。正如人們意識到的,當我們把一種技藝變成一套程序固定化、教條化的時候,其實正是背離了傳統的精神。
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沒有永恒的真理,沒有清晰、精確的概念和標準,沒有完美完備的結論,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一切都是處于永恒的流變之中,無論是創作的理念,還是創作的技法,抑或創造者自身的藝術感悟都會因人因地因時而變。藝術創作中沒有創新,就好像失去了生命本原的花朵。終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根之木”。
任何時期、任何時代,藝術品的創新都是在表現自我對客觀事物獨特感受和認識的情況下,依據兩個條件得以完成:一是與創新所伴隨的時代的脈動。二是與藝術品的創新相關聯的材料和技法的革命。
一、創新必須跟隨時代的脈動
任何藝術作品的創造都是根據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哲學思想等情況,進行有的放矢的創新求變。藝術是時代的靈魂,是時代精神的折射鏡。“創新并非指表現現代題材,也并非指全新的繪畫手段;而是指從作品深層到表層滲透著的與以往不同的時代氣息,和時代觀念”。藝術作品應當符合時代的審美取向。一切手段都可以是舊的,關鍵在于對時代新觀念、新理念、新認識的重新選擇和重新組合。中外藝術大師的創作歷程無一不是游走在承接與拓創之間,無一不是緊緊跟隨時代的脈動,例如:德國柯勒惠支的《織工暴動》《母與子》《犧牲》《死神與小孩》;西班牙戈雅的《1808年5月3日的槍殺》;法國達維特的《劫奪薩賓婦女》、德拉克羅瓦的《阿希島的屠殺》;俄國列賓的《意外歸來》,蘇里科夫的《近衛軍臨刑的早晨》;美國約翰?特朗布爾《幫克希爾大會戰》等。他們的畫像一面鏡子折射出當時社會政治動亂和革命戰爭帶給人們的挫折、災難、困苦、恐慌、悲傷與無助。
印象派伴隨著時代物理科學的發展,在一個早晨睜開了雙眼,看到了繽紛的色彩,突破了人類的固有色的認知概念。打破了以往單一色調、造型嚴謹的古典主義的審美框架,從此藝術家們的畫面充滿了浪漫色彩和激情,拓寬了繪畫領域的新天地。
畢加索之所以被稱為“藝術偉人”,是因為他一生的藝術生涯都是在不斷擯棄舊風,探索新路的自我否定之中,他在不同時期、不同感覺,產生出不同形式的美術作品。前無古人,即便是有后來者,或后來者超出了他,也占據不了他第一人的位置。因為后來者只是重復、再現,而沒有創新。達?芬奇的《蒙娜麗莎》也是如此,即便后來者畫出了遠遠超過《蒙娜麗莎》的驚世之作,但它依舊難以擺脫“仿效”與“臨摹”的夢魘,更無法撼動《蒙娜麗莎》的原創價值。
中國近代畫家石濤的創作風格的形成與演變也是一個極好的例證。作為四僧之一,石濤的畫對近現代影響最大,而在當時他的影響遠不及漸江。明清時代的傳統繪畫,講求的是靜穆作風和寬宏氣度;講求儒家“文質彬彬”和“外柔內剛”的靜態美。而對那些表現出強烈氣氛和外現張力感的繪畫視為浮躁和粗鄙,甚至對“渾厚”、“剛勁”皆有所忌,王原祁就說,要“化混沌為瀟灑,變剛勁為柔和”(《麓臺畫跋·題仿大癡筆》)。漸江就是把靜態美做到了極至,他的靜的意識、靜的精神狀態附和當時社會的審美需要,所以才倍受推崇。其后,社會發生了大變動、大變革,當世界列強用大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弱肉強食的時候,民族意識覺醒了,不再柔弱、不再寂靜。民族意識決定了時代的審美標準的改變。這個時代需要雷霆萬均之勢,來驅除列強,掃除黑暗勢力。因而需要吳道子的磅礴大氣和“天付勁毫”,需要梁楷式的天風海雨的逼人氣氛,需要石濤的“沒天沒地當頭劈面”式的縱橫揮灑。石濤的畫筆情放縱,奇異多變,“動”到極點。以奔放“動態美”取勝。從這個意義上說,石濤的畫在契合時代脈動的同時,也筑就了其獨樹一幟的畫風和強勁的生命力。
由此可見,不同時代的政治經濟、科學文化,哲學思想,都會影響人們的審美觀念,同時也不可避免對藝術作品的風格、樣式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創新要跟隨時代,抓住時代的脈搏。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這樣的藝術作品才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和蓬勃的生命力。
二、繪畫材料和技法的棄舊圖新是中國畫創新的基礎性建構
繪畫風格、形式的變化與創新往往以材料和技法的開創性變革為先端,畫家的創新理念也大多借助材料和技法的創新來得以表達和傳遞。繪畫材料和技法的創新與革命,一直是國畫創造者不懈探尋的領域,也是中國畫創新的基礎性建構。中國畫材料和技法的創新在傳統與創新的悖論中,一直艱難地游走在承接與拓創之間。
縱觀中國畫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中國畫已具備了一套完整完備的、獨特的藝術語言和表現技法、藝術樣式及材料使用的寶貴經驗,并伴隨著時代的精神在不斷地完善和發展之中。
從中國畫表現技法的發展看:最開始使用比較簡單的“五筆七墨”、“十八描”發展到“皴、擦、點、染、絲”;以及“沒骨”、“雙鉤”、“工筆”、“寫意”等形式語言;另外還有“膠”、“礬”、“油”等繪畫媒介的混合使用;“鹽”、“砂”、“洗滌劑”等特殊技法的配合運用等等,在逐漸地豐富發展和棄舊圖新。
從中國畫藝術樣式的發展看:最初的基本要素是“線”和“面”;再由“線”、“面”發展到“色彩”、“明暗”;色彩、明暗的進一步發展,是在平面上塑造“立體空間”感;再進一步是“半成品”藝術,亦即是在畫面上粘貼實物(如植物、昆蟲)和“現成品”等等。近年還出現了巖彩畫和綜合材料等繪畫形式。從中也可以看到多源化的發展趨勢。
從中國畫材料使用的發展來看:原來由“墻上、門扉上、天花板上”發展到“布帛、絹綾”,再發展到“紙”上。現當代中國畫的多元趨勢在保留“紙”的基本運用基礎上,有的又延伸到“亞麻布”上。在顏料使用上由原來的“礦物質顏料”,發展到“水彩、水粉、炳稀”的混合運用及礦物質“粗顆粒”和各種“金屬泊”、“泥土泥沙”的混合運用。總之,這些技法、形式、材料的形成和不斷發展,是伴隨著時代科技的進步、審美觀念的改變而出現的。并伴隨時代的進一步發展而不斷完善、發展和延伸。
隨著信息時代和知識多元化趨勢的來臨,中國畫所賴以附麗的社會生活正日益變得豐富多彩,原有單一的繪畫材料和技法已不能充分表達現已拓寬的繪畫題材。題材的拓寬需要與之表現形式的擴大。新形式的擴大需要新的語言技法和材料的不斷豐富與更新。中國畫的創新,需要根植于華夏民族的傳統文化并跟隨時代的精神,不斷開闊視野、吸納百川,以“拿來主義”的精神,廣泛地吸收古今中外不同民族、不同畫科的營養。研究邊緣學科的處女地,把握各學科相互滲透的時代脈動,才能創作出與現代人精神結構相吻合,表達現代人新宇宙觀、新時空觀以及新審美意趣的形式語言,形成有別于傳統文化的創新語境。
(作者單位: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學院美術系)
(責任編輯:王嘯)